王祥夫 文人心志 闲逸情怀
文/ 韩修龙 厚圃

王祥夫
1958 生,辽宁抚顺人,现居山西大同,著名作家、画家。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冈画院院长。文学作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等,著有《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40 余部。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美、法、日、韩文在域外出版。美术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2015 年亚洲美术双年奖”等。
王祥夫是著名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米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谣》《屠夫》等,中短篇小说集《顾长根的最后生活》《愤怒的苹果》《狂奔》《油饼洼记事》等,散文集《杂七杂八》《纸上的房间》《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等。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散文《荷心茶》获第一届“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第一名,长篇小说《种子》英译本获美国丹佛尔奖等。《儿子》《怀孕》《回乡》《西风破》《驶向中北斗东路》等中短篇小说被改编并拍摄为电影。
王祥夫还是一名著名的画家,他的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深刻的人文意识。他曾说过,“文字与绘画一样,要达到那么自然舒适,一切都从平常起,但一切到最后又归于不平常,不平常也只藏在平常之中”。他还认为,艺术家和作家都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一个人的兴趣太单一了不好,你既写文章又写字画画儿,到最后你会明白你占了不少便宜,画画滋养着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反过来又滋养你的画儿。
可以说,王祥夫的审美情感是平民化的,但平民化的作品不是给人以社会性主题的图解,而是更加原汁原味地展示出生命中的本质力量,从而由低调的平民意识升华为深沉的人文关怀。这一如他专注于底层的人物和琐细的生活的短篇小说,牢牢植根于乡土,从卑微且苟活于草间的草虫中寻找共鸣。他那简约的用笔、准确的把握、高度的提炼,更是助他对大自然和大自然中的生灵传达出丰富的情感:喜爱、怜惜、慨叹、欢欣甚至歌颂,并将自己生命的体验——或创痛或欢悦、将人生的况味融进笔墨色彩构图之中,从而构建起自己的风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世上最好的文章应该是用血泪写的
王祥夫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学,在他12 岁时就已经读完了《中国文学史》,而那时候他最喜欢的是郑振铎的那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唐宋和明清小品他都十分喜欢,这也为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一个作家,终其一生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完成他自己的语言体系,这里包括句式或语言风格及特点,好的作家一定是语言家,一定在语言处理上要与别人不一样,这就像是戏曲中的流派,你一开口,人们就知道这是谁了,这很重要。”王祥夫说,他的小说和散文在语言上共同的一个追求就是尽量口语化,尽量像是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让人感到亲切。
说到流行的闲适小品,王祥夫认为我们似乎写不过古人,首先在于古人一旦执笔为文首先想到的不是要给人看,而是想要把自己内心的愤怒或感受写出来,像《天问》啊、《离骚》啊,包括颜真卿的《祭侄稿》,他们是不写就活不下去,不写就有要死掉般的难受。而我们虽然有时候也痛苦着,但我们的痛苦都比较大众化,太大众化的痛苦到了后来就不太像是痛苦了。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瀚海,好作品几乎无法一一枚举,相对明清,我还是比较喜欢先秦和唐宋的散文,心与情血与泪都在文字里,降至明清,如张岱和三袁等小品文作者都渐渐闲适起来,不是说闲适就不好,但王祥夫还是喜欢看些血泪文章,这点和王国维的主张是一致的,世上最好的文章应该是用血泪写的。虽有血泪,但还要温柔敦厚,他不喜欢岳飞的《满江红》就是因为太壮志了,昂扬壮志。他喜欢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李后主、李清照的东西有血泪在里边,但声气是婉转于心扉之间,真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一时有多少的惆怅与苍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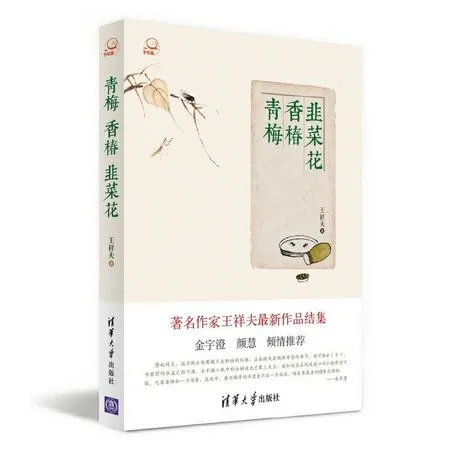

我们只能是贴着生活写作
谈到散文写作,王祥夫认为当下散文家比比皆是,但东西好的少,一是心性的东西少;二是文化素养太低;三是急于搞一个什么流派出来,写文章不是打仗,低调一点最好,也最好不要搞什么集团军,你的散文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当下的几个评论家说了算,是时间说了算。王祥夫以为,“中国的散文还是要有中国传统散文的特点,最好短小一点,用周作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除了要用必须用的生活品之外还需要一些完全没用的东西,比如闻闻花香,看看山岚光影。他曾说过一句话,是关于艺术的,“艺术”二字是梵语的译音,原意是“做”,艺术是做出来的,而这个被艺术家做出来的东西注定是没用的,既不像是工具,又不像是什么消费品,艺术其实是没用的,没用才是艺术,要是有用了,或有大用了,那就不是艺术了,是工具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把艺术变成了工具。”“所以,我写散文和我的小说一定是不一样的,小说要批判现实,要揭露和抨击它,而散文却适合于‘只谈风月’,让人轻松点,让人咀嚼一下文字,比如《西湖七月半》这篇小品也就是在意境上取胜,文字上取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这就够了。我写散文,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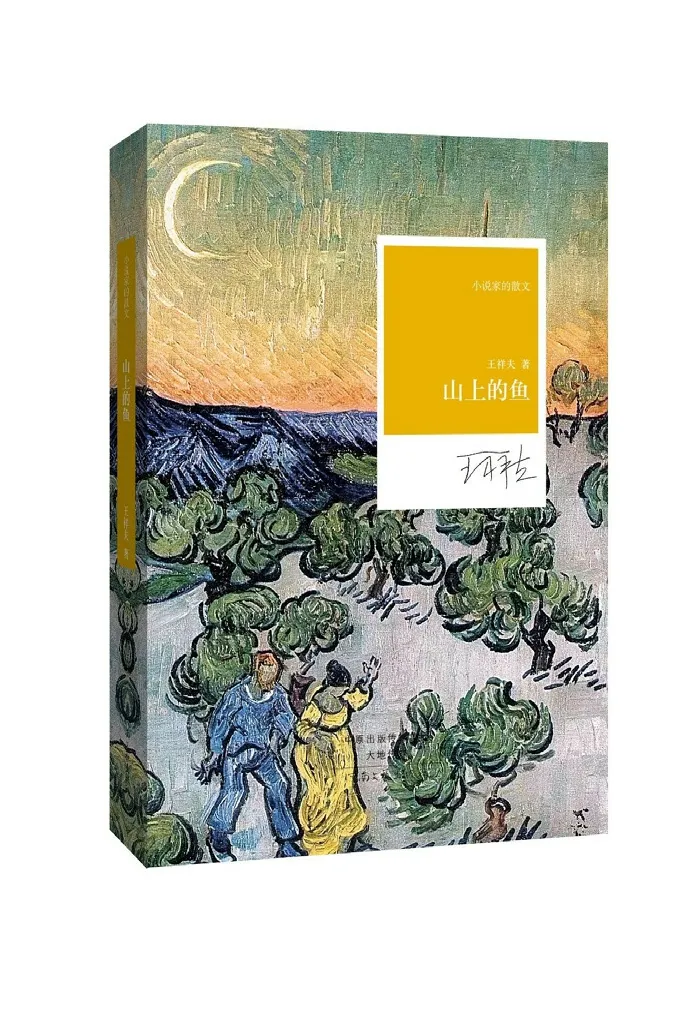
王祥夫喜欢《红楼梦》,这么多年来读《红楼梦》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就是有再伟大的理想,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不可能“高于生活”,我们以前经常说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不对的,作家面对生活,是既不可能“高于生活”也不可能“低与生活”,你说一说可以,实际上你做不到,你高于生活,那你的东西就是伪现实主义,你低于生活,你低一下给我看看,你也低不来,我们只能是贴着生活写作,这就是《红楼梦》带给我的最好的经验。
写作之余每日习画
王祥夫自小习画不辍,继承中国笔墨传统,花卉草虫从向齐白石等前辈取经,到逐渐有了自己的态度,自成一格,充满了王氏韵味。那些谷穗、水仙、鸡冠花、紫藤或者秋海棠,多是大写意,看似“粗枝大叶”,寥寥几笔中尽显功力,不过当那些草虫一闪现,这些“粗枝大叶”便只好退到后面去,成了渲染烘托的背景。他笔下的蚂蚱、蛐蛐、蜻蜓、蜜蜂、灰蛾……无论工与写,皆形神兼备纤毫毕现,没有一丝丝的造作与呆板,特别是最难画的虫足,一提一顿,一转一弯,笔断而意连,有筋有骨又富于弹性。如此工写相衬,虚实、动静、浓淡、繁简、素艳相结合,既能至广大又能尽精微。观王祥夫的画,不喧哗,不芜杂,不清高,也不媚俗,线条简逸,色彩淡雅,给人以内心的安宁。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画表现了宇宙的“无限静寂”,那些花花草草,还有小虫,还有因小虫的鸣叫而益显幽深的氛围,都折射出画家平淡、恬静的心态。而作为观赏者,则不得不调动视觉、嗅觉甚至听觉,仿佛一不留神,那些可爱的精灵就蹦没了影。
王祥夫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希望他做一个画家,希望他的哥哥做一个古琴家。还在王祥夫上小学时,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句话王祥夫直到现在都不敢忘怀。他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是学电气的,也画画儿。王祥夫回忆说,“我画虾,画了许多节,我父亲就说‘虾能有那么多节吗?’就亲手画给我看,几节几节说给我,在这方面,他是严谨的。我父亲给我请老师,第一位老师是朱可梅先生,从画工笔花鸟开始,而我现在只画画工笔草虫。我的第二位老师是吴啸石先生,教我画山水。我现在还是以写作为主,写字画画是每天起来必要做的日课,就像吃早饭喝茶一样很少会有间断。现在是每天最少要画一只工笔虫,我的眼睛还行,所以想多画一些。我还会做颜色,比如赭石、朱砂,都会自己淘澄。”

土狗
好的工笔虫要靠感觉
王祥夫曾说过,齐白石老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本色”。无论是诗、书、画、印,还是为人,都呈现着一个“本色”。说到白石老人“本色”,其真正意义王祥夫认为是白石老人的画风不怎么受别人的影响。但他总是在影响别人,别人的东西一旦到了他那里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白石老人的气场真是十分了得,是一个巨大的胃,有那么好的消化能力,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在白石老人身上,肯定一点的是没有士大夫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老农民或老木匠,质朴而聪慧,一生下来就已经八十岁,到了八十岁以后还是十八岁的那样一颗心。你看他用颜色,赭石就那么漂亮,胭脂就那么好,花青就那么丽亮。我在中国美术馆离近了看他展陈于展柜里的册页,一下就被他的颜色和墨色迷住,且不用再说其他。白石老人的本色还在于他的干净,画什么都不灰。白石老人的诗写得好,但说到他的画作却没有诗的东西在里边,他的画里更多的是民间的情趣,但把他的诗书画印综合在一起,这真是十分了不得的,都有主张,都有建树,白石虽是一个农民的底子,但他一出现就是君临天下的气派,他真正本色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他永远在影响着别人,却不受别人影响,别人到了他那里只会被消化。朱新建针对画家有“葡萄酒和葡萄”一说,而白石老人既是葡萄酒又是葡萄!

红叶小蝉
白石老人的花草与虫,一个是写意,一个是工笔,合在一起是兼工带写,世人无出其右者。王祥夫钦服而又身体力行,也画得一手工写有致的花鸟草虫。王祥夫从实践中得出好的工笔虫是要靠感觉的,首先要笔下的功夫好,但更重要的是那种感觉。画工笔虫这么久,王祥夫才明白,几乎所有的工笔虫都要有写意的东西在里边,古代一位书法家说写楷要飞动,写草要静,这就把怎么画好工笔虫的道理告诉了人们。“你说工笔虫要工,一旦工到和原物一样,和照片一样,那才难看呢,一个苍蝇,你把它用放大镜放大了看,然后再画,画到和用放大镜看到的一样,那你这个虫子就不能看了。画工笔虫,重在取舍,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你都要心里有数,我画蜻蜓和白石老人就不一样,我的蜻蜓的两只眼留反光的白点,看上去眼睛就更水灵好看,我们这地方把蜻蜓叫做“水包头”,说的就是它那两只眼睛的水灵好看。我画蜻蜓翅膀根,要在赭石上再加一点点朱砂,以表现蜻蜓翅膀下面隐约可见的部位,这都和白石老人不同,画什么东西,你要多画,还要多想,多看实物,然后就会明白一些东西。画工笔虫最容易画死了。就眼力而说,苍蝇肯定是最难画的,颜色和勾线都麻烦,虽是工笔,却要极写意,极工的东西要有极写意的东西在里边才行,蜜蜂飞动的那种感觉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王祥夫的画是典型的文人画。文人画曾作为古代知识分子遣怀的方式,表达精神诉求,它的存在可稀释沉积于文人心中的苦闷,舒解精神上的重压。王祥夫的作品既不取媚于上,也不炫耀于下,他所描画的不仅仅是现实表层和面面俱到的“形似”,还接续了文人画“寄寓”的可贵传统,除极力画其所见,还画其所想、所知,因此从他的画里,你能读出的更是他的人品、才情、学养、操守、趣味等。但是,王祥夫的作品有时又似乎超出了文人画的范畴。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梅兰竹菊等成了文人寄托志趣、情操的物象,而王祥夫的作品却超越了固有的题材,将花卉草虫这些百姓喜闻乐见的寻常题材纳入创作中来。无论画里的物象,还是题字、印章,呈现出对鲜活生命的褒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对艺术精纯境界的追求。而且,并非所有文人画家都敢将精细复杂的草虫入画,因为这需要极高的写实能力,更难的是如何甩掉精雕细刻所引发的那种刻板,使作品散发出更多的生活气息和乡野趣味。

荷塘蜻蜓

老玉米

葫芦

小品 34cm×68cm

小品 34cm×68cm
——草虫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