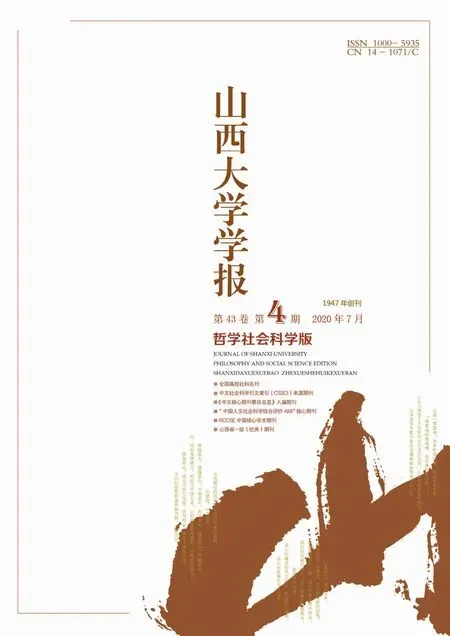明清辟兵宝物母题、辟邪观念及其佛道渊源
王 立,韩雅慧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还珠楼主(李寿民,1902-1961)对辟邪信仰有深切的理解与娴熟表现。《蜀山剑侠传》第一四八回写初凤在安乐岛遇虎面龙身的怪兽龙鲛,“角能辟水分波”,且喜与水陆猛兽恶鱼为敌,融御敌、辟水辟邪于一身[1]1731-1732;第一八七回写凌云凤在岷山白犀潭下地仙宫阙见水晶柱:“乃是辟水之宝,便无人来,柱前后这一片也是常年无水。”[1]2406-2407《青城十九侠》第五十三回写灵姑斩取千年蜈蚣脊骨宝珠九粒分赠吕伟父女等,每人佩一粒,“以为山行辟毒之用”。后王渊凭宝珠慑退滇黔凶悍的铁线蛇(蒺藜练);灵姑所佩红珠(蜈蚣眼珠)发出红光照红洞壁:“那蛇仿佛遇见煞神,退又无路,急得身子似转风车一般摇摆直上,意似要破壁飞出”,[1]1504-1509后才挣扎僵卧死。龙鲛角辟邪来自《抱朴子·登涉》:“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退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以此角著积谷上,百鸟不敢集。’”[2]312冷兵器时代如盾牌类防御器物只能挡住正面,以抵御锐器打击,而更多的威胁如水火、毒气等,则防不胜防,多种辟兵、辟水、辟毒、辟邪等“消极防御”宝物遂多发歧变。何以明清以降此类故事踵事增华愈加活跃,当与神秘思维的认知局限有关,也与内忧外患、水旱瘟疫叠加形成的死亡恐惧氛围有关。而与之呼应的巫术、辟邪仪式,凭借神奇宝物为媒介,杂以咒语,借助宗教法术与想象消极躲避灾难,此又与生产力及科技力量处于劣势的现实状态形成非良性互动,使辟兵辟邪母题展示出防御式生存竞争策略,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辟兵宝物的多样功能与社会属性
明清小说辟兵类宝物呈现复杂的功能特征指向,其丰富性与持有者的宗教特性、世俗社会伦理以及叙事者的道德精神评判标准等都有密切关联。
首先,是辟兵宝物对于英雄的护佑,往往与人物的教门派系有关。《封神演义》第七十八回写通天教主发雷震诛仙宝剑,元始天尊顶上千朵金花璎珞垂珠,剑下不来。接引道人头顶上现出三颗舍利子,也射住了戮仙剑。“舍利子”暗示这辟兵宝物实出佛门。当通天教主发雷震那陷仙剑时,“只见老子顶上现出玲珑宝塔,万道光华,射住绝仙剑”,准提道人手执七宝妙树放出万朵青莲,也射住了绝仙剑。道教应用的辟兵宝物,实所受佛家影响,像璎珞垂珠、舍利子、青莲花均佛常出现的宝物。《西湖二集》写女仙马自然拥有辟兵术,“又传辟兵咒,道:‘唵,阿游阿哒,利野婆诃。’每日清晨,诵一百二十遍,可以辟兵。又神仙辟五兵冠军武威丸,能辟疾疫百病、虎狼蛇毒。凡白刃兵戈盗贼,一切凶害,不能近身……羖羊角一两半,烧焦黑,各为末,如细粉,以鸡子黄并赤雄鸡冠上血和为丸,如杏仁、尖样三角,绛囊盛五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间,居家悬当门上,一切盗贼凶恶兵自解去。”[3]所用辟兵、辟邪(病、毒、精怪等)之物讲究而渊源有自。《飞龙全传》第五十六回写文修祭起宝物兵器金铙,劈向赵匡胤,“(匡胤)泥丸宫早现原神,只见这赤须火龙伸爪把金铙抓住,不得下来……”[4]文修大惊,谢罪退兵。第五回写山大王董龙、董虎见匡胤头顶门现赤龙,吓得收兵求赦。辟兵宝物昭示出主人公身份,意想不到又合乎情理,一再强调帝王发迹得天佑。一些名将亦然。《五虎平西演义》也写狄青金盔藏血帕鸳鸯,还有人面兽面具。小说第七回写乌麻海以大斧劈下,狄元帅金盔上血结鸳鸯毫光冲起,斧不能下。[5]此宝仙师王禅所赠,英雄仿佛具“双重保险”。《万花楼演义》第二十回授此宝者被置换为狄太后,懿旨吩咐把血鸳鸯镶嵌金盔上避诸妖刀箭;第二十四回宝鸳鸯霞光可挡住对方大刀[6]。这种被加工到头盔上的辟兵宝物,极为符合狄青的战将身份,成为宝物书写的主要模式之一[7]。
其次,是以辟兵宝物抵御对拥有者部下、同伴的袭击。《五虎平西演义》写辽将牙里波以丸弹祭空中,张忠、李义被追得飞跑,“幸得狄元帅盔上血帕鸳鸯红光飞起,丸弹不能下来。元帅又把金刀向空中撩上几撩,说‘妖物慢来’,果然,这弹子光华冲散了……只因他的盔甲、刀马,皆乃鬼谷仙师所赠,是以妖法不敢近前。”[8]本来,狄青头盔的血帕鸳鸯是仙师赠予自用的,但这宝物功能也扩散辐射到其部将,部将为本体力量的体系构成部分,在荣损与共的战斗“共同体”关系中,辟兵宝物的社会伦理化功能得到显现,拟人化地表现出宝物似有生命物,也具有正义善恶的道德辨别力。
再次,辟兵宝物,还往往具有辟火等其他泛化的辟邪功能。《封神演义》第七十二回写火灵圣母打翻姜子牙,被广成子拦住,“火灵圣母把金霞冠现出金光来,他(她)不知广成子内穿着扫霞衣,将金霞冠的金光一扫全无”,怒而剑砍火攻,被广成子以番天印打死。“扫霞衣”克“金霞冠”的相生相克威能,与拥有者代表的正邪派系紧相关联。《说唐演义后传》写薛仁贵等九人进了天仙谷口,张环、张士贵父子的火球火箭雨点般打来,仁贵以九天玄女赠的水火袍罩在九人马上,火不着身[9]。照应了小说第二十四回玄女所嘱:“若逢水火灾殃,即穿此袍,能全性命。”《粉妆楼全传》也写木花姑黑气喷来,因罗灿身佩雌雄二剑不能相侵[10]。辟邪兵器亦当来自剑崇拜的辐射力。
复次,辟金(兵器)珠、辟火宝衫,往往表现佩戴者身份可不一般。《圣朝鼎盛万年青》写天子微服私访,以五宝绸汗衫送当铺,无人识货,还是成安当铺张计德给价百两,原来这五粒珍珠纽乃连城之宝,狄青、五虎平西取回的,“旗上有避土、避火、避风、避尘、避金五颗宝物即此物。于是利刀砍不伤,炭火烤,火灭。”[11]第九回,84-88宝衫放水缸不湿。但宝物出世激发了张计德贪欲,唆使店主以假珠替换,张被杀。小说还写姚粦中五毒神针,这五宝珍珠衫使其肿毒全消而苏。[11]十三回,131清代历史演义这类描写,所在皆是,种类与功能较先前均有扩大化趋势。
最后,揭示辟邪神物的由来。如辟火法宝,无名氏《后西游记》写金星送给小行者一粒可生金的“金母”才豆大一粒黄土,他埋地下:“化成金汁,将地土培厚,任是妖精,也钻他不动了。”[12]这里“金母”实一种黄土,辟兵宝物与传统五行生克理念相结合。
二、辟邪仪式的军事想象与宗教观念
与丰富的文献载录相对应,辟兵宝物实际运用所显现的辟邪观念与实用操作更为复杂。近年来结合巫术文化研究,辟兵法术也被认为是传统辟邪观念的继承与新创[13]。如有的出土文物被考索为“避兵图”[14]。河南邓县长冢店画像石墓二主墓门楣“驱魔逐疫图”,绘有猛虎正欲扑食仰面跌倒的怪兽,虎后绘一兽,“形体似马而头生一角,应是可以辟火的神兽矔疏。”[15]甚至,在具有空间想象和更为形象直观的汉画像石,也有了朱存明、李立兄等研究[16]。又如马王堆汉墓《太一避兵图》,研究者认为其图体现的避兵仪式,可能属“兵祷”,即元鼎五年秋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图。”[17]


观察动物昆虫行为有巨大军事价值。晚唐易静词集《兵要望江南》,托猿公以宣神道,名曰《白猿奇书兵法杂占彖词》,多有对动物昆虫之于战争征兆的占卜,为《占鼠》《占蛇》《占兽》《占水族》《占鸟》等,如《占蜂》:“军行次,蜂蝶接连来。定有伏兵居草莽,逆好防林木与山崖,先探保无灾。”据考该书诸多传本都出自明天启二年苏茂相本[24]。苏氏叙:“兵家有杂占彖词,名曰《白猿奇书》……上而日月云星风雨雷电之变,下而山川草木鸟兽虫豸之灵,中而人事国计,以及厌禳占验之术,罔不巨纤俱备。”此当与明代后期辽东战争需要及其激发的“兵书热”有关[25]。辟邪宝物的叙事功能因与宝物自身物理特性、宝物地域局限以及宝物被附加的社会伦理内涵等结合,致使宝物的个体生命张力在军事与宗教实践中充分彰显。
其一,是护身原始巫术功能,昭示了其与艺术审美的结合。如辟兵宝物与北方真武帝崇拜交汇,《妖乱志》称军阀高骈重用方士吕用之,后者“匣一铜匕首”献,“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其实,“铜匕首”的保护庇佑功能除利器本身外,还有“北帝所佩者”的顺势巫术在[26]。宝刀辟邪见干宝《搜神记》,说有神王方平赠陈节长刀二口,其一名泰山环,“独卧可使无鬼,入军不伤。勿以入厕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后求者,急与。”[27]神赐宝刀可辟鬼,但禁忌秽气。相生相克之理折映出人对宝物的“爱惧”共存之心。
辟水物亦早有之。段成式称长白山邵敬伯就从水中宫殿获赠辟水物。说南燕时有人寄敬伯信称是吴江使,请沟通以渡过长白,取树叶投水,有人引入水宫,一翁发函开书:“裕兴超灭。”敬伯出时蒙赠刀,说持此无水厄。其年宋武帝灭燕。后夜发洪水举村没,唯敬伯坐榻床(大鼋)到岸[21]131。辟水物使得邵敬伯水中行成为可能。如果说,刀含有鱼龙畏惧铁器信仰,那么,树叶避水则是神树崇拜延伸。宝物的艺术审视从远古和神秘,走向现实和大众,拥有了更多的世俗审美特征。由此,威力更大的辟水物则可将一方水的容积迅速缩小,继元杂剧《张生煮海》,这类神物更普遍地进入民俗视野,石成金《笑得好》称龙王的恩主失去煮海宝物很尴尬:一人好放生,龙王感恩命夜叉赠一宝钱为“摆海干”,将此钱在海中摆,海水即干,金银任取,其人大富后钱失,只空手摆,夜叉说你手中钱都没了,还摇摆什么?[28]说明民间对这类辟水宝物广泛熟悉,才有能笑起来的前提。
其二,辟邪兵器保护其使用者,常与对敌方的震慑力相搭配。说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为西戎所惮,据吐蕃战俘的印象:“尝见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遗留的宝剑有时在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21]62-63。清代民间还传闻剑气、古剑能辟邪,说泰山麓道士练气,能鼻中吹气二三丈,凝结不散后吸入;古剑可治百病驱疫,某家人相继死,三岁幼子亦垂毙。道士仗剑怒目视榻上:“半晌,子手足忽屈伸,索茶,饮以药,卒得不死。”[29]
其三,是与宝物同某些珍稀英雄(也包括不同凡响的反面人物)命运神佑的信念结合,从而曲折、艺术化地表达生命体与特定宝物之间有机联系的生态理想。恶势力或对手的偷袭、进攻,对有着神物护持的人物往往并不起实际作用。宝物兵器、特定人物身上某些部分似乎伴随着该人吉运的始终,辟邪护身,而兵器宝物失去、毁损则往往为该人物败亡的先兆。这一观念西域早有,法国汉学家沙畹笺注《宋云行纪》,载宋云自述北魏熙平元年(516)奉命与僧惠生(一作慧生)同赴西域求经,到佛沙伏城(《大唐西域记》的跋虏沙)城北白象宫,寺内佛像庄严华丽:“寺前系白象树,此寺之兴,实由兹焉。花叶似枣,季冬始熟。父老传云:‘此树灭,佛法亦灭。’”[30]白象树乃该寺保护神。物在,某种更有价值之物亦在,这一思想当给予中原人深刻印象。而类似观念北方民族广泛存在,如蒙古族“宝物失则人亡”信奉,说有蒙古人告窝阔台,前夜伊斯兰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尽害其畜群。窝阔台命以千巴里失(货币名)购此狼,赏以羊一群来告者,命释狼,狼刚被释,被猎犬群起啮杀。窝阔台见此忧虑沉默许久,语左右:“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寿。孰知其难逃定命,此事于我非吉兆也。”[31]不久果死。此中亚传说印证了中原的同类型故事,如关公长髯中“须龙”,在其败亡前梦中告离;岳飞沥泉枪也在遇厄前失去,等等,这代表了英雄的兵器本来就不单为杀伤性武器,也护佑着英雄自身免受伤害;这又不限于正面英雄形象,《平闽全传》写梅花洞女妖里金容(鲤鱼精)腹中五光珠被紫金钵盂收走,即被斩,洪水随之退去,亦为多种宝物表现模式之一。[32]
其四,体现上天好生之德与佛教救度思想。说安禄山作乱时,女尼真如被人领见天帝和诸天,他们商议说第三宝不足以对付下界“疠气方盛,秽毒凝固”,须用第二宝。授八宝,连同先前所授五宝,把宝名和用法授给真如。这五宝其一即“玄黄天符”,辟人间兵疫邪疠;后又出示八宝,代宗得宝后,“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即登位,乃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邑为宝应焉……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壖高厂,境物润茂。”[33]天赐宝物危难能救护大众,这一功能又须与世间帝王及大众的向善之心呼应。因此往往道德上乘、禀赋优秀且具备拯救社会能力者获此宝物,能很好地领会并及时完成上帝旨意。
其五,辟邪宝物常被用来说明殊方异物的神通,既渲染“辟兵宝物”的边缘特征,又以“他者”的眼光展现宝物神秘来源及其神力。这也是在与异域交流过程中,对“他者”神秘恐惧及中外、地区间战争中“自我矮化”的表现。《酉阳杂俎》载代宗即位日庆云见,楚州有尼真如被人接上天,天帝言下方有灾,“令此宝镇之,其数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献焉:一曰玄黄,形如笏,长八寸,有孔,辟人间兵疫……”[21]4相对于中原,南方楚地是边缘,更偏远的是西北、西南乃至域外。《酉阳杂俎》还称波斯国出产安息香树,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烧之通神明,辟众恶。”[21]177通过海上和西域进入中原的各种香料,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即具有解毒祛疫功能,在年深日久的朝贡体系下,难怪明清写解毒疗瘟的辟邪物多外来。元代张存眇一目,遇巧匠安一瓷睛如真,后回杭言于“藩中”获圣铁辟兵,“作法撒沙布地,噙铁于口,刀刃不能伤。”[34]
国外民俗学家指出,神物(fetish)一词已用得太滥,“这种神物不管是什么东西,它的受珍视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作为某个精灵的容器……神物作为生命和财产的保护物,在灾厄降临时发出警告,并对作假证者、非法入侵者、窃贼、奸夫以及秘密的仇敌施以惩罚。”[35]严耀中先生指出,佛教贴近民间必然会出现些负面东西,世俗化、普及化同时也减退了其严肃性。如江南一些祠庙主供的是各类杂神而非佛像,僧侣掌管久了模糊了其与正式寺院的界限。[36]就狭义说神物带有辟邪、保护性功能,这支撑了广义上的指称,增强了杂糅、泛化趋向。但“辟兵宝物”母题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上述论断,其在军事与宗教实践层面的超常表现正是对此共识的有力反驳,展现出传统辟邪文化浸染中的辟兵宝物,具有更强的超物质存在性。
三、辟兵法术与辟邪符咒的世俗化
外来佛教文化,非常关注辟兵术与辟兵符咒,在法术、斗法场面的描写中,作为佛教征服本土大众的舆情宣扬着眼点,世俗性的一面已现端倪。丰富生动的中古汉译佛经,以其文学魅力和众多相关母题,卓有成效地丰富了辟邪文化,从而也补充扩展了辟兵宝物叙事及辟兵符咒的表现理路。
其一,古印度文献中,妻子贞操多作为其夫的辟兵法宝,暗中护持。《湿婆往世书》称雪山神女向毗湿奴告知水持恶行,让其变成水持模样去破坏其妻婆林达的贞节,毗湿奴用法力达到目的,几天后婆林达知错,怒而诅咒:终有一天会有苦修人也如此去引诱你妻(果然罗婆那变为苦修人抢走了悉多)。婆林达失贞,其夫水持便被湿婆杀死[37]。于是贞节就成为一种辟邪物。等级森严的古印度,妻为夫之附属品,存在价值就在于丈夫的专属权,专属权失去就意味着妻子价值消失,便意味着丈夫有效控制力丧失,存在价值与精神力量丧失。
其二,密教法术中多辟兵符咒。唐代天竺僧菩提流支所译《五佛顶三昧陀罗尼轮王经》称:“若有军将及诸兵众敬信斯咒,亦令书写,持系旍旗及佩头臂,往他军阵。皆自臣伏,互不残害。何以故?以诸如来力加持故。”又波罗颇蜜多罗所译《宝星陀罗尼经》卷二云:“斗战时,应悬此经置自幢头。以经力故,彼怨敌王所有兵众,自然退散。”阿质达霰译《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也有:“若纸或树皮写密言,头戴,辟兵。”因而有理由认为:“后世各种秘密宗教及帮会如红枪会、义和团等所谓‘刀枪不入’的符咒盖渊源于此。”[38]而佛经、符咒等辟兵宝物的构成除了佛教本身无上法力,实施中往往还融合文字崇拜,这在中土影响更大。
其三,佛经所载辟邪信奉还有镜、剑类法器,与道教神物崇拜互动,甚至因佛教异域特色而增力。《西京杂记》载宣帝被收:“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印度)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释慧皎《高僧传》写宝志“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东晋《佛说灌顶经》称:“佛告普观菩萨摩诃萨:若后末世,遭灾祸者,为诸魔魅之所伤犯,当净身、口、意……以青铜之镜照耀五方,使诸魔魅不得隐藏其形。”《楞严经》也有:“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净心诫观上曰:“今唯使汝净除业镜客尘曀等。见汝身中少分佛性。”这都说明古印度镜子神话随佛经传入,直接影响华僧[39]。隋代智顗《摩诃止观》指出时媚(即按不同时辰出现的精怪)扰乱修行人,防治办法即包括辟邪宝镜,“三转即有三十六,更于一中开三,即有一百八时兽。深得此意,依时唤名,媚当消去。若受主稍久,令人猖狂恍惚,妄说吉凶,不辟水火……治时媚鬼者,须善识十二时三十六兽,知时唱名,媚即去也。隐士头陀,人多畜方镜,挂之座后,媚不能变镜中色象,览镜识之,可以自遣。此则内外两治也。”[40]镜剑这一功能还常连用。张邦基《墨庄漫录》引《金华神记》称金华神为女子,吴生惧而拿出剑、镜二物,女曰此剑镜,精鬼则畏,“昔《抱朴子》尝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41]的确,《抱朴子·内篇·杂应》讲辟五兵法属道教法术,《登涉》介绍入山辟猛兽:“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此物(大鼋)能作鬼魅,行病于人。吴有道士戴昞者,偶视之,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良久,大鼋浮出不敢动,乃格煞(杀)之,而病者立愈。”[2]313褚人获《坚瓠续集》还将辟兽、辟百邪与辟水综合:“山行,念‘仪方’二字,可却蛇虫。念‘仪康’二字,可却狼虎。念‘林兵’二字,可却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帝’,可避恶(噩)梦。赌博时,念‘伊谛弥谛,弥羯罗谛’,万遍,则赌博必胜。又渡江河者,朱书‘禹’字佩之,免风涛。”[42]第十五册,360后世辟兵宝物还同神秘崇拜结合,陆粲《庚巳编》载神龙辟兵,都指挥平安追燕王运槊将及,“忽空中有黑龙,舒爪掣其臂,安马跪于地。安知天命有在,叹息收兵而止……”[43]与前引小说写赵匡胤危时顶出赤须火龙原神互证。
“辟尘珠”,揭示出受北方扬尘天气粉尘威胁,俗信宝物超越宗教转向世俗化生活,即“生态一体”理念之于辟兵言说的形象体现。久居华北干旱地区的纪昀确信“辟尘之珠”,言其外舅马公亲历:“福隆寺鬻杂珠宝者,布茵于地(摆摊),罗诸小箧于其上。虽大风霾,无点尘。或戏以囊有辟尘珠。其人椎鲁,漫笑应之,弗信也。如是半载,一日顿足大呼曰:‘吾真误卖至宝矣!’盖是日飞尘忽集,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44]民国学者研究乡间习俗称,遇雷可将女人裤脱下顶头上,雷公若遇裸女便乱滚如雄鸡,乡愚相信春画辟邪功效同于《易经》,“至其内容,无论是经书,是春画,倒不注意。”《韵鹤轩集》载帝王古墓中常有春画陪葬,“盖置于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画春情,亦似‘厌胜’,恐蛟龙侵犯之也。由是言之,春宫秘戏,其传最古,今人置春画于皮衣箱内,谓可避虫,其亦厌胜之意欤!”[45]
辟邪称得上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中世纪欧洲也曾盛行辟邪文化。如所谓女巫惧铁:“女巫和铁的关系,和妖精及家神一样,属于同一范畴,铁的武器和制品使它们恐惧……”[46]圣·奥古斯丁即从不怀疑奇迹是通过魔法产生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像其他出色的前任一样完全接受了魔法具有威力的思想,他以预言术来对待魔法与奇迹间的区别:对他来说,魔法是通过药草及其他实物实现的,它利用了图形、文字、蜡像、礼仪和星座。”[47]在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看来,魔法威力的确存在,但需要药草、图像、文字等辅佐物才行得通。华夏辟兵宝物的救护功能,也必须有浓厚的辟邪文化土壤及能激发更多功能的外来文化触媒,三者结合才能确保辟兵宝物母题书写,熔铸丰厚的文化内质。
明清辟兵宝物母题具有强大的文化吸附功能,借助文本叙事策略与艺术审美功能,母题生成了超越现存的抵御与救助功能。
其一,所谓辟兵等,实乃一种明清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惯用的“史诗手法”。这种模式化的超验想象,使故事的叙述进程得以超越现实存在逻辑地推进。超常物的介入,构成原有思路的转折点和新思路的生发点。且文本与现实生活互动生发借鉴创新,形成超常态精神力量,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其二,明清小说中的辟兵母题,以神物崇拜为核心,往往在英雄叙事中遮蔽、弥补英雄的凡人弱点,这些弱点既然是凡人所难于避免的,就需要用超现实的手段来填充。普罗普揭示,某些工具崇拜是由于人的努力被忽略所导致,随着工具愈益完善,“最初通过动物的某个部分附在充当相助者的动物身上的巫术法力现在转移到了物件上。人们很少看到自己的努力,而更多看到了工具的作用。这样便得出了一种观念,即工具之所以好使,不是由于人的努力(工具越完善,花的力气就越少),而是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神奇性。于是就得出了工具无须人操纵、工具能代替人的概念。工具此时被神化了。”[48]而辟兵母题,实际上也是在显示正面英雄之弱点的同时,烘衬邪派对手的非同寻常,若非辟兵神物则英雄难逃血光之灾。凡人英雄由此拥有被上帝选中的神奇经历,使接受者在可容受的心理距离中,审视拥有神性的凡间英雄,在理想的不远处体验文学形象的神秘魅力。
其三,辟兵神物及其相关法术,难得地呈现英雄半凡半仙或凡人的“仙性”身份,成为该主人公仙师佑护的法宝,也是确证仙凡特殊关系、保持联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半人半仙的英雄生存于仙凡交界地带,是世俗社会伦理精神与理想社会愿景的结合体。上帝借超凡英雄传达旨意,世人通过超凡英雄窥视上帝意图,殊途同归,修正和构建现实社会伦理,彰显正义之精神。
其四,该母题属“英雄功业”表现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被置放在英雄建功立业征程的必经之“历险”,往往是“非一次性”的。在开放性的故事演进中,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理想化社会伦理精神得以生成、确立。辟邪服食,现实中也常被应用。如明清华南海盗为鼓舞士气将火药掺酒中喝下,脸膛发亮、眼睛发红状投入战斗:“战斗打响后,他们还不断往身上洒大蒜浸渍的水,以此作为一种挡避枪弹的护符。”[49]虽然医学上看,海盗们的表现是中毒征兆。
早期本土人类学家指出,有史以来文明民族文化也还有与史前民族无甚差异处:“他们的战争、迷信、魔术、宗教、婚姻等事,也常见有原始的色彩……而所谓汗牛充栋的文明典籍中也尽有野蛮的原料为人类学家所欣赏。”[50]充满想象力与审美意味的辟兵宝物母题,暴露出不仅华夏古人控制异空间力不从心,以及应对现实灾难的无能为力与恐惧感,需要麻醉才能消解。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辟兵宝物源于宗教巫术的辟邪法术的生活化实用化趋向,当归功于文本叙事中辟兵防御功能神奇化扩大化。这一想象中的功用,正折射出生命个体借助宗教力,应对战争、水火瘟疫等危险的生存模式。战争是社会变动的现象,是瘟疫、饥饿等循环、叠加灾难的渊薮,辟兵宝物功能的世俗化延伸也是与灾难共生的包容心态之体现,变宗教消极避灾转为入世的积极抗灾。二是,宝物与英雄建功立业的密切关系,也从一个角度折映出古人借重生态系统的真实意愿,虽然仅是部分地、工具实用性地肯定存在物的生命价值。文学艺术中诚然在构建与物共生境界,但重视辟兵宝物,则无疑成为视科技改良为“奇技淫巧”传统的一股逆流,在文化的自洽与傲慢中,展示出接受现代性思维的动态,文化的内生因素中增加了新动力。
-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研发投入、企业竞争力与股权资本成本
- 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共同体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国民教育政策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