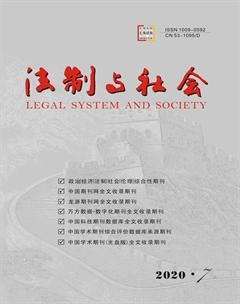论家事纠纷的仲裁
关键词 家事仲裁 家事纠纷 可仲裁性
作者简介:张小雨,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法、法律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30
仲裁是一种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公元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将纠纷交予一位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这位裁判者即为仲裁员。有西方学者曾将仲裁员视为“予民众以‘答案的圣贤之人”。 时至今日,仲裁被广泛运用于商事活动,成为商事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但家事案件的仲裁却较为罕见。我国《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不能仲裁,从法律上排除了将家事案件付诸仲裁的可能。但是,罕见并非不可,综观世界各国,当代不乏家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省都允许当事人运用仲裁解决部分家事案件。
一、家事纠纷的可仲裁性分析
(一)仲裁的本质特征
从字面而言,“仲”指“居中”,“裁”指“裁判”。《现代汉语词典》将“仲裁”解释为“争执双方同意的第三者对争执事项作出决定”。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仲裁比诉讼更为古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和古巴比伦时代的犹太人记事中都有第三人居中裁断的记载。有人认为,仲裁最古老的渊源是公正,起源于村庄中遇到纠纷时请年长者决断。在古代中国,族中长老对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争议作出公断,是长期以来的民间习惯。如果当事人不服从第三人的裁判,则必须按照族规予以处罚。有学者认为,这种自发产生的请与争议无关的第三者公断的实践,就是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雏形。
可见,仲裁的基本理念是第三方裁决:争议双方当事人共同同意邀请一位中立第三方成员,即仲裁员,来帮助他们作出决断。 在国家和国家法产生之前,作为裁判者的第三人进行裁断时依据的是公正合理的原则,因此早期实践中选择仲裁员的要求通常是德高望重、处事公道。
国家产生后,法院經历了从排斥仲裁到欢迎仲裁的转变,二战后更迅速放宽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当代,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普遍认可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仲裁的终局性和约束力是其区分于调解等其他ADR方式的重要特征。
但是,综合比较诉讼、仲裁、调解等第三方参与的争议解决程序,裁决的约束力只是仲裁结果的表面特征,根本区别在于当事人是否自愿引入第三方以及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结果是否具有决定权。正如齐美尔所强调,当事人双方在仲裁中放弃了自己对于争议解决结果的最终决定权,争议被提交予仲裁员意味着当事人从仲裁伊始即信任其裁决比其他任何决定形式都更加客观。 仲裁的基础和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其本质是当事人将争议事项的决定权让与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人。仲裁裁决的约束力和强制效力只是国家出于利益和秩序的考虑,对当事人自愿请求第三人作出决定的自由意志的确认、尊重和支持,只要这种自由意志本身不违法。
(二)家事争议的属性与可仲裁性的界定
仲裁是私法意思自治在程序法上的体现,但意思自治绝非无尽扩张、无所限制。在现代国家,法律对于仲裁事项的范围规定就是对仲裁领域意思自治的一项限制。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指依据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可以进行仲裁的争议事项的界限。
一国对于可仲裁性的规定与本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利益等国情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是本国公共政策的体现。有学者认为,可仲裁性的法理基础在于国家在主权辖区内对合乎本国公共政策的利益的保护。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在实现正义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中,国家依托于法律承担着确保社会公正运行、保护群体性的公共利益的责任。因此,国家必须对仲裁这种“私人程序”的运行界限予以规制,通过将涉及公共政策的争议排除在可仲裁性事项的范畴之外,限制私权的行使,保护影响广大民众的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确保社会有序、良性运转。
对于可仲裁性的界定标准,学者有不同分类,但大多认为只有具有可诉讼性、可补偿性和可和解性的争议才具有可仲裁性。 传统上国内学者认为,婚姻家庭争议有强烈的人身权属性,即使婚姻家庭中可能包含财产关系,也不能与人身关系相分离,因而婚姻家庭争议不具有可补偿性。 此外,婚姻家庭关系有其社会属性,涉及到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应当由司法机关予以保护。故而多国立法例和我国《仲裁法》均排除了婚姻家庭争议的可仲裁性。
家事争议具有人身和财产两方面属性,其人身属性体现为婚姻关系解除、亲子关系确认、子女监护权确认等法律状态的改变或法律事实的确认,无从纳入仲裁调整范围殊无疑义。但涉及财产关系的争议是否一定不可仲裁呢?笔者认为,涉及财产给付内容的扶养、离婚财产分割等争议可以与人身属性争议分割,单独进行仲裁。在婚姻家庭实体法中,现代夫妻财产制已经确立约定先于法定、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原则。与此相应,在程序事项上尊重夫妻意愿殊无不可。以离婚财产分割为例,财产分割问题虽然由婚姻关系的解除所引起,但独立于离婚事项。夫妻或伴侣彼此之间的财产争议主要牵涉双方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其自由意志、允许当事人将决定权交予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人不会对社会整体的公正有序运转造成影响。诚然,家事争议当事人之间客观上可能存在强弱差异。法院可以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程序以及撤销程序中,加强对裁决的实质审查,以维护弱方当事人的利益。
(三)涉及儿童的家事纠纷不可仲裁
孩子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多家事争议都关涉到孩子的利益。在当今的主要家事仲裁实践中,澳大利亚和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不允许涉及儿童的争议提交仲裁,而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部分省允许仲裁儿童抚养争议,但法院保留对于仲裁裁决的实质审查权利。笔者认为,如果一项争议涉及到儿童的利益,无论是从第三人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考量,该争议都应当被排除于可仲裁事项之外。
从第三人利益角度出发,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来源于父母双方,儿童没有在仲裁程序中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也没有将与己有关的事项的决定权交予仲裁员。从理论上而言,仲裁的效力仅止于仲裁当事人,即父亲和母亲,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事实上,每一个涉及儿童的争议解决结果都将影响儿童的利益和未来生活。允许一个没有经过儿童同意的程序——仲裁——来作出影响儿童利益的裁断,无疑是违反仲裁本质的。
就社会公共利益而言,保护儿童就是保护社会的未来,有助于儿童最佳利益的实现是处理家事争议的一项原则。即使是仅涉及金钱给付的儿童抚养费等争议,争议解决的结果都直接关系着儿童的未来。儿童的利益是否实现最大化保障关涉到儿童能否健康成长,关涉到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在涉及儿童的家事争议中,儿童利益必须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不能采取私力救济方式取得有拘束力和强制效力的结果。
二、澳大利亚家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澳大利亚在家事领域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均较为完备,在家事纠纷解决方面也确立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澳大利亚的主要家事法律渊源是1975年通过的《家事法》(Family Law Act 1975)。经过30年的不断修订和发展,2015年10月30日生效的最新版本“1975年家事法”已经有29章约180个条款 ,形成了完善的家事专门法律制度。
(一)家事仲裁制度在澳大利亚的发展
家事仲裁制度在澳大利亚家事立法中的确定始于1991年《法庭(调解和仲裁)法》(1991年第113号法案,以下称“1991年法案”)。依据该法案,原家事法第三章后面增加了题为“调解和仲裁”的第IIIA章。根据第IIIA章第19D-19G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将争议付诸仲裁,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在没有取得当事人合意的情况下将部分争议转介仲裁庭裁决。由于法院强制转介仲裁涉嫌违宪,且1991年法案关于家事仲裁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家事仲裁制度在实践中成为一纸空文。在2000年和2001年的家事法修正案中,澳大利亚取消了非合意的法院强制转介仲裁,除当事人直接合意仲裁外,法院仅可以在取得全部当事人同意后将符合规定的案件转介仲裁。2000年的修正案还为家事仲裁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案,据此确定的家事仲裁制度延續至今,成为澳大利亚现行家事仲裁原则。
2006年5月22日,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2006年家事法修正(共同承担父母责任)法》(2006年第46号法案,以下称“2006年法案”),该法案第II章确立了新的 “非诉讼家事服务”(Non-court based family services)制度,较为完善和系统地囊括了主要的非诉讼家事争议解决方式。2006年法案通过后,新的家事法在第II章第四节和第IIIB章第四节分别规定了家事仲裁制度和家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根据修订后的1975年家事法第10L条,可诉诸仲裁的争议包括第VIII章、第VIIIA章、第VIIIB章和第106A条项下争议,即涉及伴侣财产、伴侣扶养、婚前或婚内财产协议以及法院令的执行等内容的家事争议,但已经过法院批准的伴侣扶养协议和涉及子女抚养的协议不得仲裁。1999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的另一项家事法修改法案 赋予家事仲裁裁决以强制执行力,即现行1975年家事法第13H条——经法院登记的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二)澳大利亚家事仲裁裁决效力
澳大利亚家事仲裁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仲裁裁决并非当然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根据1975年家事法第10L条第1款,仲裁被定义为“争议当事人将论点和证据展现予一位仲裁员,并由该仲裁员为解决争议之目的作出决定的一项程序”。在该定义中,仲裁员所作出的是一项“决定”(decision)而非“裁决”(awa rd)。仲裁员作出决定后,任一方当事人均可以根据第13H条在有管辖权的法院登记该决定,从而赋予其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只有经法院登记的仲裁裁决,才可以被法院复审或撤销。澳大利亚家事法委员会在2007年的一项关于家事仲裁的讨论文件中认为,尽管家事仲裁员的决定没有当然的约束力,但家事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诉讼程序的本质差异在于争议当事人能否合意决定争议解决程序事项和争议解决结果:家事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只能合意决定程序事项,而争议解决结果完全由仲裁员独立决定。
尽管澳大利亚设立了相对完备的家事仲裁机制,但实践中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解决纠纷的比例仍然极低。澳大利亚家庭法院2006年的一项非正式调查显示,204个被调查案件中,仅有1个案件的当事人参加了仲裁,13%的当事人参加了类似仲裁的其他程序。与此相反,82%的当事人认为自己现阶段尚未做好仲裁准备。
三、美国家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美国《统一仲裁法》没有将婚姻家庭争议排除于仲裁事项之外, 原则上只要仲裁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家事争议就可以提交仲裁庭裁决。北卡罗来纳州在Crutchley v. Crutchley案 中确认了家事争议的可仲裁性,南卡罗来纳州在Messer案 中确认如果分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符合《统一仲裁法》中关于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规定,则仲裁条款有效。有关赡养费和伴侣扶养争议的仲裁都被美国法院予以认可。
但是,如果争议涉及儿童,为儿童利益之考量,并非所有相关争议均可仲裁。1993年纽约最高法院的Glauber v. Glauber案 排除了儿童监护和探望权争议的可仲裁性,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法院也曾作出类似裁判。即使是涉及儿童抚养争议的仲裁裁决,法院亦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因为法院对于儿童抚养有“不可被[仲裁庭]代表的特别监管责任”。如果裁决没有实现儿童最佳利益的保护,法院可以不尊重或修改仲裁裁决。
成文法方面,美国部分州颁布了专门法案调整家事仲裁程序。例如,北卡罗来纳州1999年颁布的家事仲裁法案确认,除儿童抚养、儿童监护和离婚本身的争议外,当事人可以将与婚姻有关的其他任何争议提交仲裁。佐治亚州2007年第201号参议院法案将家事仲裁纳入法典第17章“家庭关系”项下。依据该法案,当事人可以将除儿童抚养、儿童监护和离婚本身争议以外的其他婚姻争议提交仲裁;无婚姻关系的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后签订书面协议将儿童监护、儿童抚养等相关争议提交仲裁,但如果相应仲裁裁决没有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法院有权撤销该裁决。除各州立法 外,美国仲裁协会和美国婚姻律师学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家事仲裁的规则,发展了家事仲裁实践。
四、其他家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除魁北克省以外的加拿大各省均允许当事人将家事争议提交仲裁。例如,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的《仲裁法》都没有排除家事案件的可仲裁性。安大略省的家事仲裁在2006年以前由《仲裁法》和《家事法》共同规制。2006年,安大略省通过了《家事法令修改法案》(Family Statute Law Amendment Act,以下称安大略2006年家事修改法案),建立起一套新的较为完备的家事仲裁制度,排除了以宗教规范等非加拿大实体法为准据法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效力。2013年以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没有关于家事仲裁的立法,但是在实践中已出现适用《商事仲裁法》(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的家事仲裁案例。 该省于2013年修改仲裁法案,将《商事仲裁法》更名为《仲裁法》(Arbitration Act),家事争议被正式纳入可仲裁爭议范围。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地区,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规定“仲裁协议”系指同意将现在或未来的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无论该争议是否为合同性争议。该法第1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争议的解决方式,仅受制于保护公共利益之必要。虽然法律没有限制家事仲裁,但是传统上认为仲裁法规定的仲裁不适用于家事争议,且该立场在司法部2008年的一份书面答复议事录中得到申明。20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有所转变。当年通过的家事程序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运用非诉讼的ADR方式解决家事争议,并要求法院促进当事人使用ADR方式解决争议。 英国家事法仲裁员协会(Institute of Family Law Arbitrators)参考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实践,于2012年建立家事仲裁体系,为家事案件当事人提供经济和财产争议仲裁,但不包括任何与人身、儿童照顾或亲子关系、破产等有关的争议。
五、结论
从前述分析的国家实践可知,目前开放家事仲裁的国家和地区中,与财产权益有关的赡养费、伴侣扶养等纠纷均被纳入仲裁范围,但各国对于离婚、监护等与人身权益相关的纠纷和涉及到儿童的纠纷持谨慎态度,仅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全面允许各类家事纠纷提交仲裁。即使立法允许涉及人身权益或儿童利益的纠纷进行仲裁,法院也大多保留了对于仲裁裁决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利。理论上,允许仲裁解决仅涉及夫妻或伴侣双方与财产给付有关的争议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不会影响社会健康运行,只要法院对家事仲裁实施严格的司法监督以保护弱方当事人和儿童利益。诚然,对于家事纠纷的当事人而言,仲裁程序如何便捷有效地运行以及仲裁裁决的执行都是当事人选择家事仲裁后将面临的难题。尽管如此,仲裁作为一种已在商事领域受到广泛认可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未尝不可为家事领域的纠纷解决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可能性。
注释:
Bloch, R, ‘Arbitration as a career, in Max Zimny, Ann Harmon Miller, Christopher A. Barreca (eds), Labor Arbitration Development-a Handbook, 1983.
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英]西蒙·罗伯茨,彭文浩.纠纷解决过程: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第二版)[M].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李广辉,王瀚.仲裁法[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宋朝武主编.仲裁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宋连斌主编.仲裁理论与实务[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Simmel, 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 Wolff,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151.
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王德玲.争议可仲裁性问题探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6(7),第57-58页;乔欣,李莉.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上)[J].北京仲裁,2004(2),第37-41页.
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 12-13页。另参见饶传平,焦洪涛.可仲裁性理论探微——意思自治及其限制的视点[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第48-49页.
本文中使用的“1975年家事法”均指修订后的现行版本。
Section 5, Courts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Act 1991, No.113 of 1991.
Family Law Amendment Bill 1999.
Australian Family Law Council, The answer from an oracle: arbitrating family law property and financial matters, Discussion Paper, published on May 2007, para.4.22.
美国《统一仲裁法》明确排除了劳动争议的适用,除非劳动合同载明合同争议依据《统一仲裁法》进行仲裁。
306 N.C. 518, 293 S.E.2d 793 (1982).
333 S.C. 391, 509 S.E.2d 486 (1998).
192 A.D.2d 94, 600 N.Y.S.2d 740.
?0-42, the North Carolina Family Law Arbitration Act.
目前,美國密歇根、科罗拉多、密苏里、新泽西、新墨西哥、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等共约17个州颁布或修改了成文立法以调整家事仲裁程序。See Walker, G., 2006 Revised Handbook: Arbitrating family law cases under the North Carolina Family Law Arbitration Act as amended in 2005, Volume 1, 2006:7; Walker, G., ‘Family Law Arbitration: Legislation and Tren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21 J. Am. Acad. Matrimonial Law. 521 (2008).
Pawlowski, 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Hague Convention child custody disputes, Family Court Review, 45 Fam. Ct. Rev. 302.307.
Mcgill, S., ‘Family arbitration: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olicy, 21 J.L. & Soc. Poly 49 (2007):50.
Morris, C., ‘Arbitration of family law disputes in British Columbia—paper prepared for the Ministry of Attorney General of British Columbia, 2004:11.
De Jong, M., ‘Arbitration of family separation issues—a useful adjunct to mediation and the court process, 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 17 Potchefstroom Elec. L.J. 2355 (2014):2369-2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