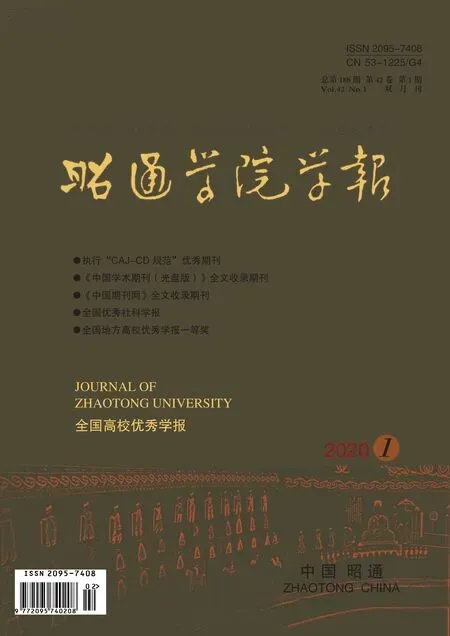方志兴修与国家认同
——明代乌蒙山地区地方志修撰考略
胡 超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一、明代乌蒙山地区行政区划建置及其区域特征
乌蒙山脉坐落于贵州高原西北部和滇东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横跨今贵州毕节、六盘水、黔西南,云南昭通、曲靖、昆明北部一带,长时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元代以前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多实行“统而不治”的“羁縻”政策,元朝平定云南后先后在此设立“乌撒乌蒙宣慰使司”(辖乌蒙路、乌撒路、东川路、芒部路)、“曲靖宣慰使司”(辖曲靖路、普安路、普定路)等土司机构,以流官为正,土官副之。明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命征南将军傅友德率蓝玉等人领十四万大军平定云南,分胡海洋一支偏师由永宁进兵以进攻攻乌撒等部,白石江大战击败元军主力后,傅友德又自率大军“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宁之兵”[1]8003,与胡海洋等人合军一处击败了乌撒等部彝族土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乌撒等部后,以元东川路、芒部路、乌撒路、乌蒙路、普安路、曲靖路、仁德府分置东川军民府、芒部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乌蒙军民府、普安军民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均属云南。十六年因诸部叛乱,将芒部、乌蒙、乌撒改属四川,十七年将东川改属四川;二十一年普安军民府被削,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设普安安抚司,永乐十三年革去,改设普安州,隶贵州布政司;成化十三年革去寻甸军民府,改设寻甸府。其中寻甸军民府改流后由流官管理;普安州、曲靖军民府由流官主事,其治下均有土通判、土知州等土官名目;东川、乌蒙、乌撒、芒部四军民府由土官主事,流官为佐贰;贵州宣慰司则不设流官。整个明代虽然在乌蒙山区进行了一些改土设流的工作,但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处于土官的管理之下。
而且乌蒙山区的土司“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2]2889-2890。其关系错综复杂,时而互相仇杀,时而联合叛乱。由于该地区分属三省,作为中间协调者的国家力量—川滇黔三省镇巡官—往往也各执一端,难以协调,多次产生重新调整行政区划隶属的大讨论。
总而言之,明代的乌蒙山区虽被划归三省,但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因其少数民族土司地区的特殊性使得其区域特征明显,划分省域而治并未割裂乌蒙山区的整体联系。
二、明代乌蒙山地区方志考略
方志修撰作为边疆文化逐渐向内地靠近的一大参照因素,其修撰的次数可以看到其与“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明代方志考》等志书目录及《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嘉靖《四川总志》《正德云南志》等古方志中序跋和引用情况的梳理①,可以看到乌蒙山地区明代至少修撰了以下十四部方志,其中部分志书有存目而无作者及年代,但其修撰的时间段亦可就引用情况和存目情况看出。
(一)明代乌蒙山地区现存志书情况
1.六盘水地区
永乐《普安州志》十卷,修纂者不详,永乐十六年(1418年)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胶卷版[3]809。
嘉靖《普安州志》十卷,高廷榆修,宁波天一阁藏有嘉靖刻本,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以天一阁本为底本影印了该志,2006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辑》以该本收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及《明代方志考》载其成书于嘉靖二十八年,卷首有蒋宗鲁序一篇,并附永乐旧志序。蒋宗鲁所作的《嘉靖普安州志·序》:“嘉靖昭扬赤奋若之岁,普安志成。”[4]3按此说则该志成于嘉靖癸丑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若按志叙中称“旧志成于永乐十六年,距今一百三十年矣”[4]10上,则刚好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但志叙中虽然提到了该书纲目体例,但并未明言何时成书。且其科贡年表记至嘉靖乙丑年,即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4]37上,则天一阁本成书更在其后。
2.曲靖地区
《寻甸府志》二卷,王尚用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成书。卷首有王尚用自序。宁波天一阁存有嘉靖二十九年刻本[3]827
(二)未见存世的乌蒙山地区明代志书
据上列志书来看,乌蒙山地区现存明代的志书资料远远算不上丰富。但现存志书的状况远远不能代表明代这一地区志书修撰的真实情况,通过对明代历次修撰的贵州、四川、云南三省的通志、《大明一统志》《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以及明清两代川黔边界各地志书的序跋记载和引用的梳理,可以看到除了现存的3种志书外,还有一些明代修撰但久经岁月而亡佚的志书存在。除《明代方志考》已有考证出六盘水地区的景泰《普安州志》、万历《普安卫续志》;曲靖地区的《陆凉州志》《马龙县志》外,[5]415,423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地区的七部方志。
1.东川区
《东川军民府府志》,《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东川军民府”条载东川风俗“贸易为业”,下注:“府志:‘夷人有一种,其一曰僰人’”[6]3237。《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七》风俗条完全照抄《大明一统志》,其后的《万历四川总志》论及东川、乌蒙、乌撒、芒部四军民府几乎完全照抄《嘉靖总志》,此处不论。至清初东川改流时该府志已亡佚,乾隆《东川府志》序说道:“滇蜀黔隶土人之地皆无志,不独东川也。”[7]1清初时修志之人已不知有此府志存在。按东川在明洪武十五年设府,十七年改军民府,当修于明洪武之后。考之于《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条,确有《东川军民府志》[8]230,成书年代当在正统《文渊阁书目》成书之前。
2.毕节地区
《乌撒军民府志》,《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乌撒军民府”条载乌撒形胜“前临可渡,后倚乌门”,下注出处:“郡志”[6]3242,风俗“刀耕火种,不事蚕桑,病不医药,惟祷鬼神”,下注出处:“郡志”[6]3242。当地在元代已有修撰志书,元李京著有《大德乌撒志略》四卷,《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六》记《大德乌撒志略》:“《方舆纪要》引‘元志’云:‘乌撒山崖险厄,襟带二湖,羊肠小径十倍蜀道’,即京书之文也”[9]554上。按该句在《大明一统志》中有引用,并注明出处均为‘元志’。与同书所注的“郡志”显然不是同一部书。就乌撒、乌蒙等地设府的时间来看,郡志应修于明代《大明一统志》成书之前。考之于《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条,有《乌撒军民府志》[9]230。则该书成书更在正统《文渊阁书目》成书之前。
《乌撒卫志》《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乌撒军民府”条载乌撒风俗“荷毡披毳”,下注出处:“乌撒卫志”[7]3242。《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乌撒卫”一条载乌撒卫形胜“山高地险”,下注:“乌撒卫志:‘界于诸夷之中,山高地险,实西南要厄之处’”[10]173。由此来说该书应当在弘治前就已经成书。按《嘉靖贵州通志》对《乌撒卫志》的引用,此时《乌撒卫志》应当还流传于世。《万历贵州通志》中已不见引用。《文渊阁书目》中亦不见收录此书。
万历《毕节卫志》一卷,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六》:“《万历毕节县志》一卷,明高少室、韩襟江撰。”下文说道:“罗英《毕节县志序》云‘毕志,明万历中高少室、韩襟江先生所撰’”[9]555上。按万历时毕节有卫无县,故而不可能存在“县志”。以民国《贵州通志》所引的史料源头来看,高、韩二人编毕节志的说法最早是出自清代罗英的《毕节县志序》,考之,该序只说“毕志”,未言“毕节县志”。又查《道光大定府志·旧志叙录》,则明言“万历毕节卫志一卷”[11]162上。则记为万历《毕节县志》是民国《贵州通志》之误。《毕节县志序》中提到的“毕志”,应当是万历《毕节卫志》。
《贵州宣慰司志》②。《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载贵州宣慰司风俗:“病不识医药,披毡衫以为礼。”下注:“俱贵州宣慰司志”[6]3934。《明代官修四种贵州省志考评》和《贵州方志考略》均认为《贵州宣慰司志》修于元代③,考之于《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条,有《贵州宣慰司志》[9]230。既称“新志”,又与《乌蒙军民府志》等志书同列,当修于明代正统以前。
3.昭通地区
《芒部军民府志》《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七》载镇雄府风俗“性劲而愚,俗朴而野,男业耕稼,妇绝粉黛,子日贸易。”,下注:“府志”[12]274上。《大明一统志》中所引的同一句话下面注解为“以上俱郡志”[6]3239,可以发现“府志”“郡志”实为同一部书。考之《文渊阁书目》“新志”条,有《芒部军民府志》。按明代府有称郡之惯例,而明以前此处未设府,成书当在正统《文渊阁书目》成书以前。
《乌蒙军民府志》《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乌蒙军民府”条载乌蒙府形胜:“龙洞环于左,凉山耸于右”,下注:“新志”[6]3240,《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七》“乌蒙军民府”条引用本句,下注:“本府志”[12]272上。参照各总志和通志中分别用到的“元志”“府志”“郡志”“新志”四种注解。“元志”应是指李京的《大德乌撒志略》,此书《文渊阁书目》和《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均未见收录,《大定府志·旧志叙录》及《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有存目。《嘉靖四川总志》中称的“本府志”在《大明一统志》中被称为“新志”,明代以前该地无府亦无郡,参考《芒部军民府志》的“府志”、“郡志”为一书的例子,《乌蒙军民府志》所引用的“府志”“郡志”“新志”应是同一本志书。考之于《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条有《乌蒙军民府志》,则乌蒙确在正统以前就有府志。
三、方志兴修与国家认同
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政治掌控的不断加深,相应的文化建设也逐步跟进,现代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明代在这些地区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土官承袭与入学挂钩等内容并作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反映出封建中央王朝以传播儒学的方式来加强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志书作为记载一方物产、风俗、政教、山川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历史记忆、保存珍贵文化,促进内地边疆一体化等重要的作用。金燕在研究“改土归流”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时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国家,是国家的一分子,既享受着依靠国家所获得的利益,又承担着国家规定的义务。”[13]63诚然,个人或群体对国家所授予的权力和规定的义务的承认显示出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但普安州和寻甸府两地志书的序中可以使人注意到国家和地方之间认同的另一个层面——国家对地方的认同。
《周礼·地官·诵训》说道:“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14]441上这说明了自古以来,方志作为一地掌故之书,具有向统治者传达地方情形以方便治理的作用。贵州作为边疆之地,“在寰宇西南之极”,明人以为贵州“在古为荒服,入圣代始建官立学……百七十年来骎骎乎齐美华风”,故而增修方志,“以启百代之瞻仰”[15]193-194。而云南则“古沦异域,山经地志皆鲜及之”,志书修撰之后,使得观志者得以知晓云南“昔为不毛之地,而今建郡作邑张官置吏也,昔为旃毳干戈,而今衣冠弦诵也”。[16]
《普安州志·序》亦云“普安军民指挥使司所辖地本西南荒服之表,蛮夷部落,元世始拔土豪吏置官署,顽风暴俗仍习旧污,大略羁縻而已。幸入圣朝,城守屯戍,怀德畏威,而来三十余载,垦田编户,趋事赴功,渐拟于华郡。”[4]5-6其开创之意,甚为明晰。在明人的视野中,西南地区历来是国家控制之外的边疆之地,而在明代将其纳入版图,并且开科取士,教化边民,新修或增修方志将这一百代未成之功业传之后世,以便后世考察明朝在开疆域、设制度方面的历史功绩,并宣扬有明一朝在西南地区的文治武功,彰显出明朝在西南治理历史上的开创性作用。故而泛览西南边疆地区的明代志书,都有意突出与前代的对比而强调其“骎骎向化”“渐拟华风”,以展现出要荒之服逐渐化为内地,由“野蛮”而化为“文明”,凸显出国家力量到来之后当地面貌焕然一新的结果。而寻甸府则“昔为土部而改设流官,涵濡圣朝文化有年矣,礼乐颇垺中土亦久矣,可缺是典而使文献无征于郡耶?”[17]1可见在修志的同时就意味着华夏的中心承认了羁縻之地成为治下之邦,因而要将它的历史掌故记载并纳入华夏整体的文化脉络之中,摒弃了土官制度而直接处于朝廷管理之下的边疆“涵濡文化”、“礼乐垺于中土”,这样的地区值得兴修一部方志来记载中央王朝“变夷为夏”的历史功绩,“改土设流”正是寻甸府方志兴修的一大前提。方志是华夏的文化边缘逐渐向边疆、山地逐渐扩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控制逐渐加深是乌蒙山区地方志修撰的一大重要原因,亦是在日益加深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结果。

图1 乌蒙山区明代方志修撰次数示意图
由上图可看到乌蒙山区明代方志至少有十四部,有九部修于正统以前,仅有五部修于正统后(《陆凉州志》④《嘉靖寻甸府志》《嘉靖普安州志》《万历普安州续志》《万历毕节卫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正统后持续修志的都是长期处于流官管理或初设流官不久的地区。东川、乌蒙、乌撒、芒部四军民府府志及贵州宣慰司志均修于正统之前,这一时期平定云贵的军事余威仍在,且朝廷在这一地区派驻了很多的流官佐贰,修志具有稳固的政治基础。这几个土司地区的方志极大可能是在明初修一统志时各地修志的大浪潮下修撰的。但也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的方志在正统以后就未见新修。从正统时开始,这几府的流官相继被裁撤。[19]122这恰好和方志修撰的时间段不谋而合。可见,代表国家控制力度的流官管理是方志兴修的一大重要条件,方志的兴修体现出中央王朝对新纳入直接管理体系的地区的文化承认。
四、结语
明代的乌蒙山区土司林立,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但从缓慢进行的改土归流动作和方志兴修事业仍然可以看出明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推行国家管理体制的努力。边疆方志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不仅其内容可以反映出中央王朝对边疆认知的逐渐扩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方志兴修本身也反映出了古代华夏中心对边疆国家文化认同的塑造。方志的修撰状况与国家管理力度和对边疆地区的认同是息息相关的:“改土归流”带来的是将边陲纳入国家直接管理体系的需要,而方志兴修带来的是边疆—内地的双向认同。我们无法想象当贵州水西地区没有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时是否能够有足够的人力和组织力修纂一部令大部分志书都“未能望其项背”的道光《大定府志》,当然也无法想象没有道光《大定府志》和道光《遵义府志》的大定府和遵义府能够为梁启超津津乐道并为后世读者所采择摘取。⑤方志在无形中加深了边疆和内地的文化心理联系,促进了地方和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当华夏的边缘不断对外扩展并吸纳更多的族群进入华夏体系时,方志的兴修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注释:
①《中国地方志综录》中载有《嘉靖普安州志》、《嘉靖寻甸府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除此二部外还载有《永乐普安州志》;《明代方志考》对此三部均有著录,并将已佚之景泰《普安州志》、万历《普安卫续志》、《陆凉州志》、《马龙县志》、万历《毕节县志》(即万历《毕节卫志》)收入。见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 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②明代贵州宣慰司治贵阳城,但其地大部分在今毕节地区,故列入.
③见张新民.明代官修四种贵州省志考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2):45-52.史继忠.贵州方志考略[J].贵州民族研究,1979(01):95-101.
④《陆凉州志》修撰者为张星耀,按《乾隆陆凉州志·卷三》“监司”条载有张星耀,同卷载明“监司”始设于万历十九年,故而《陆凉州志》应当修撰于万历以后.
⑤林则徐曾赞道光《大定府志》“编纂之勤,采辑之博,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梁启超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大定府志》、《遵义府志》均列为清代名志。见肖忠生.林则徐与《大定府志》[J].福建史志,2005,(第6期).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