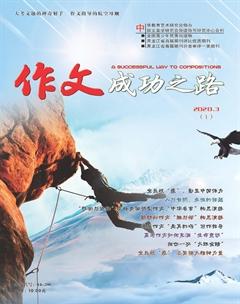高中语文读写深度融合的有效探究
许夏
叶黎明先生指出:以支架为拐杖,以训练为手段,是可以把阅读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写作能力与思维方法的。只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出现了以下一些现象:(1)“以读促写”变成“以读代写”。在高中阅读教学中,部分教师由于对读写结合缺少深刻的认知,导致在高中阅读教学中,过分强调学生的读,忽略了学生的写。还有部分教师认为读的越多就会写得越丰富,不对阅读的书目加以筛选,不对阅读的章法加以讲解,只是让学生广泛阅读。(2)阅读与写作明显脱节。阅读课还是阅读课,写作课还是写作课,没有很好地在课堂上将两者有机结合,做到”在读中写”“在写中读”。(3)读写结合的教学效率低下。部分教师在课堂上虽然设置读写结合的环节,但是缺少可行的教学方法,使得阅读和写作的效率低下。出现以上三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搭建阅读与写作的桥梁,做到深度融合,有效提升。筆者根据学情教情,谈一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读写深度融合的三个有效途径。
一、以读导写——问题导向的到位
读和写相互促进,符合“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课程理念。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能够以读作为主线引导学生,与文本展开对话,用自己的语言解读文本,可以让阅读更加具有方向性,也更到位。
首先,引导学生在自读时会表达感受。在阅读的初始阶段,由于每个学生认知水平和阅读经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教师可以根据这些差异,推荐阅读经典文本,师生共读共商共写,激发意趣。比如。在阅读《我与地坛》时,每位学生在自读完文本后,由于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不同,对文本的感受也不一样。比如:
学生一: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却双腿残疾,这是一种巨大的挫折,但是在文章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对生命的不屈,对生命清醒的认知。
学生二:史铁生把自己化作了地坛里的一草一木,地坛里的那些小虫子,那些蚂蚁摇头晃脑,那些摔倒在地的露珠,是“轰然”的,是发出万道金光的。
其次,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来表达不同。深度阅读,与文本细节对话,与作品对话,与作者对话,意趣理趣的激发会更到位。通常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只会抓住文章写什么,如何写,表达效果如何。很少去关注文本中一些细微点,引导学生质疑,从而让学生表达出个性见解。比如,我们在阅读《老王》的时候,不能将眼光仅仅集中在老王这一人物形象上,也要关注杨绛一家与老王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写出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比如,关注文本中的“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语句,形成了以下见解。
“他蹬,我做”简单的四个字,却表明“我”和“他”的最大不同就是身份、地位的不一样——个是拉车的,一个是坐车的,两个阶层的人。正是引文“我”以这样一种心理和眼光去与“老王”交往,所有的关心都是浮于表面,老王生病了,我却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老王去世了,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始终与老王保持着距离。当愧怍者与被愧怍者具有相当的距离时,愧怍才有价值意义,这也是杨绛要表达的主旨。
由此可知,咀嚼文字,体悟背后的情感,深度阅读,深入理解文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与文本展开对话,走进作者的心灵。同时以“写”的方式也能够强化整体感知效果,读写的深度融合才有到位有效的可能。
二、从读练写——方法体悟的到位
阅读是一种输入,在阅读中,教师如果依托文本,从文本阅读中寻找阅读方法,潜移默化地来带动写作训练,将会得到自出心裁,不露痕迹的效果。
首先,依据文体的结构特点和论证特点进行读中练写。在高中阶段,我们大体会接触文言文、散文、诗歌、小说、论述类、实用类这几种常见的文体。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这几种文体的特点,明晓这几种文体写作的侧重点,然后以典型的例文作典范,引导学生进行写作技法上的借鉴。比如,学习《拿来主义》,引导学生梳理文章的思路,由此可以得出这篇论述文主要是“先破后立”的结构方式,引导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巧妙运用。同时《拿来主义》作为一篇典型的驳论文,可引导学生阅读掌握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比如文章中除了运用“引用论证”和“举例论证”以外,还很好地运用了“比喻论证”让读者仿佛亲眼看到“屏头”“昏蛋”和“废物”三种人糟蹋“大宅子”的样子,形象生动。学生在写作中也可以巧妙地将这种论证方法运用到写作之中。
其次,参考文本的语言特点进行读中悟写。学生只有将优秀作品中的语言文字进行内化,进行有机整合,才能在写作中灵活应用,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比如在学习《今生今世的证据》时,引导学生抓住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和语言特点进行品味,从而体会语言背后的内涵,从而进行自我创作。当读到“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己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学生体会到了刘亮程在写作中,很好地抓住村庄中一些已经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人和事展开,激起了我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刘亮程选取了“草、巴掌大的墙皮……”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在平实的语言中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比如学生在写无锡高三期末试题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了。具体片段如下:
所有渐行渐远的人情温暖中,我最不舍的是那方承载了无数回忆的,已然消失的戏台。
老家的戏台不是什么稀罕物,村村都有。过年时戏班子到各村“巡演”,戏不见得有多好,但邻里乡亲都坐在自己搬来的条凳上,挨着彼此大声叫好。这儿可没什么大戏院跑堂的规矩,渴了就自泡一杯老茶梗,馋了就抓一把旁边人的铁蚕豆,故作气恼地打闹一会儿,又话起邻里家常……
可后来,戏班子越来越少,城里好玩的也多了,交通方便了,戏台就渐渐冷清下来。但人们还是习惯着戏台的陪伴,虽然它沉默无言;村东和村西的乡亲偶尔碰到也会寒暄几句,虽然戏台的沉寂让他们好久未见。
从习作的片段看,学生巧妙地运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的一些小众化的素材,抓住生活中的一些小物件,运用平实的语言,从而表达出戏台的消失,传统文艺逐渐衰落的情感。这种以读促写的方式,很好地为学生的写作提供了方向和方法指导,实现自我创作。
三、抓写促读——思维意识的到位
写作是一种输出,是学生动态思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基本上是:观察——思考——表达。学生按这个思维过程,我们可以有效地进行序列化训练。
首先,可进行“主题式”的读写训练。所谓“主题式”读写训练就是在“主题”主线的引导下,进行读与写有效融合。我们可以围绕某个主题进行写作,依据学生所写的小议题进行文本的筛选、归类,进行有针对性的主题式阅读。比如,学生写“精神归属”为主题作文,形成以下小论题:(1)故园之思,落叶归根。(2)人总在漂泊之中,心总得找一个归属之地。(3)风景无处不在。教师可以围绕这些论题,让学生依据文本进行有针对性地筛选,筛选出《肖邦的故园》《今生今世的证据》《故都之秋》《我与地坛》等四篇文本,然后进行主题型阅读。
其次,进行“微专题式”的读写训练,实现以写促读。比如以无锡期末考试《氧气》为例,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由实到虚,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只会从事物表面的特性写起,导致缺少思辨性。可引导学生阅读曹文轩的《前方》,你会发现曹文轩借助家园实际是阐释人与家的关系,人有着离家的天性但是离家后又想家,难以找到心灵的归属,从而揭示了人生的戏剧性。可借助《前方》的写作思路帮助自己打开思维,形成了“生活中氧气必不可少——人情无处不在——冰冷的枯井缺少人情——有了人情才有人间四月天”的思路。也对《前方》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具体片段如下:
若想活在世界上,氧气,便是不可或缺的。人若想活在社会上,人情便是不可或缺的。人情之于活生生的人,便如氧气一样,无形无感,却又必不可少。
正如赫胥黎于《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乌托邦那样,充满高科技却没有人情。野人先生努力地脱离“野人区”,再来到这个他心心念念的城市,才突然发现了人情的珍贵。
委实如此。正是人情让冰冷的枯井迸发出温暖的泉涌。
如泰戈尔于《飞鸟集》中所记:“纯粹的理性是冰冷的刀锋,直叫握着它的人双手溢满鲜血。”不基于人情之上的理性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好比一座空中楼阁,看似繁华辉煌,可当你想要住进去,问题便出现了。若失去了人情。人与机器又有何不同?
行走人间,不应只有纯粹的黑与白,在光与影之间还应隔有一片灰色地带以供喘息。有了人情,才有了人间四月天。
在高中语文学习方面,教师需要让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得以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做到在阅读中汲取写作的智慧,在写作发挥阅读想象力和审美力,真正实现读与寫两者的深度融合,到位是最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