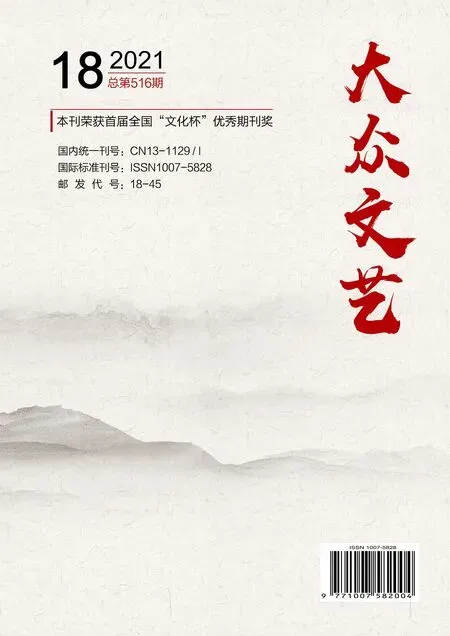姓甚名谁:身份象征与女性写作
张艺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的一种,是社会成员相互区别的符号,是社会的产物。”[1]在公众生活中,名字是个兼有社会性与个体性的概念。社会大众的名字不仅是人与人相互称呼的语言符号,更是研究社会心理与集体意识的重要元素。
女性角色的塑造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而女性角色的名字往往带有作家对于这一角色的一定期许或暗示。在部分文学作品中,同一女性角色往往拥有多个名字——不同的名字代表女主人公在不同时期内各异的精神面貌和身份象征。这类著作中,名字的改变往往带来叙事的转变和人物关系的进一步推进。人物被赋予的多个名字符号,“使得在这部作品中名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得到了发展[2]”,为进一步解构作者未诉诸笔端的弦外之音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女性变更姓名的主动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自身的女权思想萌芽。女性由“默许定义”到“质疑定义”、由“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革命性进步体现出对自身独立身份的追寻与渴求。女性为自己命名,是从男权社会掌控下夺取话语权的一种体现。女性由沉默到着手变革,使得她们有机会不再作为“他者”存在,而试图成为“可以构建胜利、历史、理性”的“话语权的持有者”[3]。
一、“斯巴达的海伦”
《伊利亚特》中,斯巴达王后海伦因容颜美丽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据为己有,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随着配偶关系的变更,海伦的“姓氏”经历了一次改变。自海伦被掳,书中对她的指代由“斯巴达的海伦”变为“特洛伊的海伦”,以此象征女主人公身份的转变。然而,作为故事的导火索,海伦的角色塑造却并不是整篇史诗的中心——正相反,文中对她的外貌和语言描写甚少。全篇着眼宏大场面,对于女性的描写常集中于几位女天神,而对“海伦”的提及只见于决战中的英雄之口,往往一闪而过。海伦这一形象扁平化,表现为“战利品”般的物化存在。
作为读者,假使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发问:海伦是否是自愿随帕里斯离开斯巴达?如果是自愿,她为何执意背井离乡?如果非是自愿,她可曾反抗?她可曾试图逃回?她如何看待这场“由她引起”的战争?历史与文学文本的间隙决定着这些问题注定得不到确切答案。荷马书写的史诗是男性史诗,而对于这个点燃了整片大陆的女性,则在寥寥数笔后弃置一边,人物的叙事目的已经达成。被作者荷马剥夺了的海伦的话语权反映出在古希腊社会下女性无力为自己发声、争取自身命运的处境。她由“斯巴达的海伦”变成“特洛伊的海伦”,姓氏的变化象征着归属权的移交,而这正是那个时代下女性卑下地位的体现,她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选择。文中当斯巴达大军压境时,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提出条件:让帕里斯出城与墨涅劳斯决斗,获胜者拥有“海伦和她的财物[4]”。在两军交战的篇章中,海伦的名字出现数次,均是与“财物”相绑定,实则是古希腊社会将女性物化的体现——女性没有独立公民身份,自身便是“财物”的一部分。
二、“简·爱略特”
比起“简·爱略特”这个名字,其原名“简·爱”更家喻户晓。《简·爱》成书于19世纪中期。孤女简·爱与庄园主罗切斯特先生相爱,然而两人成婚之际,简·爱在得知罗切斯特先生早有妻室后在离开庄园。而“简·爱略特”则正是简·爱在逃离后,为避人耳目随口取的化名。
简·爱改名之举虽出自无奈,但由于是在自身主动意愿下的行为,因此具有了一丝追寻独立身份的意味。女性改变自己的名字,不仅代表割断与过去的关系、寻求新的自我,更代表着对于男权社会强加给自身“身份”的反抗。简·爱对别人说出“我的名字是简·爱略特[5]”的行为实质上是女性重新定义自身的象征。使用一个由自己所取的名字,追求在男性统治范围之外的独立生活,对于十九世纪之前的女性社会地位而言,已是极大的突破与反叛,而同时也正是这个时代刚刚兴起的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象征着女性逃离男性绝对话语权、寻求独立身份的主张已开始萌芽。
然而,就这一点而言,《简·爱》中的女性独立意识却并不完整,也并不彻底。“简·爱略特”这个名字仅被女主人公短暂使用。不仅如此,在其回归男权社会的庇护后,“简·爱略特”化名自然而然地被弃置不用。由此,女主人公的自由精神并不持续,而后便被其主动放弃。而女主人公有保留地回归男性话语权统治这一结局则可被视为作者勃朗蒂对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规范一定程度的妥协。
由此可见,在本时期的英国,女性对于自由意志的追求已见端倪,女性独立意识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然而囿于社会道德观的压力,女性主义思想尚未形成稍具规模的运动倾向,女性对于女权的斗争态度仍有所保留。
三、“泥娃娃老婆”
及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史上迎来了更加具有“女性主义”意义的《玩偶之家》。剧作中充斥着女主人公娜拉对于社会中男性价值观的思考与反抗,由此被视为女性自由呼声的先行者。在这一时代,女性在家中的附属地位已不再能够使女性不假怀疑地服从,由男性价值观构筑的男权社会已逐渐开始崩裂。女性们开始思考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正如文中易卜生借娜拉之口所揭示:“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6]”
十九世纪后期挪威的政治运动极大地带动了本国女性平权思想的发展,女性逐渐倾向于从“家中的天使”这一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中解放自我。因此在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中,女性对于男性权威的挑战也描述得更加激烈。文中的娜拉代表了社会中的典型家庭女性,而当娜拉的家庭出现危机,她发现丈夫对自己的爱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她不能损害他在社会及家庭中的男性权威,否则便会被抛弃。由此,娜拉形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她开始怀疑男性价值观的权威性,她的发问“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7]”代表着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环境下追求自由身份的女性呼声。
在文中不难发现,丈夫海尔茂对娜拉从不直呼姓名,而是代之以“小松鼠”“小鸟儿”“泥娃娃”等动物或玩偶类的称呼。对女性的物化倾向在这篇作品中更加明显,男女两性间家庭地位上的差别也从而被体现得更加具象。当海尔茂把妻子视作可供玩耍的泥娃娃、欣赏取乐的小动物,自然不会把她看作与自己平等的个体,而仅仅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反抗的“泥娃娃”。而当娜拉明确要求夫妻间的平等谈话,便是对自身“泥娃娃”身份的第一次否定:“咱们结婚已经八年了,你觉得不觉得,这是头一次咱们夫妻正正经经谈谈话?”[8]女性对于自身话语权的要求代表了女性主义精神的觉醒,她们对于自己平等身份的追求使得为自己发声成为必然。自此,娜拉形象由“泥娃娃”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由只会唱歌的“小鸟儿”、取宠男性的“小松鼠”变回她自己。娜拉通过抛弃男性施加的绰号而回归自我,变成一个拥有独立身份的“人”。
四、“穿长裤的女人”
电影《达利和他的情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女友、女作家玛格达丽娜抱怨报社不愿刊登她的作品,除非她使用男性笔名。电影的时代背景为二十世纪初,而那时的女性社会地位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女性高等教育已在欧洲各国发展,社会公众层面的女性意识却仍不能够为她们提供充足的土壤,女性主义的运动停留在萌芽期,尚未发育完全。对于女性抒发自己的政治、社会见解的社会接受程度仍在缓慢发展,女性作家不得不通过男性笔名发声,这种现象在欧洲文学进程上屡见不鲜。
自18世纪,女性作家通过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已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在发表作品的审查上对于男女作者采取双重标准,女性以其本名投稿过审可能性极小,还有可能被指责为“伤风败俗”。简·奥斯汀的早期作品基本均用其兄亨利之名,勃朗特姐妹选择以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之名行走,乔治·艾略特本名是玛丽安·伊万斯,乔治·桑在用男名外还模仿男性举止、被称为“穿长裤的女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女性作家弃用自己的原有姓名而启用男性笔名的现象,非但不是对男性话语权的妥协,反而可被看作一次对于男性社会权威的机敏的挑战。女性作家此举并不是出于对被社会舆论所诟病的惧怕,而是出于表达自身作为女性的独立主张的理想。新兴的女性作家拒绝为社会对女性的低认可度所局限,而是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向社会抒发自己的思想与主张,从而获得自己作为女性的话语权。
女权运动经过千年的历程已取得了极大发展,历代女性对自身名字的否定、反抗与重塑构成了女权发展史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女性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促使她们敢于发声以试图平衡男性在社会话语权方面的掌控,从而极大地启发和推动了争取女性地位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已取得极大进展,女性逐渐获得了享有与男性相等的社会地位的权利。然而,仍有一些国家及领域内的性别平等制度尚未完善。国际范围内的女性权利实现程度仍需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