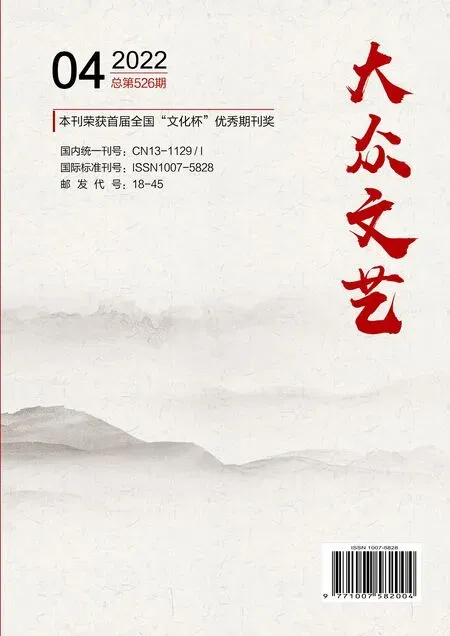莫言的早期创作及文艺观念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363105)
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发表于1983年,是莫言最早受到文坛瞩目的作品。孙犁先生当时指出,小说的手法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瞎子的形象也“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1本文尝试追踪莫言早期的创作生涯,发掘《民间音乐》艺术至上主题形成的内在逻辑。
一、莫言早期的小说创作
莫言于1976年参军入伍,一个主要动机是能吃饱饭。到1981年发表小说《春夜雨霏霏》之前,他已经在山东黄县、河北满城等地服役超过5年,虽然在部队里刻苦自学,甚至担任过文化教员,终因学历较低、年龄较大等缘故,始终不能提干,面临着复员退伍、回乡务农的黯淡前景。小说的发表为莫言争取到了时间,他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在随后一年里又发表了《丑兵》《因为孩子》两个短篇,“遣返回乡的警报终于解除了”2,1982年秋,莫言成功提干。1983年,新作《售棉大路》得到天津《小说月报》的转载,此前,莫言的小说仅见于保定文联主办的《莲池》双月刊。以上四个作品,勾勒出莫言早期小说创作成长的轨迹,构成了《民间音乐》的创作前提。
它们都取材于农村或军营生活。
《春夜雨霏霏》以类似书信的第一人称,表达了一位军嫂对驻守荒岛的丈夫的深情告白,她对家庭的奉献和牺牲,今天读来仍有感人之处。《丑兵》的主人公是农村士兵王三社,他因为相貌普通遭到排长轻视,被战友谑称为“卡西莫多”,失去了很多上进机会,王三社没有自暴自弃,养猪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还主动请缨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不幸触雷后,王三社救下了嘲弄过他的受伤战友,自己却伤重不治。《因为孩子》写两户农民因为小孩之间的打闹而结怨、又因为其中一个孩子落水遇险而和解的过程。《售棉大路》写杜秋妹等四位青年农民连续两个昼夜风餐露宿排队售棉的经历。
从中可见莫言早期创作的特点。
它们落后于同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艺术资源主要来自“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中,《丑兵》在普通士兵身上发掘英雄光辉,借鉴了茹志鹃《百合花》、王愿坚《一根火柴》等军事题材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范式,《因为孩子》在家长里短中见出新农民风貌,延续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准《李双双小传》等农村题材短篇小说轻松欢快的风格。和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或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何士光《乡场上》等比较,差距是明显的。
它们在取材方面比较依赖于作家自身的生活。《春夜雨霏霏》写军嫂“兰兰”思念守岛丈夫,就取材于莫言和妻子杜勤兰的婚后生活。《售棉大路》中“杜秋妹”等青年农民排长队售新棉的艰辛历程,素材也来自莫言夫妇婚前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见闻。
从小说的文体功能来看,它们从主观的抒情、说理明确转向了客观的写实、叙事。在《春夜雨霏霏》中,作家尝试为军人的妻子代言,通篇以抒情为主,绵绵的情思浓到化不开。莫言多次提到,自己因为相貌丑陋曾备受嘲笑欺凌,所谓相貌丑陋,融合了因为成分不好而被迫辍学、过早务农、参军受阻等创伤记忆,是他孩提时代在饥饿之外还感到孤独的重要原因。被群体排斥的遭遇,在军营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为只有小学肄业的学历,无论莫言多么追求进步,也无望提干。在《丑兵》中,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农村士兵王三社的形象,出于一抒块垒、为己正名、渴望认同的强烈动机,还让王三社在上战场前发表了一通关于心灵美的滔滔雄论。兰兰的雨夜深情告白固然真挚动人,王三社关于美与丑的辩证固然有理有据,却都不是小说的本色当行,情理必须让位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事。在摒除这些情感泛滥、抽象说教的成分之后,《因为孩子》尤其是《售棉大路》的面貌出现了明显的改观,能够在设定的有限场景中,集中描写人物的外貌、语言、行为、心理等丰富的细节,通过它们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就小说的文类重心而言,它们逐渐从高度戏剧化、封闭式故事情节的虚构,转向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对日常生活的如实再现。《丑兵》和《因为孩子》的尾声都出现人物牺牲或濒死的情节,它们要么作为故事的高潮,用来升华主题,要么作为情节的突转,带来悲喜震荡,似乎非如此不能够解决矛盾、完成叙事,呈现出高度戏剧化的面貌。《售棉大路》摆脱了这种必须在有限时空里达到高潮、带来震撼的戏剧化强迫症。四位青年排队售棉的故事中出现过一些小插曲,但都波澜不惊,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小说坚持写实、叙事从容,把握改开之初的社会心理比较到位,四位青年农民也能写出个性差异,开放式的结局更有一种轻松明丽、余音袅袅的艺术效果。
为了摆脱叙述的主观色彩,增强小说的似真幻觉,它们特别留心于叙述者的设置和叙述时人称、视角、知阈的选择。在四个短篇中,莫言主要尝试了第一人称人物视角的有限叙述、第三人称上帝视角的全知叙述两种方式,已经可以摆脱机械单一的固定视点,灵活出入于不同视角之间。
它们也开始追求比较多样的语言风貌:《春夜雨霏霏》中的情丝绵软柔美,句繁词丽;《丑兵》中的情怀磊落郁塞,色调斑驳;《因为孩子》中的人物对话利落明快,具有生活实感;《售棉大路》中的叙事语言从容周致,饶富牧歌情调。
总之,这时的莫言,已经能够写出《售棉大路》这样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的小说。农民售棉的确遇到了困难,但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并且及时解决了问题,而且人物各具个性、细节丰富真实、基调乐观明快。然而,《丑兵》中那种表达自我的强烈冲动,也被完全压抑了。是在接下来的《民间音乐》中,莫言初步实现了客观写实与主观表达之间的平衡。
二、《民间音乐》的艺术主题
对于莫言来讲,参军使他走出农村、吃上白面馒头,写作帮他提干成功、继续留在军营。在他已经获得体制接纳、取得创作资格之后,有必要反思一下过去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观了。为此,莫言创作了以艺术至上为主题的小说《民间音乐》。
经过数年农业改革,中国农村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八隆河畔的马桑镇上,从春到秋的半年时间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路、工厂已经陆续完工、即将投入使用,而石油开发马上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得风气之先的私营业主们依托传统集市,纷纷开办酒店、茶馆、饭铺、小卖部,服务对象由赶集的农民转向筑路的工人,营业时间也相应调整,先是突破了集日的限制,继而推出了夜市。马桑镇就像《丰乳肥臀》中的大栏镇一样,正在从一个农村集市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工商城市。
马桑镇民已经不用操心衣食温饱问题,然而,他们在小农经济中养成的一些狭隘意识、保守思想,也要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冲击与考验。小说首先虚构了茉莉花酒店的女老板花茉莉的形象。她年轻貌美,而且集同情弱小的传统美德、灵活精明的商业头脑、先进女性的自主意识于一身,在马桑镇上可谓鹤立鸡群,但也有些落落寡合。她与前程大好的丈夫离婚,理由是“副科长像皇帝爱妃子一样爱着她”,言下之意,她的价值不止于美貌,她的追求不限于家庭。在普通镇民看来,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丈夫,婚后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这就是天经地义。花茉莉视若等闲的“休夫”行为,给他们带来强烈的震撼。不仅如此,她也不像古来弃妇那样,自怨自艾之余更加严守所谓贞节,反而泰然自若地打开门户、当垆卖酒、迎来送往。面对如此出格行为,马桑镇民们无法理解、彻底失语了。其中的泼皮无赖三邪,在欲望的支配下垂涎花茉莉的美色而不能得,于是蛊惑镇民们群体围观所谓男女私情。当小说写到镇民们透过门缝墙头、登上河堤高处来窥探他人隐私时,已经与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母题相遇,并由此表达了小说的第一层意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亟需重建。
莫言将建设精神世界的使命赋予了文艺。为此,他塑造了一无所有、四海为家却痴迷艺术的民乐演奏者小瞎子的形象。精神疾患在马桑镇民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等。三邪的泼皮无赖最为明显,次要一点如方六的瘸腿、黄眼的隐疾、杜双的麻子等生理的缺陷,都暗示着某种心理的疾患,比较隐晦的是花茉莉那略带斜视而倍添妩媚的眼神。是她灵心善感、慧眼独具,最先“被小瞎子那不凡的相貌触动了灵魂”,也是她创造条件、提供舞台,让更多的人从只能“欣赏畸形与缺陷”的精神泥沼中脱身。不过,花茉莉也有“风流刻薄,伶牙俐齿,工于心计”乃至睚眦必报等“令人望而生畏的”一面。小说用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描绘小瞎子使用洞箫、二胡、琵琶等乐器演奏民乐时创造的非凡审美意境,也不吝笔墨夸张其神奇艺术效果:“这声音有力地拨动着最纤细最柔和的人心之弦”“有一股甜蜜的感觉在人们心中融化”,它不仅使花茉莉眼睛迷离、面如桃花、泫泪欲滴,渐渐地多了温情、少了刻薄;使“好奇心极重,专以搬弄口舌为乐”的妇女们“眼泪汪汪,如怨如慕”,惟愿小瞎子和花茉莉早结良缘;使悠闲的酒客和下班的青工像铁屑被磁石吸引一样,为之不分昼夜、不舍远近地神魂颠倒着;也使唯利是图的小买卖主们为之动容失态;使心术不正的三邪大眼圆睁。小瞎子演奏的音乐,洗涤、充实了马桑镇民原本荒芜的精神世界。在镇民们心中,他也从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埋汰、猥琐、可怜形象,一变而为掌握法器的魔鬼一般“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人物”。《民间音乐》对于文艺功能的理解,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人心”论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找到思想的源头。但是,对于莫言来说,净化不仅针对接受对象,更要首先指向创作主体。
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仅仅将艺术视为实现美食、美色、金钱、名誉等个人物质欲望的工具,为了迎合政治或市场、权力或金钱的需要,而陷入自我重复、沦为技术匠人,那么,终有一天,那些曾经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文艺作品,艺术魅力会流失殆尽,创作者自身也会被他试图依附的势力抛弃或吞噬,这是每一位艺术家需要面临的风险。正是在这里,莫言借小瞎子的故事,首先“净化”了自己“利欲熏心”的创作动机。有花茉莉体贴地照顾日常生活,有马桑镇民拥趸般的热情期待,小瞎子得以大显身手,无所保留地演奏了所有拿手的曲子。然而,箱底很快就被掏空了,小瞎子陷入重复演奏有限曲目的困境,为此“满面羞愧”“良心不安”。当接受他启蒙的酒徒们居然将音乐和烧酒相提并论,将净化人心的音乐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时,他受到强烈刺激,“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
小瞎子放弃唾手可得的妻室与名利,义无反顾地继续流浪生涯,体现的是莫言心中艺术至上甚至为艺术殉道的庄重态度。它要求艺术家在各种诱惑面前,勇于摆脱世俗功利、个人利欲的纠缠,始终怀有一种神圣使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只有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饱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能够获得不竭的创作源泉。真正有出息、有追求的艺术家,也像从事任何事业一样,必须心无旁骛,甚至为之备尝艰辛也在所不惜。小瞎子已经用他的音乐洗涤和丰富了马桑镇民的精神世界,他播下的艺术种子也已经通过筑路工人们生根发芽、流播四方。小说尾声写道:“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筑路工人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
三、结语
综上所述,莫言之所以在军中服役期间致力于文学,出自借写作改变命运的强烈动机。因此,早期小说自觉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大多从军嫂、士兵、农民、青年等普通人的生活中取材,发掘人性中淳朴善良的一面、社会中和谐美好的一面。虽然这些作品在思想方面落后于当时的文学潮流,却在技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解除退伍警报之后,莫言开始自觉调整文艺观念,并在小说《民间音乐》中,通过塑造小瞎子形象、讲述马桑镇故事,表达了艺术净化人心、警惕利欲诱惑、扎根民间生活等一系列艺术至上的严正命题。乍一看去,莫言晚近的文艺思想和创作面貌,已经与其早期创作迥异其趣。然而,这些习作见证了莫言小说在思想艺术上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为后来创作的多种变化乃至独特个性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间音乐》中的艺术至上命题,虽然带有八十年代的时代特色,认识难免不够周到和深刻,但莫言几十年精益求精于小说艺术的庄重态度,仍然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注释:
1.孙犁.《读小说札记》[N].《天津日报》,1983年5月18日.
2.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J].《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