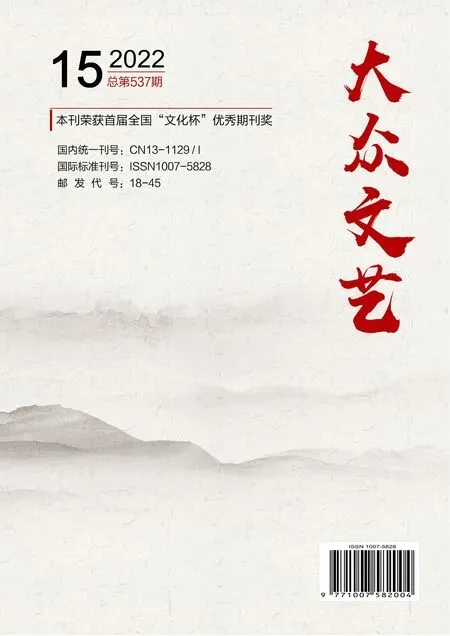关于丁西林独幕戏剧的创作特色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丁西林是我国近代戏剧史上唯一一位专写喜剧的剧作家。他将创作重心放在独幕戏剧上,一生共发表过七部独幕戏剧。丁西林的作品既受到本土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得到英国世态喜剧的滋养。因此他的戏剧内容多是通过观察中产阶级生活的喜怒哀乐,从中抽取值得被揭示和披露的社会现象,再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创作。
一、总体创作风格
丁西林的戏剧创作风格与其成长经历和受教育背景紧密相关。他的戏剧语言直白,借诙谐的对话与矛盾冲突表达严肃的社会主题。丁西林惯用的诙谐是一种理科生式的诙谐,以求观众会心一笑。例如在《一只马蜂》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吉老太太问:“那么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吉先生回答:“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吉先生通过一个比喻简单地阐明了自己迟迟不结婚以及未找到妻子人选的原因,同时也巧妙地躲过了老太太的追问。而在了解丁西林的物理教育背景后,也就自然对他使用这样的行文方式和修辞手法不奇怪了。由此可见丁西林的戏剧语言透露出的其强烈的个人特色。
丁西林的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30年代。他一生发表的七部独幕喜剧中,有六部完成于这个时期。3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整个创作背景的大时代上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30年代各类文艺作品产生了毋庸置疑的深刻影响。丁西林的独幕戏剧也不例外。封建古板的大家长(《一只马蜂》中的吉老太太、《压迫》中的房东太太)、探索自由独立人格的弱势群体(《亲爱的丈夫》中的戏子黄凤卿、《酒后》中的妻子)、渴望婚恋自由的年轻人(《一只马蜂》中的吉先生和余小姐、《压迫》中未出场的房东太太的女儿)等“五四”文艺作品的惯用形象在丁西林的戏剧作品中也屡见不鲜。丁西林于1923年发表处女作《一只马蜂》时,才刚到而立之年。这也就代表了对丁西林本人而言,他的绝大多数戏剧作品都是在其青壮年时期完成的。作为一个青年剧作家,丁西林的戏剧内容是年轻化的、受到进步思想的。而进步的婚恋观是他尤其钟爱的主题。
丁西林家境殷实,曾到国外留学,又受到英国世态喜剧的影响。因此他的戏剧所描写的对象多集中于中产阶级。他通过中产阶级人群嬉笑怒骂的生活化片段来反映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却很少触及到底层百姓的生活。即便是其独幕戏剧中唯一一部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生存艰难的《三块钱国币》也仍旧将故事发生的场景设立在了他所熟悉的中产阶级太太家。并且《三块钱国币》发表于1939年,离他上一部戏剧问世已过九年。因此丁西林写这部戏剧时的心理状态、所处的人生阶段已大不同于其他六部,不可放在一个创作阶段讨论。丁西林在《压迫》的序言里说:“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因为他专写喜剧,政治面貌又是无党派人士,也就直接决定了虽然他的戏剧具有讽刺意味和批判意识,但都并不尖锐。他擅长的是通过诙谐的方式化解尖锐的矛盾,在轻松的戏剧氛围里给予社会批判。
二、进步的婚恋观对丁西林戏剧的影响匪浅
前文已提到过,虽然丁西林的戏剧受到“五四”时期种种进步思想的影响,但他钟爱的题材一直是“进步的婚恋观”。我认为这主要与其创作多在青壮年时完成有关。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进步婚恋观主要由两点组成:(1)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旧道德。(2)冲破了封建家庭主义的束缚,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离婚自主。
丁西林发表的七部独幕戏剧中,有三部直接表现了五四倡导的进步婚恋观(《一只马蜂》《酒后》《瞎了一只眼》)。虽然《亲爱的丈夫》要表现的是戏子地位底下的艰难生存状态和对人格独立的追求,但它借助了婚姻关系这一载体。而《压迫》在反映当时北京社会有房产者对于无房产者的封建性精神压迫之余[1],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女两代人对于婚恋观点的矛盾。下文我将结合具体的戏剧内容对丁西林各独幕戏剧想要表达的婚恋观点分别进行分析。
《一只马蜂》讲述的是封建的吉老太太向儿子催婚,又企图将一位余小姐说与侄子为妻,却不料儿子与余小姐早已偷偷两情相悦的乌龙故事。这部戏剧是丁西林的处女作,它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很基本年轻人要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思想。丁西林在结尾处还通过吉先生不结婚的观点展现了民国时期社会新兴起的“不婚族”现象。
《瞎了一只眼》讲的是一位太太在丈夫受轻伤大出血时给朋友写信,却因六神无主而不小心夸大了病情。在朋友前来探望时,妻子由于不想让朋友觉得是自己故意夸大病情而产生尴尬,索性让丈夫假装病情很严重。故事的结局是丈夫新编造了一个“是他自己故意装瞎整太太”的谎言,既替妻子解了围,又得以摘下脸上扰人的绷带。《瞎了一只眼》通过丈夫和妻子有来有往的互动和无恶意的谎言以及丈夫机智幽默的反应向观众呈现了一种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
《酒后》讲述的是一位醉酒客人昏睡在了一对夫妻的家中。通过夫妻的对话可以得知醉解客人是妻子的钦佩对象。在酒精的作用下,妻子向丈夫提出了想给予客人一个纯洁之吻的请求。妻子提出纯洁之吻的请求可以看作是女性自我与独立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仍旧是不彻底的。因为妻子的言行在主观上还是受到了丈夫的约束,她行动前执意征求丈夫的允许。《酒后》还借夫妻的争论探讨了婚姻的实质。以下是一段剧本节选。丈夫:“中国的女人,只要结婚,不管爱不爱的。”妻子:“这样说,婚姻的制度应该被打破。”丈夫:“那可不要提倡。从前的人,以为结了婚就是爱,那已经受不了;现在有不少的人,以为不结婚就是爱,更受不了了。”从选段中可以看出,该部戏剧对于婚姻的探讨范围已经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传统,深入到探究爱与婚姻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当时“不婚族”现象的一种反映。
《压迫》讲的是房东太太因无家眷的理由要赶走已经交了租金的男租客,男租客通过与女租客假扮夫妻而得以租下了房子。这部剧虽然要探讨的主要社会现象不是婚恋,但我们可以从老妈(仆人)口中得知,房子迟迟未租出去的原因是房东太太的女儿要将房子租给单身的男人,而房东太太不愿租客与女儿产生情愫,所以只愿将房子租给有家眷的人。母女俩行动背后的实质是女儿想借租房寻觅良人,母亲则生怕女儿有越矩之举。所以这个冲突表现的是两代人之间关于婚恋的思想差距和代沟,也借喻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三、以《压迫》为例分析丁西林独幕戏剧的固定创作模式
丁西林的有一套固定的创作程式,即“一个固定场景+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欺瞒任务[2]+趣味性的紧收/慢收”。这个创作程式几乎应用到了他的每一部独幕戏剧中。
“一个固定场景”指的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它既要满足戏剧表演需求,又要满足情节需求。如《压迫》的故事发生在出租房的客厅内。从戏剧表演上看,这个场景的布景难度相对较低,且空间开阔,便于演员表演;从情节上看,这个场景满足了人物出场和故事发生的可能性,是合理的。
“三个主要人物”指的是故事矛盾中心的人物数量一般为3个,而这三个人又会因为一个矛盾(目的)被分为两个抗衡的阵营。比如《压迫》中的主要人物是房东太太、男租客、女租客,矛盾是租房。显而易见,男、女租客属于一个阵营,他们想要租房;房东太太属于他们的对立阵营,不愿意租房。而戏剧要讲的正是这两个对立阵营发生的故事,也就是中心矛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主要人物并不一定等同于出场人物,出场人物很可能大于三个。例如《压迫》中除了上述的主要人物外,还出现了仆人(老妈)和巡警,但他们都只是辅助情节发展的次要人物。由于次要人物没有真正参与到矛盾中心,所以不在讨论范围。
“一个欺瞒任务”即矛盾的解决方法,丁西林戏剧中矛盾的化解多是通过一个阵营对另一个阵营的欺瞒。《压迫》中,男租客正是和女租客假装夫妻骗过了房东太太,才得以租下房子。丁西林擅用欺瞒方法解决矛盾,一方面巧妙地、不起冲突地化解了原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还为戏剧增加了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戏剧结尾因分为紧收和慢收两类。因此他的戏剧结尾也多以这两类为主,且均富有趣味性,使观众看后会心一笑。《压迫》采用的是慢收。顾名思义,慢收在节奏上是慢的。要等到巡警、房东太太、仆人都退场后,男租客才开口问道:“你姓甚么?”女租客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啊……我……”两人都扮了一场夫妻,却还不确定对方叫什么,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结尾通过这充满尴尬地一问一答,带领观众回味了一遍之前两人‘拙劣而精彩’的表演。紧守即戛然而止,最经典的紧收是《一只马蜂》。故事没有停在吉先生和余小姐互诉衷肠这样一个圆满但平淡的地方,而是以余小姐的欺骗吉老太太的一句“喔,一只马蜂!”作为结尾。这种猝不及防又充满趣味的结束从戏剧效果上看增加了戏剧的可看性,能够让观众觉得没看够瘾。丁西林式结尾最典型的效果就是戏剧已经结束,但是余韵悠长。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坛中,丁西林的戏剧风格是特别的。而即便是放在近百年后的今天看,丁西林的剧本仍旧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他年轻化、幽默化的戏剧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让他的独幕戏剧在保有社会批判和艺术成就的同时,最大限度上拓展了受众群体。虽然他的戏剧有固定的创作程式,但并不代表这些戏剧是死板的。固定创作程式只是他的创作手段之一。他将社会现象融合进趣味性的情节,再巧妙地与其戏剧程式相结合,一张一弛间更加容易牵动观众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