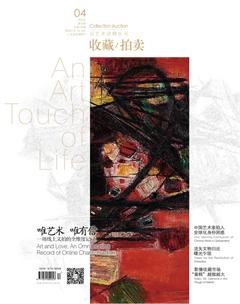流失文物归还曙光乍现
冯翊



曾几何时,我们为国寶级文物《女史箴图》被大英博物馆裁为三段收藏而感到无比遗憾;也因法国枫丹白露宫按西方人偏好混搭展出的圆明园珍藏而视为国耻,每一次有关流失海外文物的消息,总会牵动千万国人的神经。在西方,围绕是否应归还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讨论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如今,随着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西方开始出现尝试向原属国归还文物,不管是出于文明自诩,还是迫于长期的批评压力,文物归还已成为近来西方博物馆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归还案例的逐渐涌现,今后或将引发新时期的文物回归潮。
归还,已渐成大势
尽管多年来,中国、埃及、希腊、伊拉克、伊朗等多个文物流失严重的国家不断向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追索文物,但一直收效甚微。面对追索,他们选择概拒绝。
不过,在长期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不少博物馆开始在批评声中反思曾经沾满鲜血的文物掠夺史,将掠夺文物归还原属国已日益成为西方的种政治正确。英国著名法学家、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Ceoffrey Robertson)曾指控大英博物馆,称其展出的是“盗窃所得的文化财产”。他呼吁欧洲和美国的相关机构归还从“被征服的人民”手中夺走的财产。罗伯逊在新书《谁拥有历史?埃尔金的战利品和返还掠夺宝藏的案例》中公开表示:“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赃物接收者,其中大部分赃物甚至都没有公开展出。”
在越来越强的舆论压力下,为“顺应民意”,些国家在政府层面开始松口,答应归还殖民时代非法掠夺的文物。以往一切免谈的强硬态度渐渐出现了“松动”。
比如,2018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承诺归还在殖民时代被法国掠夺的非洲文物;同年12月,大英博物馆终于屈服于尼日利亚60年来的压力,同意归还一批惊世之作——16世纪贝宁王国的青铜牌饰。
相比口头承诺,一些国家甚至在官方层面开始纳入到行动上来。荷兰开始与印尼、斯里兰卡洽谈当年殖民时期掠夺文物归还事宜。“荷兰现在才把注意力转向殖民遗产的归还,这是一种耻辱。”“我们应该更早做这件事,没有任何借口。”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塔科迪比茨(Toco Dibbits)曾这样对媒体表示。在德国,德国国家文化部、外交部和城市市政当局同意与博物馆合作,制定一套归还前殖民地文物的指导方针。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来自官方的松口让不少国家看到了追索文物的希望。西方多家博物馆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文物追索压力。尤其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这样汇集全球各大文明古国藏品的综合性博物馆,他们的馆藏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路不明,甚至被认为是不义之财,与掠夺、偷盗脱不了干系。
除了近代上千万件文物流失海外的中国,其他文明古国或曾被殖民的国家也面临自家国宝被英、法、美等国收藏的窘况:希腊政府一直向英国追索收回帕特农神庙浮雕,尤其近期随着英国成功脱欧,希腊又一次提出了追索;埃及一直向德国争取收回娜芙蒂蒂胸像;甚至同为近代殖民列强的意大利,多年来也直向法国指出其镇馆之宝达·芬奇《蒙娜丽莎》应回归故里……为了避免单打独斗,中国、埃及、意大利、希腊、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已在近年加强联合,成立文物追索国际合作会议,增强追索力量。
迫索成功背后的法理依据
实际上,国际流失文物追索的基本依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之间禁止进口“博物馆或宗教的或世俗的公共纪念馆或类似机构中窃取的文化财产”,如果发生非法进出口文物的事件,要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并归还此类文化财产。
中国于1989年加入公约。1997年,中国还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根据公约,如果文物流入国没有主动归还,原属国可以启动追索程序,这些公约对于非法流失文物的归还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通过公约追索文物有两大限制的条件。
第一个限制是文物流失时间必须在1970年之后,这意味着在此之前流失的文物都没有强制追索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文明古国近代流失的文物仍旧堂而皇之地被一些博物馆奉为镇馆之宝,继续展出的原因;第二个限制是文物流失时间还必须在流出国和流入国都加入公约之后才具有效力。比如说,中国是1989年加入公约的,如果另外一国2000年加入,那么只有2008年之后流失的文物可以依据公约追索。
在上述现有法理依据的基础上,中国经过多年努力,近年已在流失文物回归方面不断取得突破。2015年,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圆明园鼠首与兔首;同年,法国吉美博物馆归还32件中国古秦国金饰片;2018年2月,美国归还中国361件文物,其中包括大批中国古代墓葬随葬品,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这是美国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返还活动;2019年4月,经过十余年的追索,796件/套中国流失的珍贵文物从意大利米兰正式开启“归乡之旅”,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返还。上述案例,除了圆明园兽首回归属于民间行为,其余均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非法流失海外的文物,同时中、意、法、美国均为公约缔约国,故经过多番争取,才能让这批文物回归。
回归之路依然漫长
当然,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绝非从此一帆风顺。即使面对越来越大的追索压力,一些博物馆依然会选择“鸵鸟政策”,不予回应,或含糊其辞甚至继续狠心拒绝。如英国V&A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埃塞尔比亚的文物,但面对追索,明确回应拒绝归还,顶多愿意向非洲提供这些文物的长期出借展览权。而大英博物馆、卢浮宮收藏了大量中国、希腊、埃及文物,如果这些文物都归还到原属国,那么他们的许多展厅将空空如也,这也是为何大英博物馆。卢浮宮可以答应归还非洲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但在中国、希腊、埃及等国流失文物的归还上却选择性地“遗忘”。
过往,作为拒绝理由,这些博物馆给出诸如“集合人类文明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属于世界并服务于世界的博物馆”“最好将世界上的珍宝集中到许多人能够看到的地方”等“冠冕堂皇”的说辞,甚至美其名日文物留在第三世界的原属国并不能很好保存,维持现状是为原属国更好保存文物等,但当诸如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已日益完善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西方后,这些说法显然不再能站得住脚了。
为了塑造新的收藏合法性,2018年开始,大英博物馆还举办了系列讲座“收藏历史”,讲述部分馆藏文物是如何进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该系列讲座也试图向观众自证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并非都是“抢来的”。
诚然,光靠掠夺者们的“良心发现”与“文化自觉”实现流失文物归还是显然不够的。毕竟收藏各文明古国的瑰宝给大英博物馆、卢浮宮等博物馆带来经济、文化收益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让所有文物都回归原属国在现实层面操作也是不现实的,姑且不论一些年代久远的文物已难以查清当初具体来源,一些文物即使博物馆愿意让其回归,围绕其归属也可能引发多国争夺,而文物回归后能否得到妥善保存与展示也的确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文物流失严重的阿富汗,即使西方一些博物馆向其归还文物,该国动荡的局势与落后的文保条件又是否能为文物觅得一处安身之所?一个事实是,近年的阿富汗受国内局势影响,大批国宝文物仍旧漂泊海外,外交大使曾寻求中国帮助,让阿富汗的国宝文物在国内多家博物馆中流转展出,以免回到国内遭遇不测。为此,让文物回归原属国并不能简单地“刀切”,需要经过长期、多方面的磋商。一些学者指出,西方的博物馆在文物归还上并不一定要全部归还原属国,即使一些文物归还后,也不影响“百科全书式”的展示,可以在两者中取得平衡,这或许是当下的可行方案。
而作为文物流失国,除了不断加强自身文物保护条件,并不断加紧运用国际公约,向文物流出国追索,才能不但取得成果。当然,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终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过,越来越多的归还案例也让人可以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