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丢了“革命精神”
雷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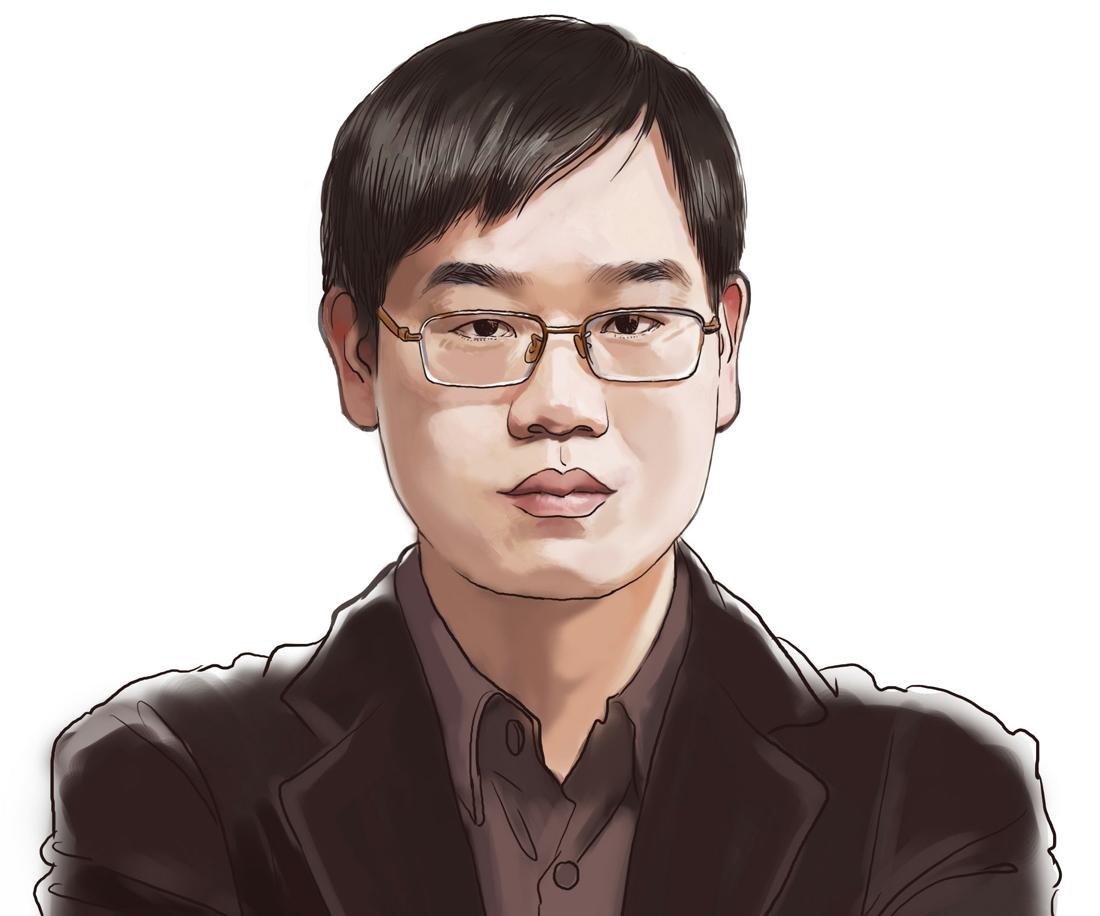
当席卷全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浪潮进入到“推倒雕像”阶段时,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美国人是不是要掀起一场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政治文明以来,推倒历史人物的雕像,往往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运动的“标配”,以至于不推倒几尊雕像,那就算不上在革命。
眼下美国发生的这些事,平权运动高潮期的1968年都曾上演过。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如今的美国没有,也不可能发生革命。因为美国人早已丢掉了“革命精神”。
一说到革命,总能让人联想到激进。再往下联想,可能还有刀光剑影、火烧城池和人头落地。这只是革命的表象,或者说理解革命的维度之一。如果这样看美国,那很难把这个国家与革命联想在一起。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把革命理解为重塑式创新,即人与人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度调整,那么美国人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革命,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成就美国伟大的核心因素。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馬杰,在1950年曾撰写过一本名为《美国精神》的书。这本书基本上是名人传记式的美国辉煌历史,康马杰也没有给“美国精神”下一个权威的定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那个我称之为美国精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
但从康马杰的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美国人冒险精神、革新意愿、进取意志的偏爱,以及对美国历史上成功“调整关系”的肯定。这种美国精神,可以说就是革命精神。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中这样写道:“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过很多新鲜的事物,要说最引起我注意的,那非身份平等莫属了。我很容易地就发现了这件大事给社会的进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
如今的美国没有,也不可能发生革命。因为美国人早已丢掉了“革命精神”。
他所说的“身份平等”,相对于当时欧洲大陆贵族对平民的二元社会结构来说,就是一种革命性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虽然当时美国社会的身份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调整的意愿为后来废奴运动做了铺垫。如果没有身份关系上的革命性变化,谁也不能保证后来美国会出现经济大发展的“镀金时代”。
废除奴隶制并没有解决黑人的平权问题,所以后来的美国继续革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但谁也不能否认,那场运动是美国诞生首位黑人总统的历史先声。
对于美国的革命精神,历史学家戈登·伍德也有肯定式的论断:“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大小、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也像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
不过,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更像是美国革命的历史余波。对于种族多元的美国来说,种族歧视的普遍存在,意味着身份平等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没有完全到位。无论在种族问题上多么极端的人,都不得不正视有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存在的现实。
所以,“关系调整”的意愿与成效,是检验美国是否还具有革命精神的关键指标。但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美国选出了一位明显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倾向的总统。这样的总统以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太可能延续历史上的美国革命,如果不是希望回到革命前的历史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