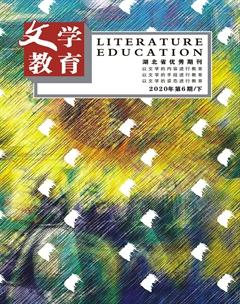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视域下聂赫柳多夫的形象解读
黄皓睿 向紫钰
内容摘要:聂赫柳多夫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巨作《复活》中的男主人公。在文学伦理学的视域下,聂赫柳多夫拥有着赎罪者、贵族、弟弟等多重伦理身份。其赎罪者是众多伦理身份的主导,他由追求救赎出发,开启了错综复杂的情节,多重伦理身份与困境使其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最后在《福音书》中真正觉醒。这本质上也体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伦理观,暗示人类共通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聂赫柳多夫 文学伦理学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到了托尔斯泰笔下,出现了一种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并达到了颠覆。19世纪7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精神上的风暴逼近,开始从学习农民的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了贵族阶级的寄生生活,猛烈抨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存制度,形成了一套以“清洗过的宗教”为核心的宗教道德主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晚年创作出显示他“撕下一切假面目”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的《复活》。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杰出代表,以男主角聂赫柳多夫为主线,展示了一副“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其中也牵扯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现象。聂赫柳多夫作为诱奸马斯洛娃的赎罪者、俄国上层贵族代表、娜塔丽雅的弟弟等,在做每一个决定时都面临着多重困境。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聂赫柳多夫多种伦理身份与面临伦理困境时做出的伦理选择,重新分析其救赎与觉醒之路,以期窥探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伦理观。
一.聂赫柳多夫:以赎罪者为主导的多重伦理身份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一)诱奸马斯洛娃的赎罪者
最初的聂赫柳多夫纯洁崇高、朴素向上,是一个思想单纯、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于为一切美好事物献身的在校大学生。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从道德角度反对土地私有制度。十九岁时他在姑姑家愉快的度过了暑假,也和姑姑家半养女半奴婢的玛斯洛娃“形成了年轻纯洁的男子和同样纯洁的少女由于相互爱而往往发生的那种特殊关系”1,此时的聂赫柳多夫的伦理身份不仅是姑姑的血缘侄子,还是马斯洛娃的初恋情人。三年后,聂赫柳多夫再次来到姑妈家时,已不再是以前那个“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2在此情况下与马斯洛娃的重逢必然会点燃他心中欲望的兽性之火,在临行前一夜诱奸了马斯洛娃。
虽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犯了错误,给了马斯洛娃一百卢布,然而这种补救不是为玛丝洛娃而是为内心的平衡。此后车站的抛弃与意外的怀孕,直接将她推入了一个不幸的深渊,这也成为了二人未来错综复杂的奔波的导火索。可以说聂赫柳多夫不仅触犯了法律,更是冲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根本上使他增加了一层如今的诱奸犯和未来的赎罪者的伦理身份,因为如此,他将以各种方式来偿还、赎罪,为未来他所面临的重重伦理困境埋下伏笔。
(二)俄国上层贵族代表
聂赫柳多夫虽然军队生活使其变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但邂逅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后,潜意识中的高尚与善良开始不断回归。但作为俄国上层贵族的代表,无法改变的社会伦理身份使得他在贵族阶层的生活中异常难受,所以在无法改变此伦理身份的情况下他开始忏悔赎罪并逐渐实现“复活”。这一伦理身份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与私情
这里的婚姻与私情分别是未婚妻科尔恰金娜和有夫之妇玛丽娅。与贵族小姐科尔恰金娜的婚姻在所有上层贵族包括他自己看来,属于上流社会界定的“正派”。作为贵族代表的聂赫柳多夫,于公要顺应贵族间的联姻;于私已有婚约在先仍答应,此时的他不仅是科尔恰金娜的未婚夫,他还有个隐藏的伦理身份即玛丽亚的情夫,即使这不符合道德规范。在一次科尔恰金家午餐会后,聂赫柳多夫开启了他第一次贵族的觉醒,就像他自己所言“可耻又可恶,可恶又可耻”3,他已经对此厌恶至极。加上情夫的伦理身份致使他此刻的伦理混乱,他要么选择其一,要么统统放弃,聂赫柳多夫必须做出伦理选择。
2.地产与案件
聂赫柳多夫在决定与马斯洛娃同行去西伯利亚后,他的思想似乎又回到了讀大学那会儿,否定土地私有。因此他摒弃了上层贵族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思想,决定将田产低价售予农民。这引起了上层阶级的反对,就连农民自身都不敢相信。聂赫柳多夫对于土地的处理办法实则是对传统宗法制度的挑战,对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制的挑战。这背离了俄国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聂赫柳多夫成为了贵族阶层的众矢之的,他对于土地公有的态度就如蚍蜉撼树一般谈何容易,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不是简简单单分配些许土地就可以解决,而是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层面,他的思想拥有着早期共产主义的雏形,也是托尔斯泰晚年思想的缩影。
(三)娜塔利娅的弟弟
娜塔利娅姐弟曾经都有过纯真的时候,但他们后来都堕落了,在聂赫柳多夫看来,姐姐现在如同躯壳一般。娜塔利娅对聂赫柳多夫关于娶马斯洛娃的计划亦是纠结,这源于其婚后的生活环境——唯有肉欲而无思想的堕落生活,但只有最疼爱的聂赫柳多夫让她获得一些慰藉,仿佛找回了年轻时的纯真。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是以丈夫的意志为轴心,因此在弟弟决定死后将土地赠予她的儿子时,她用推脱掩饰渴望,内心深处仍是希望通过金钱、地位来寻找尊重与安全感。聂赫柳多夫似乎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认为“当初在他是那么亲近的娜塔莎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所剩下的是一个跟聂赫柳多夫格格不入、面目可憎、肤色发黑、胡子很多的丈夫的奴隶而已”4。弟弟的伦理身份并没有给聂赫柳多夫带来更多的伦理困境或混乱,反而是加强了他前行的动力,姐姐的形象似乎与浮躁功利的贵族并无二样,因此在他身上血缘的伦理身份引发的矛盾与社会的伦理身份类似,他不愿重蹈覆辙。
二.救赎与觉醒:聂赫柳多夫伦理困境的“复活”
伦理困境是因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处于伦理困境中的人物必然做出相应的选择以实现道德成熟和完善即为伦理选择。玛丝洛娃堕落为娼的悲惨遭遇,被无辜判刑的冤案震撼了聂赫柳多夫的灵魂,他感受到自己是导致马斯洛娃堕落的罪魁祸首,他必须用行动得到马斯洛娃的原谅,进而获得灵魂的救赎。在赎罪路上,种种新的伦理困境不断出现,聂赫柳多夫通过做出符合内心所向的伦理选择走出困境,获得“复活”的新生。
(一)悔恨与救赎
首先,他开启了监狱道歉请求原谅-多次探监表白心意-奔波劳走试图翻案-翻案不成陪同流放-惨遭拒绝幡然觉醒的一系列赎罪之路,这也是他最主要的行为动作,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内容,其余的一切伦理困境的“复活”都是穿插在此之间的。面对与马斯洛娃的伦理困境,他并没有逃避,虽有过混乱但一如既往的前行。作为诱奸马斯洛娃的赎罪者,在他下定决心赎罪后,曾经的种种犹在眼前,人生初见的美好、想象生活的幸福以及赎罪成功后的坦然是他前进的动力,而赎罪道路上的繁杂尘世是他觉醒的动力。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马斯洛娃依旧没能翻案,一切的绝望和无奈化作他同行前往西伯利亚的决心。此时聂赫柳多夫已经注意到沙俄贵族上层隐藏的诟病,但因力不从心而难以改变,无奈的他要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要么积极应对,寻找伦理困境的出口。显然他选择了后者,社会与人际关系的重重碰壁使他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阶级的局限,道德层面上的完善使他第一次重获新生,前往西伯利亚的陪伴是他赎罪和走出伦理困境的唯一出路。聂赫柳多夫为马斯洛娃所作的一切是爱,但“他爱她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5,为了使其摆脱伦理的困境和实现思想的解脱。
(二)挣扎与逃脱
其次,社会身份和血缘身份引发的不同程度的伦理混乱加剧了聂赫柳多夫的伦理困境,但在困境中他实现了觉醒。
1.婚姻
与科尔金恰的婚约使他在马斯洛娃的救赎之路上分身乏术,多重伦理身份让他在贵族关系和自我向往间喘不过气,他认为只有让自己心中的上帝慢慢苏醒,方可真诚的忏悔,以此缓解心中的痛苦。因此聂赫柳多夫断绝了与科尔恰金娜一家的关系,前日相识化作过往云烟,只有心中所向方为完成救赎的无上妙谛。
2.社会
土地问题上,聂赫柳多夫坚持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获得社会层面的第一次觉悟:在和普通农民的接触中,他感到他们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和马车夫谈话,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改革后的农民带来的灾难。从与社会上层各个官员接触到前往西伯利亚上目睹囚犯的惨死,他再一次觉悟。各个案件的处理又使他接触到政治犯,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道理。政治犯崇高的价值观与善良正直的精神改变了他对政治犯的刻板印象,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社会和所谓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人。
3.亲情
血缘伦理身份上,正如上文所道,虽然姐姐一定程度上在为弟弟着想,劝解他勿要重走了自己的老路,但当聂赫柳多夫提及自己的财产将由姐姐的儿子继承后,“一下子破坏了原先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亲热的手足关系,他们反而感到现在彼此疏远了。”6此刻的姐姐已然等同于那些令聂赫柳多夫憎恶的贵族,这样的沉闷、别扭,使他巴不得早点离开姐姐。按常理来看,这不是一对正常姐弟应有的关系,但正是因为聂赫柳多夫的觉醒冲破了贵族伦理身份的牢籠,他对姐姐这种希望用物质的丰富来赢得男方对自身的尊重,用金钱的慰藉、名利的浮华来填补自身缺失的爱的行为感到不耻与厌恶。
(三)觉醒与回归
最后,西伯利亚之行彻底解放了聂赫柳多夫,不仅是对于贵族的认识,更是对于马斯洛娃,有了久违的结局。西伯利亚的流放使马斯洛娃的思想有了质的变化,而与聂赫柳多夫的关系变化的转折点是上谕的减刑。此时的马斯洛娃也在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最后她选择了拒绝聂赫柳多夫而与同行的政治犯西蒙松结合。这个惊人的举动并非空穴来风,“她爱他,认为同他结合在一起,就会破坏他的生活,而她跟西蒙松一块儿走掉,就会使得他自由。”7可见,马斯洛娃依旧还是爱着聂赫柳多夫的,只因她认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连累聂赫柳多夫,不想他再因为自己受苦受难。同时也是因为“革命者为解除人们的苦难儿自己甘受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她,使她迅速回到人们中间。”8这种甘愿自己受苦而成全对方的革命精神与人性的崇高可歌可泣。
对于聂赫柳多夫而言,被动的伦理选择虽然使他完成了救赎的任务,但再一次使他陷入伦理困境,这也是他在小说中最后一个困境。一方面,马斯洛娃看似无情的拒绝,从伦理身份的根源上宣告聂赫柳多夫对她赎罪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另一方面聂赫柳多夫认为马斯洛娃和西蒙松的结合“破坏了他的行为的超群出众的性质,使得他所承担的牺牲的价值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眼睛里降低了。”9救赎不彻底而觉醒不完全,因此他伤心羞愧。
再一次的伦理困境必然导致聂赫柳多夫重新找到新的出路。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答案:“不以暴力抗恶”,即皈依基督教,这种思想让他在最后一个伦理困境中重获新生。虽说翻开《福音书》是他无意识的行为,但若非他历尽如此多的伦理困境,也不可能从中悟出属于他的人生真谛。至此,聂赫柳多夫最终走出了他的伦理困境,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慰藉,使他重新开启了新的生活,但“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果,那却是未来的事了”10。诚然,未来如何,作者没有说,也没有暗示,仅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三.结语:从聂赫柳多夫到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伦理观
小说结尾处,聂赫柳多夫处理好了多重伦理身份混乱而致的伦理困境,于其而言确实获得了新生,但他的新生并非身体力行地去参加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仅仅在《福音书》中完成了救赎与觉醒,找到人性的复活。这和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有本质的不同,他是“带着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幻想和宗教宿命论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在道德心灵里否定现实的运动和革命的手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