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的病原学特征与宿主免疫功能调控的研究进展
张典 牛慧 王晓晓 李春霞 程静 张立志 张雅青
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CoVs)是一类具有广泛天然宿主的正链RNA病毒。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进化的CoVs已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1]。在CoVs感染期间,宿主的免疫系统会对病毒感染触发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对于控制和消除CoVs感染至关重要,免疫调节机制异常可引起免疫反应失控,导致肺组织细胞损伤及肺功能受损。了解CoVs和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明确肺组织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揭示肺部炎症反应的演变和发展方向[2]。本文对CoVs的病原学特征及宿主免疫系统在CoVs感染期间的调控机制予以综述。
CoVs的病原学特征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多次出现CoVs相关性感染,例如,2002年由CoVs引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COV),2012年CoVs引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2019年底和2020上半年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流行病学表明,突发冠状病毒感染传播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3]。
CoVs是有包膜非节段的正义单链RNA病毒,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表面有许多规律排列的颗粒状突起,病毒直径约80~120nm,基因组包含2700~3200个碱基,是目前已知RNA病毒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4]。CoVs病毒体由基因组RNA和膜蛋白组成,膜蛋白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糖蛋白,即刺突糖蛋白(Spike Protein,S)、小包膜糖蛋白(Envelope Protein,E)和膜糖蛋白(Membrane Protein,M),某些种类还有血凝素糖蛋白(Haemaglutinin-esterase,HE)。病毒糖蛋白含有受体结合位点、主要抗原表位,具有对营养物质的跨膜运输、新生病毒出芽释放、形成病毒外包膜等作用。CoVs分为四个基因型,即α、β、γ和δ亚型。α-CoVs和β-CoVs是人类常见的病原体,30%~60%的中国人群血清抗CoVs抗体呈阳性反应。β-冠状病毒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病毒谱系,即A~D。目前已知感染人的CoVs共有7种,HCoV-229E、HCoV-OC43、HCoV-NL63和HCoV-HKU1在人群中较为常见,一般致病性较低,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症状,类似普通感冒;另外三种是MERS-CoV、SARS-CoV和COVID-19,传染性及致病性强,严重病例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5]。除感染人类外,CoVs还可感染蝙蝠、老鼠、貂、骆驼、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CoVs对热敏感,温度达35℃则可抑制病毒生长。紫外线、来苏水、0.1%过氧乙酸等消毒液可在短时间内将病毒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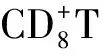
CoVs感染与宿主先天免疫应答
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是病原微生物表面特异存在的,由多种病原微生物所共享,结构恒定且进化保守的分子结构。PAMP是病原体赖以生存,变化较少的主要部分,使病原体很难产生突变而逃脱固有免疫的作用。非甲基化寡核苷酸CpG DNA、单链RNA、双链RNA均为病毒相关的PAMP。宿主先天免疫系统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识别CoVs。已知的PRR主要包括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RIG-1样受体(RIG-I-like receptor,RLRs)、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NLRs)、C型凝集素样受体(C-type lectin-like receptor,CLR)等。与干扰素(Interferons,IFN)产生有关的PRRs主要包括TLRs、RLRs和NLRs[9]。
研究发现,TLRs识别CoVs的病毒核酸,通过激活不同的衔接蛋白(如MyD88,TIRAP,TRIP和TRAM)诱导不同的生物学反应。MyD88是第一个被鉴定的Toll/白细胞介素-I受体(TIR)家族成员,主要激活转录因子NF-kB和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s)途径,以诱导炎症因子的表达[10]。与MyD88不同,TRIF是TLR3和TLR4的衔接蛋白,可激活转录因子IRF3和NF-kB诱导I型干扰素和免疫炎症因子的表达。TRAM和TIRAP的功能是将TRIF分子募集到TLR4受体,并将MyD88募集到TLR2和TLR4受体。MyD88依赖性通路可激活免疫炎症因子,而TRIF依赖性通路可激活I型干扰素和炎症性细胞因子。通过相应的PAMP激活TLR后,MyD88募集busy-1受体相关的激酶IRAK4、IRAKI、IRAK2和IRAK-M。IRAK4在激活MyD88下游的NF-kB和MAPK中起重要作用。IRAK与TRAF6相互作用,导致K-63泛素化,进一步促进NEMO泛素化以激活NF-kB、IRF3和干扰素β[11]。
RLRs包括H家族成员RIG-1(DDX58),MDA5(IFIH)和LGP2,主要识别CoVs病毒核酸。RNA具有DExD / H-box RNA解旋酶结构和C末端终止结构(CTD),而RIG-1和MDA5具有N末端半胱天冬酶募集结构,可与下游衔接子MAVS相互作用。C端RNA解旋酶和CTD结构可以识别RNA,其构象变化需要ATP才能使CARD结构与MAVS相互作用。病毒RNA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三磷酸结构的短双链,互补末端和/或富含聚U/UC的结构。RIG-I可以识别5'端含有三磷酸RNA的病毒核衣壳蛋白。当CTD结构识别出病毒的5'端三磷酸时,引起ATP依赖的构象变化,使CTD结构形成双链RNA复合物,然后CARD结构从自我抑制中释放出来并与MAVS相互作用[12]。NLRs是另一类模式识别受体,其识别CoVs病毒成分中包含保守的NOD结构。NLRs受体家族成员根据不同功能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与多种蛋白质形成复合物,这些复合物包含至少八个NLR蛋白的炎症小体,包括NLRP1、NLRP3、NLRP6、NLRC4、NLRC5W和AY2 等。第二类对于生殖和胚胎再生至关重要。第三类由调节性NLR组成。这些NLRs是阳性或阴性条件性炎症信号传导级联的重要途径。NLRs对CoVs的识别作用机制尚不明确[13]。
CLR是一类可溶性跨膜模式识别受体,在髓样细胞中广泛表达。由于其在细胞内区域具有多种信号传导途径的基序结构,CLR受体具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包括细胞粘附、组织修复、血小板活化和自然免疫反应等。细胞中CLR主要由巨噬细胞诱导的Mincle和CLEC4E受体直接激活,以及受体细胞内HAM样基序来激活受体,涉及募集酸化的脾酪氨酸激酶,进而促进CARD9、B细胞淋巴样组织10和Maltl复合物的形成。同时,凋亡相关颗粒样蛋白,被SyK和JNK酸化后,激活了下游分子,包括NF-kB和MAPKs,并引发多种细胞反应,包括细胞吞噬、DC细胞成熟和细胞趋化性等[14]。
研究发现,CoVs入侵宿主时,PRR最初会识别病毒核酸,收集特定的信号衔接蛋白,激活IFN3和IRF7,然后再转移至细胞核并促进IFN-I合成。IFN-I激活下游JAK-STAT信号通路,促进IFN刺激因子ISG的表达。作为宿主的主要抗病毒分子,IFN可抑制病毒复制和传播,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以促进抗原的巨噬细胞吞噬作用,以及NK细胞对受感染靶细胞和T/B细胞的抑制作用。PRRs中TLRs、RLRs和NLRs与IFN产生有关,IFN异常可直接影响病毒在宿主体内增值[15]。另外,血浆树突状细胞激活后,TLR7/ TLR9识别病毒核酸,以诱导由NF-κB和IRF7介导的炎性细胞因子和IFN-I的产生。树突状细胞在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起关键作用。作为生物体中最强的抗原呈递细胞,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可以有效激活T细胞,在免疫应答的启动、调节和维持发挥中心作用[16]。与健康对照组相比,COVID-19感染患者初始血浆IL-1β、IL-1Rα、IL-7、IFNγ、TNF-α等细胞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更高。重症COVID-19患者的血浆IL-2、IL-7、IL-10和TNF-α的水平显著高于轻症患者。因此,免疫病理学在不同严重程度的COVID-19感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另有研究发现,SARS-CoV编码一种核衣壳(nucleocapsid,N)蛋白,N蛋白可以抑制poly(I:C)或仙台病毒诱导的IFN-β生成。然而,N蛋白不能抑制TLR3和RIG-I依赖途径信号分子过表达诱导的IFN-β产生。研究认为,SARS-CoV的N蛋白可作为免疫逃逸蛋白,N蛋白的C末端结构域对IFN诱导产生拮抗作用,使SARS-CoV保持高致病性,影响宿主的先天性免疫应答的效果[18]。
CoVs感染与适应性免疫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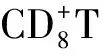
B细胞亚群具有天然记忆细胞和抗体分泌细胞的表型特征,可在CoVs中大量聚集。使用特异性的9-mer肽CYSSLILDY,检测到针对MERS-CoV的抗原结合位点,位于S糖蛋白区域内的437~445位点。该序列具有最强的B细胞抗原性,在计算机模拟中与MHC I类等位基因的相互作用最大[23]。研究显示,体液免疫对于控制持续的CoVs感染至关重要,从MERS-CoV感染康复的患者分离出多种抗体,包括MCA1、CDC-C2、MERS-GD27和MERS-GD33等。研究发现,CoVs患者体内的抗体反应涉及复杂的单克隆抗体混合物,可作用于病毒包膜糖蛋白上的不同抗原结构域。已经发现了20多种人类抗体或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在针对MERS-CoV感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作用。此外,MERS-CoV利用S蛋白作为粘附因子,通过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4,DPP-4)受体进入宿主细胞。DPP4是信号传递以及获得性和先天性免疫应答激活的关键受体,针对DPP-4的靶向单克隆抗体可能具有与疫苗相似的保护作用[24]。
有学者发现,由噬菌体源制备的人单克隆抗体m336,可与MESS-CoV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区相互作用,体外实验显示对MES-CoV具有较强的中和活性,抗体m336可使肺组织中病毒RNA滴度降低40000~90000倍[25]。用MERS-CoV感染模型猴后,分别用高滴度超免疫血浆或单克隆抗体m336进行处理,两组的临床症状均可得到明显缓解,但仅在超免疫血浆组中发现呼吸道病毒载量降低。研究表明,抗体m336可显著降低兔肺组织中的病毒RNA滴度和与病毒相关的病理变化。但两种疗法均未能完全阻断MERS-CoV感染,不同模型动物对MERS-CoV感染引起适应性免疫反应存在差异,MERS-CoV 感染可能存在种属特异性[26]。此外,接种S纳米颗粒的小鼠产生了针对同源病毒的高水平中和抗体,该抗体与异种病毒无交叉保护作用[27]。在受到SARS-CoV感染后,免疫雪貂比对照组产生更快更强的中和抗体反应,在肝组织中也观察到强烈的炎症反应[28]。研究显示,SARS-CoV 的S蛋白与肝组织的炎症反应增强有关。也有学者研究了SARS-CoV病毒血症和抗体应答的时间分布。在SARS患者病毒血症的高峰期,诊断前1-2周血液样本中75%可以检测到病毒RNA,但均未在恢复期患者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研究认为,在SARS-CoV急性期的体液免疫反应和疾病恢复过程中,持续存在的IgG抗体对于控制病毒血症及清除病毒具有重要意义[29]。
综上所述,CoVs引起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适度的免疫反应对于抗CoVs感染至关重要,免疫调节机制异常可造成免疫反应失衡及靶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损伤。明确CoVs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了解CoVs逃避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途径,选择应用CoVs靶向单克隆抗体,将为完善CoVs感染的抗病毒策略及改善预后提供依据。尽管COVID-19感染的流行时间较短,但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多,可能与COVID-19 独特的病原学特征有关,需要更多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予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