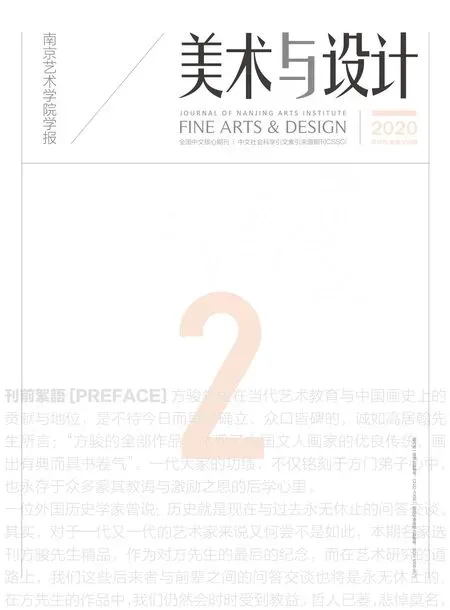尽善尽美
——清代苏州年画女性形象特征的构建①
范银花 樊媛媛(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苏州年画在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孕育并繁荣,审美对象和消费对象的阶层特性,使苏州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民俗心理和文化特色。女性人物、儿童是桃花坞年画中出现最多的人物形象,频繁现身于各类题材的作品中,尤其到了“康乾盛世”,在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中,女性人物井喷式地出现。于是乎,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成为观照女性社会地位、生存状态的一面镜子。
一、女性形象的大量涌现
苏州年画自明末即已出现,清初进入繁盛,康乾时期,“海宇清宴,民物雍熙”,城市商业繁荣刺激了市井文化的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戏曲小说、民俗、风景、仕女等为题材,“仿泰西笔法”,刻工精美、尺幅较大的作品。中国著名文学史家、艺术史家郑振铎在其《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中说:“而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盖自徽派版画式微以后(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1]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以仕女、婴戏形象为主作品几占近半,如《美人戏婴》《双桂轩抚琴图》《美人裁缝图》《美人题诗图》《仕女浇花图》《帘下美人图》《弄花香满衣图》《清音雅奏图》等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吴县人顾禄(铁卿)《桐桥倚棹录》卷十记:“山塘画铺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花坞、北寺前之多用印版也。唯工笔、粗笔各有师承。山塘画铺以沙氏为最著,谓之‘沙相’。所绘则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而画美人尤为工耳。”[2]除去所占比重较大的颇受市场欢迎的仕女题材的“美人画”之外,其他描绘女性人物的年画亦不在少数,按期画面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反映底层劳动妇女生活的,譬如《渔娘图》《渔家母子图》《采茶歌图》《提鱼上市图》《纺织图》《耕织图》《采桑织机图》等;一类则是以戏文小说(包括历史故事)入画的,如《宝玉黛玉图》《黛玉调琴》《妙玉惜春弈棋图》《桃花记崔护偷鞋》《白蛇传》《杨贵妃游花图》《杨家女将出征》等;再一类就是寄寓普世大众美好的世俗愿景的,如《瑶池献寿图》《麒麟送子》《五子夺魁》《冠带流传》《玉堂富贵》等等。
在桃花坞年画鼎盛之际,市面上涌现了大量表现女性形象的年画,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或是主要表现对象,或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尤以仕女形象最甚。究其缘由,形式最直接且辐射范围最广的影响因素就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革。清兵入关,明朝覆灭,至清康熙,经过20 年民族斗争的战乱已渐进尾声,连年的兵燹马祸之灾,加上时有的自然灾害,使得人口锐减,百姓渴望休养生息,繁衍子嗣,重建家园。女性,作为繁衍后代最不可或缺的工具,此时的她们就是开枝散叶的象征者,她们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符号意义,这就不奇怪,在许多年画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女性形象与婴儿形象如影随形、跬步不离。
其次,经过康熙、雍正两朝平定西南、西北之叛乱,文化上倡儒学礼,经济上轻徭薄赋,民生安定,乾坤清泰。苏州民间画师宝绘轩主人在其所绘《苏州阊门三百六十行图》(1734 年)中题诗道:“绣阁朱甍杂绮罗,花棚柳市拥笙歌;高骢画舫频来往,栉比如鳞贸易多。”[3]苏州商业贸易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人们纷纷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中,不仅男子如此,女子也加入其中,渔娘、采茶女、采桑女、织女、裁缝等劳动女性的身影逐渐增多。男女共作,城市一派热闹繁盛,这样,对于太平盛世的讴歌载道成了年画艺术的一个新方向,那些底层劳动妇女欢乐、富有世俗气息的劳作画面,也同时贴合市井百姓的生活脉搏和审美情趣,从小处体现了处在全国商业中心的苏州人的自足与自豪。
“饱暖思淫欲”,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赏玩似乎是永恒的旋律,更何况正值康乾盛世,物阜民熙,男性对女性的消费就显得更加突出。《提鱼上市图》歌词曰:“莫道渔家住水乡,此中有女世无双……虽然不及闺中秀,也学时新巧样装,青布兜头齐额系,束腰裙子抹胸膛。天然俊俏难描画,提鱼入市上街坊,引得闲人心似火,争先恐后话声扬,银钱带内装。”[4]词中对男性性消费场面的描绘,生动直白,足见他们对女色的趋之若鹜。作为图像制作者,创作此类年画作品的民间画工,身为男性,显然他更能够捕捉同性的性消费心理。他们化身卖鱼女,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词,以便于与男性消费者建立更为直接的交流,迎合他们对异性的需求和欲望。
高度发展的物质生活刺激了市民文化精神上的需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图像独立的欣赏价值,而开始寻求情节性、可读性更强的年画。恰逢其时,清代戏曲演出的繁荣与历史小说的盛行为女性人物登上年画舞台提供了契机,包括被禁止的小说淫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楼梦》。然而,早期的《红楼梦》题材的年画也并非一开始就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如《妙玉惜春弈棋图》在画面构图、人物形象等方面还是沿袭中国传统仕女画的图式特征,无甚情节描绘。而后发展的《红楼梦》年画逐渐迎合人们的欣赏、阅读价值诉求,人物增多,场面开阔,并竭力还原原著。此外,在苏州地区流行的苏州评弹、昆剧、苏滩还有京剧等,也藉由年画这一艺术形式以图像方式生动地演绎起来。长篇弹词《珍珠塔》就是苏州评弹中的著名书目,年画中表姐陈翠娥、翠娥之母、方卿之母、白云庵女尼等女性形象频频出现,画面连贯,情节紧凑,耐人寻味。
及至道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统治,年画艺术大伤元气,但是随着具有人文意识的启蒙思想肇始,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渴望日益加剧,女性的独立人格、反抗意识也开始受到了关注,典型如《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等,但是此类作品的创作大多还是画工藉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所需,至于真正地走出思想拘囿,能够正视女性情感,尊重女性地位与人格的年画作品恐是微乎其微。
二、“尽善尽美”的形象塑造
1.“善”之里
相较于其他地区,苏州年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气质既不同于杨柳青浓厚的宫廷气息,也不似山东潍坊、四川绵竹等地原始质朴,它所塑造的是以高雅细腻为主导创作风格的同时适应市民审美需求的雅俗共赏的女性形象。然而倘若只用“高雅细腻”“雅俗共赏”这些修饰词去解析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却是不够的,因为这都只是其表象形态所灌输给观者的视觉经验,而其图式背后,实则寓藏着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性别体系的极度倾斜,这种不平衡、畸形的两性关系在被男性赋予“尽善尽美”属性的女性人物图式中得以尽显。
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家、女性主义艺术研究先驱琳达·诺克林曾在其《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中说:“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中,为社会里取得的整体权力关系作掩护,让这些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事物自然而永恒的秩序”,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反映了西方艺术中女性地位和人格的缺失,人们意识中认定女性是脆弱的、被动的,是满足男性需求的性目标,她们被界定为具有理家和养育的功能,被认定为属于自然的领域。[5]所有的这些观点无非是保护男性社会权力、遮掩男性欲望的外衣。从这一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西方艺术于此还是有“共鸣”的,反映在苏州年画中则是褒扬贤妻良母、赞祝瓜瓞绵绵主题的作品的繁盛,如《五子登科》《母儿满床戏》《莲生贵子》《玉堂富贵》《采桑织机图》《冠带流传》《麒麟送子》等,展现在观者眼前的,都是些扮演和承担着贤妻良母角色的女性形象,她们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她们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她们是传统封建社会完美实用的女性典范。由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具有渗透力的性别差异前提基础上,不只是男性画工、男性消费者,即便是女性自己也对位于从属地位的自我毫不质疑,这样的观念虽然并非全未受到争议,但传统已根深蒂固,因而民间画工对画面中女性人物的塑造着力于赋予其“善”的性别属性。
《说文解字》训“善”为“善,吉也。从誩,从羊。”[6]善寓意着美好、吉祥,在清代封建伦理的语境下,女子的“善”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即孝敬公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等,满足一切她们所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之后,她们就成为了男性眼中美好吉祥的“善”的化身。在苏州清代诸多年画中都可以看到母子嬉戏的场面,《渔家母子图》(图1)和《采桑织机图》(图2)就是典例。在《渔家母子图》中,画工为了突出画面人物,将母子二人置于单纯的背景之前。画面中轴线处立有一位身姿柔婉背着蓑帽的朴素渔家妇人,她左手提着装有鲤鱼的篮子,右手指着篮子,正回头宠溺地俯视地上扒鱼笼的孩童,似在哄孩子回家吃鱼。与前者不同,《采桑织机图》则将人物安排在一个纵深的环境中,由远及近,一女子坐在窗旁织布,然而她的目光不在手下的活动而是投向了窗外,于是画工假借纺织女的视线颇具心机地为观者引出了他想要表现的画面重点——采桑母子。这对母子在刻画手法上出现了与上图人物刻画手法的高度一致性,妇人一手提篮一手采摘桑叶,侧转身体回眸凝视脚下玩耍的稚子。两幅图像在突出主体人物的处理上虽有所不同,但两对母子相似的情节动作和心理状态却揭示了艺术创造者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诉求。

图2 《采桑织机图》
两幅图像中的女性人物都存在回头俯视的动作,该动作无疑为画面中孩童的出现埋下伏笔。正如上文所述在许多清代苏州年画作品中,女性人物往往是与婴孩形象形影不离的,这一规律是中国传统社会多子多福的民俗心理在艺术上的表现,《诗·周南·螽斯》云:“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7]人丁从先秦开始就被作为衡量一个家族或地区是否兴旺昌盛的准则。及至清代,苏州人口和财富的集中程度皆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人丁兴旺、家族繁荣的愿望直接显现在最能表达普世大众愿望的年画中,画面中的女性人物作为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被理直气壮地注入了生殖繁衍、传宗接代的伦理诉求。画面中她们是生育工具,是承载着子嗣兴旺、多子多福的愿望载体。为了强化这一思想观念,作者还竭力营造出母子互动、其乐融融的和谐场面,这不仅符合年画吉祥喜庆的民俗特征,并在有意无意中抹杀了生儿育女、辛勤劳作的艰辛,呈现的是女性在履行自然与社会同时赋予她们的职责时的绝对愉悦,这样的画面无疑是控制女性、彰显男性绝对话语权的得力助手。
如果说民间画工通过诱导观者视线和渲染整幅画面伦理气氛来深化女性的慈母属性的行为显得隐匿而含蓄的话,那么他们在画面中附加给女性人物一些特殊的符号则更为直截地揭露了男性对女性“善”的伦理要求。细观清代苏州年画,无论是盛期还是晚期的作品,画工从未让这些女性的手处于空闲状态,或捏帕,或持扇,或抚琴,或执笔,或织布,或提篮,或穿线,或抱子,她们的手中总离不开固定的道具,似乎只有这样她们看起来才更像是个符合传统礼教要求的合格的妻子或母亲,观者才会驻足欣赏购买。在《渔家母子图》中妇女手上提的鱼篮直接表明了她所承担的劳动妇女的角色,不仅如此,在民间“鱼”和“余”“裕”是同音字,“鱼”寓意着年年有余,生活富裕。除此种种功能之外,竹篮的添加还暗示着父权权威对当时女性的家庭主妇职能要求,她们既需要担当好母亲的角色,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才能为家庭带来祥瑞和福气。《采桑织机图》中的采桑女亦是如此,还有那些携琴持书、舞文弄墨的女子,她们都是能够达到社会标准,满足封建社会不同阶层男性需求的女性楷模。画面中画工们赋予了她们持家兴家所必须的各种技能,他们紧贴时代和社会的意识形态需求,按照男性的旨意,不遗余力地将她们塑造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使她们成为一个盛纳封建传统伦理规范的容器,成为一个为父系社会所公认的吉祥符号。像这样既成功且受欢迎的年画作品在彼时可谓是比比皆是。
在清晚期同时也处于衰退期的苏州年画作品中,女性人物还出现一个显著的特征——露足。《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洋灯美人》《街头谈笑图》《莲生贵子》等作品中妇女均露出了小巧尖窄的“三寸金莲”,这种与现代都市女性审美观念背道而驰的裹脚习俗在当时看来是合乎伦理法度的且被大肆地崇尚为婚嫁标准之一。中国女性缠足陋习是古代男权专制的产物,肇始于宫廷,后流徙民间,清余怀所著《妇人鞋袜考》记载:“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絅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著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8]从缠足陋习风靡之初的动机来看,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众,愉悦家长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满足他们的欲望是缠足的根本目的。沿袭至清代,缠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风尚,它自觉地上升为人生礼仪的一部分,成了能够决定女性婚姻的度量衡,世人皆以男性娶小脚妻子为荣,而生有天足的女子则备受歧视,婚事艰难。虽然女性缠足的习俗早已盛行,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女性身体中最为隐秘的部分之一,却是不可以轻易示人的。然而与实际状况相反的是,在苏州年画画面中,无论是蓬门荆钗,还是贵族妇女,她们的小脚都被画工刻意地安排在宽大的裤筒外面,不仅如此,民间画工还以艺术手法将这些女性的“金莲”缩小得长不盈寸。通过刻意呈现的方式夸张展现女性不可外露的小脚,画工该举实际上是在强调一个女性符号,以男性视角而言,它符合当时女性的性别特征和社会地位,是女性遵守男权社会游戏规则的一个象征。画工们将这一符号示之于众,广而告之,其目的在于标榜宣扬女子应当遵循的性别规范。这一现象并非特殊,它普遍地存在于各地民间艺术中,在杨柳青等地年画中亦可找到凭证。总之,生活中,中国古代男性控制与桎梏女性身体的小脚,也成了男性图像制作者们展示清代女性“尽善”的性别角色特征的手段之一。
2.“美”之表
苏州画工创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审美特征属于与传统礼教和伦理规范相趋同的美的范畴,她们一方面承担着父权权威界定的女性行为标准,另一方面她们还要戴上“美”的面具,接受他们的视觉洗礼。她们既“善”且“美”。
从历史的延续传承来说,早期苏州年画女性的形象特征受明代吴门画派和插图版画的影响较大。《清音雅奏》《瑶池献寿图》等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宛如明·崇祯年间,项南洲镌刻《燕子笺》传奇插图中的郦飞云之像,与其《西厢记》崔莺莺像也极为相似,都是弯眉细目,绣口通鼻,削肩修体,文静雅丽。人物造型线条细劲流畅,可见明末金陵书肆刻工和插图版画名家自入清以后多流入苏州年画行业中献艺,故而苏州早期年画犹存金陵、浙派一带版画余韵。[9]清早期的《桐窗椅栏图》即采用了版画插图中的“月光型”版式,图中仕女人物以线造型,写实传神。
苏州年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征对吴门画派的继承,更接近于唐寅、仇英一路的技法和风格。人物仕女,宛若绣像,运线隽畅飘逸,套色淡雅透明,大有二人的余韵。明王世懋在《王奉常集》评说:“唐伯虎解元于画无所不佳,而尤工美人,在钱舜举、杜柽居之上,盖其生平风流韵多也。”[10]对比唐寅生平所作的《陶谷赠词图》《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作品的女性形象来看,桃花坞年画的仕女作品中,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十分深刻,在开相以及蛾眉、含笑目等容貌的描绘上几乎相仿,其绘画文质相兼、雅俗共赏的特点也是与苏州年画不谋而合。兹以《凉风扇下图》(图3)为例,图中描绘了两位娴静娇俏的女子,手执凉扇,顾盼生色的画面。二人皆淡扫蛾眉,修耳隆鼻,朱色樱唇一点,双眸含情流波,窄肩修身,姿态撩人。为避免板滞的构图,二女分别向两侧微倾,一人手执凉扇,一人轻伏身后,姿态均柔软婀娜。从相貌身段以及着装装扮来看,二人可能为普通女性市民。再观唐寅所作《秋风纨扇图》中女子,同是蛾眉细目,绣口丹唇,双手执扇,更显柔弱动人。年画《四季仕女图卷》在仇英《游戏秋千图》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图3《凉风扇下图》
这种余韵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一种程式,从民间画诀中即可得到印证,“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奓手,要笑千万莫张口。”这种描绘女性人物形象的高度概括的文字在民间画诀中仍还有许多,“画少女应削肩”“美人要修长”“官家妇,宫样装;耕织女,要时样”“贵妇样:目正神怡,气静眉舒(眉间距离稍宽)。行止徐缓,坐如山立(不偏不倚)。丫鬟样:眉高眼媚,笑容可掬,咬指弄巾,掠鬓整衣。贱妇样:薄唇鼠眉,剔牙弄带,叠腿露掌,托腮椅榻。”[11]这种定式的描绘和粗线条的概略的归纳使得苏州年画盛期的女性人物形象既继承了唐、仇仕女画传神写意的特色,又兼备了迎合市民阶层审美范式的程式化、符号化的特点。
不论是对明代插图版画的造型线条和创作版式的沿袭,还是对吴门画派唐寅、仇英之流的仕女画的画面内容和人物造像模仿,清代苏州年画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大多沦落为了一种程式化的审美范式,既没有某一个具体女性的个性特征的描绘,也缺少真正的性别角色特点的表现。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呈现出一种“病态美”,千篇一律的削肩修颈,素面玉手,柳眉细目,平胸欠腰,还有努力营造出的S 型身线,以追求一种极致孱弱的美人形象。不过,相比文人画中仕女,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更多了些喜庆欢乐的气氛,少了些伤春悲秋、迷茫苦闷的文人色彩。《美人裁缝图》《美人题诗图》《渔家母子图》等女性形象皆眉似弯月,嘴角含笑,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仕女形象与年画艺术的民俗特性相适应的产物。由是观之,苏州年画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是一种被加持了积极情感色彩的弱势病态群体。
此外,清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使得女性的身体被包裹在交领长裙之下,画工们便将画笔对准了服饰和裸露在外的头、颈、手部。初期和盛期的女性服饰还可见到文人“仕女画”的影子,含蓄雅逸,端庄凝重,如《帘下美人图》《采桑织帛》《美人题诗图》等盛期作品,服饰的颜色以典雅为主,色调和谐,通常一件作品颜色不逾五色。衣纹的处理还加入了“泰西”笔法,衣纹褶皱深浅变化制造出的明暗变化,使得整个人物更加细腻雅致。而从道光年间开始年画艺术走向颓势,仕女题材的美人图开始减少,戏文故事、求福祈祥题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描绘得简率粗狂,服饰鲜亮,紫、黄、红、绿等色彩皆具,明度较高,对比强烈,极富民间装饰趣味,如《玉堂富贵·莲生贵子》《十美踢球图》《洋灯美人》等图中女性服饰宽大直筒,纹样繁复,色彩艳丽夺目,视觉冲击强烈。
在清朝的两百多年里,苏州年画经历了由发端到衰颓,其中女性形象也在发生着转变,然而这种程式化的审美范式却一直贯穿。民间画工一边真实地记录着她们的生活,一边主观地理想化地对这些女性人物进行封建制度体系语境下的“尽善”“尽美”的描摹。“美”与“善”借助女性气质的伪装互为表里,它们使男性家长的野心和欲望的实现触手可及。在视觉文本和现实世界中,行为准则与审美要求,伦理符号和欲望载体,慧中和秀外,“善”和“美”,全部都被投射到了女性身上,成了她们无法僭越的界限。
三、完美形象背后的欲望解读
关鸿在《诱惑与冲突》中说:“权利的宝剑握在男子手中,但是美的桂冠却戴在女性的头上。”[12]审视清代封建男性中心体系下,苏州民间画工对年画中女性人物尽丽极妍地描摹似乎正印证了这句话。倘使此句在此成为一个真命题的话,那么这些女性形象应该是千姿百媚的、高雅的、被关注的,但是画工笔下温柔美丽外衣包裹着的孱弱卑恭、千篇一律的身体却又进行了自我否定,以鬻矛誉楯的手法记录着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困境。
东汉班昭著《女诫》有:“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13]家国同构是我国宗法社会的特征,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点,家庭被视为基本单位,在家庭内部,男性家长具有至高的话语权,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便成了这一制度下合理的衍生物。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女性始终被贴着自然、身体、被动者、牺牲者、致命的性、永恒不变的等等标签,而男性,则与智慧的见解、社交、理性、历史的、活跃性、权威、机制、自我决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14]这种不平衡的等级秩序以不同的形态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在清代苏州年画中亦得以体现。首先,画工将封建社会的审美观念和伦理规范融入到年画创作中去,凝练成口诀或经验付诸图像制作,在这里,他所表达的不再是个人的具体行为或观念,而是代表了清代男性市民阶层对当时社会女性的审美要求。女性被创造出的程式化的样貌身段,实际注入了清代男性对理想化女性的创造欲、占有欲。细观此时的美人图,莫不如出一辙,柳眉、细目、长鼻、绛唇、修颈、窄肩、纤腰、玉手等等,无一瑕疵,还刻意拉长头颈与身体的比例,以追求理想美。同时在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侵蚀下,男性欣赏的女性还必须贞节保守,女性姣好的身体在年画中往往被长裙宽衣所掩盖,她们成了奴隶,接受男性的视觉囚禁。年画所塑造的各色女性形象只是带有特定女性气质的一个符号,而非真正的女人,男性享有这种对女性气质特征的完全话语权,是为他们所操控,披着“善”与“美”的外衣男权文化中的一个傀儡。如《美人题诗图》(图4)中的两位女性衣裳整齐严实,形象文弱静婉,一人欲舔笔题诗,一人抱琴,相互含笑凝视,动作含蓄优雅,不论是形象姿态还是文化寓意,都是一幅成功的符合男权中心文化标准的作品。在男性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不需要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独一无二的伴侣,也不愿意将女性放在等同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的地位是不容许被僭越的。从观者的视角和距离来看,图像中的女性人物大都略低于视平线,近景式的描绘使得人物与观者的距离控制在数米以内,观者是以一个俯瞰者的角度在封闭的空间中打量接近掌控她们,而这种视角隐隐地透露出男性的占有欲和尊卑心理,封建社会男权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伦理规范于此昭然若揭。

图4《美人题诗图》

图5《采花戏蝶图》
清代苏州画工创造出的程式化的写像法则使得年画中的女性整体呈现出孱弱病态的精神状态,这是时代男性审美趣味的彰显,透露出男性的保护欲和侵犯欲。“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扶柳”,藉由女性羸弱气质来烘托阳刚的男性气质,获得可笑的满足感。如《采花戏蝶图》(图5),从表面上看,图像描绘了一挑着花篮,缓步戏蝶的女子,流露出柔弱恬静、蕴静媛婉之美,给观者造成一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假象。仔细推敲图像中的细节,蝴蝶在古代具有爱情的象征色彩,围绕在女子耳旁嬉戏的蝴蝶带有一丝缠绵的意味在其中,而将蝴蝶安排在女子的头颈周围更是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女子的体香透过画面而溢出。这种手法被画工如法炮制地用在了服饰上,女子的衣袖、裙摆全都向画面的左侧倾斜,画工不依靠背景的的衬托而将春风骀荡、体香四溢的感觉营造出来。接着往下看肩上的担子,画工在这里刻意将担子弯曲成一定弧度,看似表现花篮的重量感,实际是故意给女子施以压力从而反衬出她的柔弱,刺激男性的保护欲望。女子的手指也被艺术化,挑着担子的手不是呈紧握状,而是轻拢手指,微翘尾指,握着拂尘的手也是姿态优美,且有由内而外向上挑起之势,在此手部的细腻刻画无不带有挑逗情欲的意味在其中。无论是暗藏的体香,还是有形的柔姿,它们都是点燃男性欲望的导火索。崇尚父权至上的男性都渴望去压制母权,掠夺她们的身体、收编她们的权力,他们陶醉于立足制高点,以统治者的身份,由女性卑微地取悦他们而获得的快感。在这里,长期封建皇权专制下男性的虚伪与虚弱一览无余。

图6《街头谈笑图》
除此之外,女性的小脚也是男性欲望的输出口。从宋代伊始,经历了元、明两代的发展,缠足之风在清代达到顶峰,如果一个女子杏面桃腮、月眉星眼、素齿朱唇、玉骨冰肌,但裙底莲船盈尺,便会大煞风景;相反如若女子三寸金莲缠裹得好,纵使其相貌平平或其貌不扬,来提亲的人依旧是络绎不绝。清代诗人袁枚还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因此女性对自己的小脚格外重视,自缠足后,她的三寸金莲就变成了一个最隐私的部位,绝不可让生疏男人看见。而越是隐秘就越容易激发男性的窥探欲望,清同治年间北京就有一盲眼富商为摸女子小脚而掷五十金,男性看到女子的足小不盈握,走起路来娉娉婷婷、扭扭捏捏,会浮想联翩,甚至“昼间欣赏,夜间把玩”。《街头谈笑图》(图6)中,与修鞋匠攀谈的妇女就有着与身体比例极不相称的鹰钩般小脚,不仅如此,为满足男性的窥探欲,画工还将该妇女的两只小脚进行了特殊的处理,他摒弃了传统的双足着地画法,刻意将女子的左脚向后抬起,在飘动的衣带遮掩下抬起的小脚若隐若现,似在捕捉行路过程的一个瞬间。尖细的小脚本就足以调动男性的欲望,而欲遮还羞的姿态更将其窥探欲撩拨到顶点。渐渐地对女性小脚的窥视和赏玩欲望在传统礼教的浸染下衍化成为男性强烈的控制欲。清末爱莲居士有语:“妇女必须缠足,否则强壮如男子,为丈夫者不能制服也。”[15]男性作为权力的中心,他们根本不会同情女性断筋裂骨之苦,使妻子安分守己地待在家中,便于管治,从而确保“夫为妻纲”的正常运作,才是他们乐于见到的。所以,其时的年画作品中,小脚妇女表现出遵守纲常伦理的贤良淑德状,完全是父权权威管治下的产物。
清代苏州年画是反映清代市民阶层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折射出了彼时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地位,这些“尽善尽美”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社会男权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男性欲望与幻想的视觉化符号,记录着各种女性信息,破译它们,对我们全面研究妇女史、社会史、艺术史将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