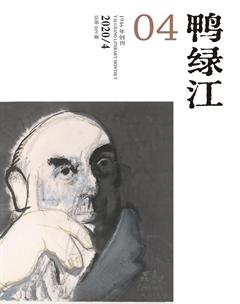疫情与乡情
名词解释:第一书记
是指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到村(一般为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担任党组织负责人的党员。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主要职责任务是帮助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2年以上,不占村“两委”班子职数,不参加换届选举。任职期间,原则上不承担派出单位工作,原人事关系、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党组织关系转到村,由县(市、区、旗)党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
名词解释:第一书记手记
本期开始设立的栏目,旨在记录奋斗在基层的第一书记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示中國乡村的真实现状与巨大变化。
早上从县里加了油出来,向村子里开去。
恍然间已经是下派到村里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了,从县城到村子,大概有十公里的样子。
县里的住处是我下派农村以后租住的,县城和我生活的城市大概有120多公里的距离,每周乘火车到一个叫大(读三声)虎山的地方,然后乘公交车到县城。说是公交车,当地的人们管它叫小客,是一种民营的公交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一般是人凑得差不多了才开车。如果人少,中间的站点有的时候还要等上一等,等坐的人多了才发车。
说起大虎山,听过这样的故事。1911年京奉铁路刚刚通车,这里就有了火车站。火车站的名字叫打虎山站。当时热河都统汤玉麟,是个性情鲁莽、脾气暴躁的军阀。他的部下为了马屁他,尊之为“虎将”。他自己也美滋滋的,经常以“虎将”自居。可是,背地里人们都叫他汤二虎。
有一天,汤玉麟坐火车去奉天(沈阳)。火车经过打虎山站停车了。他的手下人说:“打虎山站到了!”汤玉麟一听,马上火冒三丈,立刻变了脸色,大骂道:“他妈拉巴子!什么打虎山打虎山的,老子就是一只猛虎,看哪个有种的敢打?谁碰掉了老子一根汗毛,就得给我立一根旗杆!今后谁再敢把这儿叫打虎山,我就把他的眼珠子扣出来当泡儿踩,把他的脑瓜子揪下来当球踢!说话不算数,我就不叫汤二虎!”
从那以后,这个打虎山站,也就不得不改名叫作大虎山站了,但是当地人读音上还是读大(打)虎山。
我所在的村子在国道102线的边上,东边和北镇市交界。
村子的名字叫冯屯村,是由两个自然屯组成的,东边的是蒋屯村,西边的是冯屯村,加一起共有960人,人均只有2.3亩的耕地。在北方的农村中应该算不大的村子吧。
村子和北方大多数地方一样,以大田玉米为主,少量种植花生和大蒜。前年,也就是我刚刚下乡那年,赶上北方大旱,玉米很多都没有成熟。农民的辛苦付出,按照当地的话讲:白忙活了。去年几次台风登陆,北方也受到了波及,由于汛情的影响,大田作物都泡在水里了。还好,大田都有保险,我们村干部和保险公司拍照登记并上报理赔,部分地减少了村民的损失。这都是以前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农村的状况。
蒋屯、冯屯,你一定会觉得这两个村子是以蒋氏和冯氏的姓来命名的吧?你只猜对了一半。蒋屯村里的村民大多姓蒋,村子起名简直是把中国文字用到了极致,村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带个春字,三个字的名字,只有中间的一个字可选,而且还得保证不重复,这得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了吧。还好,村子里的起名规则只适用于男性。如果女人也按照这个格式来起名的话,想不重复都难了。再说冯屯,冯屯村奇就奇怪在没有冯姓的人家,大多是金姓。问过几位长者,都没人能说明原委。想来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吧。这里起名字的原则除了许多金某春这样的名字以外,还多了一个选择“奎”字,所以就多出了许多叫金某奎的人来。还好,这一现象在年轻人的名字里出现得少了。这应该也是时代特征吧。
最近由于疫情影响,村里主要工作就是在村口路边设置值班卡点,对外来的车辆和人口进行登记和扫码检测体温,同时,巡逻村里是否有秸秆焚烧的情况。
疫情值班的时候,我碰到了去年认识的一位村民。他种了十亩地果树,养了六头牛。因为果园紧挨着村委会,我经常能看到他在果园忙碌着,问过他收入情况,他无可奈何却又面带笑容告诉我:去年赔了五千多。不过养牛还好,价格行情还是比较稳定的。市场经济从经济供需角度看是科学了,从农民劳动付出而没有收获看又无法解释清楚。
从武汉封城到现在已经40多天了,村里的卡点也按上级的要求和部署同时值守了40多天。三月的北方还是有点冷,卡点就设置在路边,路的一侧是村子,另外一侧是一条小河,名字叫羊肠河。
夏季,河边的风景还是挺漂亮的。远处悠悠转动的风车,给河岸带来动感。今天刚到卡点,就看到河边来了两个画者在写生。画布上的景色轮廓已经清晰了,看来他们已经来好一会儿了。虽然我对艺术不在行,但对于艺术和搞艺术的人天生有亲近感。
有人说过,相对于自然来说,艺术是赝品。我无力反驳他人的观点,也不敢亵渎艺术的内涵。但我相信,艺术是自然情感的延伸,是自然和人类交流融合的凝聚。
昨天河面还封冻着,今天早晨已经能看到清澈的河水在汩汩流淌了。河岸边的冰层被水冲刷着,时不时掉落到水里,顺着河水向下游浮去。荡漾着波纹的河水清澈见底,水边尚未融化的冰层像被画笔涂过的一样,在岸边画出一条宽宽的白色的带子。早春的冰像雪,洁白,但不飞舞。
河边的杨树林还没有吐绿,但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摆动。河对岸的农家已经牵出了黄牛在河边放牧,地里的黄干草估计也是牛的食物吧。
天气还有些冷,但地已经解冻了。栽蒜的农民已经忙碌几天了。去年蒜农有一个很好的收获,今年又扩大了种蒜面积。村头地边的果树林,这几天一直在伐树,因为种果树收益不太好,果农把果树都伐掉了,卖给收树的人们去烧炭。
县城里,疫情初期有三例确诊病例,都是武汉返乡的人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县里的防疫工作一直很重视。前些天刚有一些放松,把村口的卡点变为移动巡逻,由于省内又有了新的确诊病例出现,各个村口的值守又恢复了。每天都有市县乡的领导检查,村里的广播整天播放疫情的通告。
和我们一起值班的,有一位村里的老通讯员,老人家是我下乡以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通讯员这个职务称呼,我都是在老电影里看到过,一般也都是年轻人。没想到在村子里还有这样的职务,感到好有艺术感和亲切感。在我第一次住到村部土炕的时候,就是这位老人家给我烧暖的热炕头。在好久没有住过的农家土炕上,那一夜我好久没睡,一会儿起来看看星星,一会儿又拿书来。在村部外面的路灯熄灭以后更难以入睡,听着外面的声响——有风声,还有庄稼摇动的声响,不知是新鲜感还是换了环境的原因,以至于从不失眠的我彻夜未眠。
老通讯员年近七旬,身体很好,对于村里的工作非常熟悉,是村里人所说的什么事都拿得起的人。老人家的性格与世无争,和历任的村干部都配合得不错,是村子里的明白人。疫情时期,他每天把桌子、椅子、宣传牌等卡点用的东西用他的三轮车拉到村口,并且悬挂好党旗,与轮流值班的村干部值守在岗位上。远远地就能看到飘扬的党旗和戴着红袖标的人,这也构成了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风景。
网上曾看过一篇专业的分析文章,说人有31天的警告疲劳期,人们紧张的神经会在时间的消磨中放松。具体数据不知道是否准确,但人们确实产生了放松的心理。几天前,市里又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再一次强调,要把疫情时期的扫码登记、车辆检查、体温检测重视起来。路過村口的车辆和村民也感叹:怎么又严格起来了?
极少吃方便面的我,现在每天都得吃一顿或两顿,有时候会咬上几口买来的馒头。因为防疫,乡里食堂已经不能就餐了,大家也都是临时凑合着。空闲时间上网浏览新闻,让人感触很多,非常自豪国家的医疗能力和管理机制,也庆幸国家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使病毒传播得到了控制。看着确诊病例越来越少,治愈的人数不断增加,让人们的抗疫信心也增强了。
在一年以前的防汛日子里,有一周的时间,我能黑天白天都窝在车里睡觉而不失眠。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像农民了。年轻时,经常听长辈人说年轻人需要锻炼,现在我觉得人什么时候都需要锻炼。人也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就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了。我想,这也是一种收获。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这次新冠肺炎对社会的影响不知会持续多久,对世界的影响会有多大,但我们应该牢记前方“战疫”的白衣天使们付出的艰辛。相比之下,在后方的我们,守护住乡土就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贡献。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海歌,原名刘为海,1965年出生于锦州,1996年入党。大专学历。锦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辽西区域文化研究会理事。供职于锦州世博园,担任场馆部部长,现为下派乡村的第一书记。
——献给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