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解读:五大亮点、六大关键词:看懂“肝癌诊疗新规范”

樊 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上海市肝肿瘤临床医学中心(重中之重)主任,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脏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我国是肝癌大国,有近全球一半的肝癌病例。2019年12月7日,在由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七届全国肝癌学术会议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正式发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于2011年首次发布,并于2017年进行了第一次更新。近两年,肝癌诊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创新药物也在我国肿瘤药物的准入和上市审批加快的大环境下进入肝癌治疗领域,非常有必要对《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进行更新,以便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统一的诊疗规范,更好地为肝癌病人提供优质、规范的诊疗服务。
新修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对普通读者而言,应当掌握哪些关键知识点?听听专家的分析。
亮点一:诊断标准与国际接轨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全面参照“2019版肝细胞癌WHO分级系统”,与国际标准接轨,以期通过制度革新进一步提升我国肝癌早期诊断率,全面提高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
亮点二:增加关注度高的肝癌筛查和诊断的内容
近两年,肝癌的早期诊断技术快速发展,“液体活检”在肿瘤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价等方面显现重要价值。肝癌恶性程度较高,早诊早治尤其重要。在我国,很多肝癌病人一经发现即为晚期,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预后不佳。《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指出,对血清甲胎蛋白阴性人群,可借助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和血浆游离微小核糖核酸进行早期诊断。目前,基于循环微小核糖核酸(miRNA)模型的肝癌检测试剂盒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已进入临床应用。
亮点三:外科治疗“升级”
近年来,我国肝癌外科治疗技术也取得明显进步。过去认为,存在门脉高压的肝癌病人不宜进行手术治疗。近两年,多项研究结果提示,经过选择的门脉高压病人仍可接受肝切除手术,其术后长期生存率优于接受其他治疗。《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将门脉高压精准评价作为筛选适合手术切除病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亮点四:强调系统治疗
系统治疗部分是《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更新的重点。对晚期肝癌病人而言,不仅要重视抗肿瘤治疗,还要重视抗病毒治疗及其他保肝治疗。有效的系统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近年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除老药索拉非尼外,在中国获批的一线治疗药物仑伐替尼、二线药物瑞戈非尼,以及在国外获批的二线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均对晚期肝癌病人有一定疗效。
亮点五:挖掘中国传统医学潜力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已提及肝癌病人可采用中医中药治疗,以改善症状,提高机体抵抗力,减轻不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指出,有1级证据显示,肝切除术后病人口服槐耳颗粒,可减少复发并延长生存期,这为中医药治疗肝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一:高危人群筛查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乙肝病毒感染、丙肝病毒感染、过度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者,是肝癌高危人群。为早期发现肝癌,宜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
关键词二:诊断方法
肝癌的诊断方法主要包括影像学检查、血清分子标志物和病理学检查。
超声检查是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常规超声可检出肝内占位性病变,并初步判断其性质;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观察病灶内的血供,还可以明确病灶性质。
经肝脏超声检查和血清甲胎蛋白筛查发现异常者,宜进行动态增强CT检查和多模态磁共振检查,以明确诊断。
PET/CT主要用于肿瘤分期,全面评价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也可以进行靶向治疗后的疗效评价。
血清甲胎蛋白(AFP)是目前诊断肝癌和疗效监测常用的指标。血清AFP≥400微克/升,在排除妊娠、慢性或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及消化道肿瘤的情况下,高度提示肝癌。仅60%~70%的肝癌病人表现为甲胎蛋白升高,30%~40%的肝癌病人甲胎蛋白始终不升高。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异常凝血酶原和血浆游离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检测有助于发现甲胎蛋白阴性的肝癌病人。
通常,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符合肝癌臨床诊断标准的病人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进行病灶穿刺活检,以减少肿瘤播散风险。对于缺乏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脏病灶,往往需要进行穿刺活检,以明确性质。
关键词三:手术治疗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指出,肝癌治疗应重视多学科协作(MDT)模式;特别是疑难、复杂病例的诊治,应避免单科治疗的局限性。
肝切除术是病人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其基本原则是:完整切除肿瘤,切缘无残留肿瘤,并保留足够体积且有功能的肝组织,以保证病人术后有较完备的肝功能。肝脏肿瘤巨大、剩余肝脏体积较小的病人,可采用术前经动脉化疗栓塞术使肿瘤缩小,或通过门静脉栓塞等技术使剩余肝脏代偿性增生,以提高切除率。对于不可切除的肝癌,可以采用术前经动脉化疗栓塞术、放疗等措施获得“降期”后再行切除。通常,肝癌病人还应接受适当的术后辅助治疗,以减少复发。
肝移植可以根治肝癌,尤其适用于肝功能失代偿、不适合手术切除及局部消融的早期肝癌病人。关于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推荐采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单个肿瘤直径≤6.5厘米;肿瘤≤3个,其中最大肿瘤的直径≤4.5厘米,且肿瘤直径总和≤8厘米;无大血管侵犯。
关键词四:非手术治疗
由于肝癌病人大多合并肝硬化,或者在确诊时已达中晚期,真正能获得手术切除机会的仅占20%~30%。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直接杀灭肿瘤的局部消融治疗,具有对肝功能影响小、创伤小、疗效确切等优点,使部分不适合手术切除的病人获得了根治机会。
经动脉化疗栓塞术也是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法之一,通过经肿瘤供血动脉灌注化疗药或用栓塞剂堵塞肝肿瘤的供血动脉,阻断肿瘤的血供,促使肿瘤坏死。
放疗对部分肝癌病人有一定效果,有助于改善症状,延长生存期。主要包括内放疗和外放疗两种:内放疗是将放射性核素植入肿瘤内进行治疗;外放疗是利用放疗设备产生的射线,从体外对肿瘤进行照射。
对晚期肝癌病人而言,有效的系统治疗有助于减轻肿瘤负荷,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一线治疗”包括靶向药物治疗和全身化疗,“二线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关键词五:中医中药治疗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中药治疗作为肝癌系统治疗的措施之一,包括汤药、现代中药制剂等中药治疗,以及针灸、穴位敷贴、拔罐、中药泡洗等中医特色疗法。
关键词六:抗病毒治疗
由于我国肝癌病人大多有乙肝病毒感染史,故《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建议,合并乙肝病毒感染,特别是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的肝癌病人,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抗病毒治疗。宜选择强效低耐药的口服核苷(酸)类似物,如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等。对丙肝病毒相关肝癌,如果有肝炎活动,也应接受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
延伸阅读:
40位肝癌病人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庆生”

2019年12月6日,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40位“新生命”超过“20岁”的肝癌病人唱起《歌声与微笑》,一起为肝研所“庆生”。他们中,生存40年以上的有3人,时间最长的已生存48年。
半个世纪前,权威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 当时,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术后病人5年生存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14%提高到如今的64%,创造了肝癌治疗的“奇迹”。
50年:从“小组”到“一流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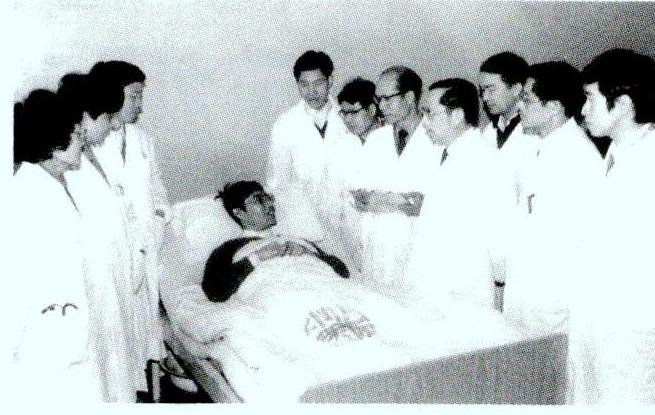
1969年,汤钊猷教授、余业勤教授、杨秉辉教授、周信达教授、林芷英教授等老一辈专家成立中山医院“肝肿瘤小组”。1988年,经卫生部批准成立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隶属于上海医科大学,下设肝癌内科、外科及实验室;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更名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简称“肝研所”)。在过去的50年里,肝癌诊疗领域的无数个“第一”在肝研所诞生。
汤钊猷院士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使肝癌从“不可治”变为“部分可治”;在国际上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论。“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及“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转移研究中的应用”分别获得1985年和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教授对肝癌肝移植、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进行系统研究,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制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成功转化并生产上市的“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实现签约转化的“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两项研发成果,均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例”。
现任肝外科主任周俭教授带领肝外科团队创新开展Alpps、废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着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继续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
“50年前,对于肝癌病人来说就是六个字——‘走进来、抬出去,短则几日、几周,长则几月,都走了。现在,可以用另外六个字来概括,就是‘走进来、走出去。”近90岁的汤钊猷院士感慨道。
50年:新起点、新征程

樊嘉院士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新发肝癌病人在中国。前辈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年轻医生进一步深入認识和研究肝癌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由于肝癌的复杂性和高度异质性,目前对肝癌的认识还不是非常全面,尤其是肝癌的早期诊断。未来,肝研所将继续加强“医、研、产”结合,不断提升肝癌治疗效果,为广大病人造福。
大众医学202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