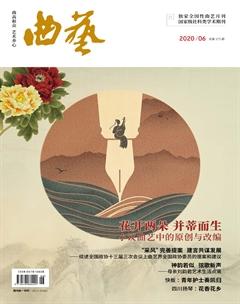新时代高品质曲艺生态建构思考
陈慰 巫志南
当前,曲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出总体式微的趋势,其原因在于曲艺过去依赖的生存环境有了变化。在新时代振兴和繁荣曲艺,并非要改变曲艺“说唱艺术”之本质,而是需要在全新社会历史条件下,优化甚至重构曲艺生态。本文从曲艺面临困境分析入手,尝试揭示变化中的曲艺生态环境和要素,进而从社会正向的价值定位、清晰有力的政策指引、以市场机制配置关键要素及社会道德环境建设等方面,阐述新时代曲艺生态建构的思路与方法。
一、曲艺独特而多元的价值分析
曲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按照吴文科说法,“曲艺在历史上不只是供人娱乐和精神审美的表演门类即单一的‘艺术之属,同时还是‘文化之舟‘文学之父和‘戏曲之母”①。吴文科在此指出了中国曲艺的双重价值:一是作为特定表演艺术门类的独特艺术价值——在供人娱乐的同时淬炼人们的审美精神;二是在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吴文科认为,“许多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在过去主要是依托曲艺化的口述表演来完成的……这使曲艺在其‘本体价值之外,还有着十分特殊的‘载体价值和‘母体价值” ②。这一观点能够得到中国章回体小说及《格萨尔王》等少数民族史诗的佐证,也可以从现今赫哲族伊玛堪等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和对其独特的文化传播、传承功能的观察和分析中加深理解。
除了上述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曲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社会价值,即更擅长用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讲述接地气的故事,在分理清浊、针砭时弊中起到抑恶扬善、引导群众、淳化风尚的社会效果。这表明,曲艺在践行和传播当代主流价值方面当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二、中国曲艺生态链变化趋势性判断
改革开放初期,曲艺在经济大改革、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开放的背景下,有过10多年阶段性繁荣,出现了群星灿烂、精品迭出、亿万群众热切期待的辉煌景象。但自20世纪末至今,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社会生产生活的总体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与数字网络技术深度融合几乎成为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社会各部类与时俱进、繁衍存续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曲艺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曲艺的生态链,与其他艺术样式的生态链基本类似,多由创作、表演、传播、传承等关键环节构成,但在古今之间,生态链各环节的侧重点及其表达方式已颇有不同。总的来说,传统曲艺业态与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生产体制基本适应,其生态链条的各个环节均有较浓重的“求温饱”气息。近现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活跃于会馆、书场、茶馆中的曲艺,已有小本微利经营之产业化端倪,不少曲种与城市休闲服务业进一步伴生发展,曲艺既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也从发展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反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以1949年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为标志,曲艺成为官方认定的独立艺术门类(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西化”影响,“虽然曲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有着广泛的消费市场和欣赏人群,但在当代艺术学科分类中却未被正式列入名录。” ③)。此后直至20世纪末,曲艺基本由原先“自生自灭求温饱”的“满天星”转变为政府主导和支持的“一团火”,国有曲艺院团和国有演出机构的出现,演员有了编制保障等,都是曲艺的社会地位显著上升的标志。这一时期,创作、表演、传播、传承的生态链主要以国有事业体制的方式出现。
20世纪末之前,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曲艺生态链中各环节之间的稳态关系及其运营方式并未有重大的变化。直到现代数字网络技术全面应用,这一稳态才真正被打破。网络技术推动着社会艺术产品需求和传播方式迅速变化,导致艺术授受的高低差被抹平,授受两端的交互界面迅速拓宽,而数字网络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出艺术领域潜在的社会化“财富效应”,使以往小本微利的经营生态相形见绌。其中,在数字网络技术条件下积极发挥市场化配置艺术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艺术生态得以改良或优化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因与广播电视的深度结合,曲艺曾一度红火,但传统事业生产和传播体制所形成的繁荣,主要表现在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方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不到必要的与市场运行一般水平相当的经济利益反哺,曲艺的社会效益也难以持久。有一部分曲艺人或借助在事业体制内积累的“名人效应”,或凭借较为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相对出色的创演运营能力,在市场中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但这还是少数。相当一部分处于市场环境中的艺术主体,或是主动地,或是委屈地向市场妥协,以便获得更为丰厚的利益回报,这些主体比重的逐步扩大及其力量的累积,已隐约勾勒出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传统主流曲艺事业渐渐模糊的轮廓和曲艺内在固有的艺术及社会价值逐步淡化的轨迹,并最终有可能转化为解构主流曲艺事业及千年优秀传统的负面力量。基于這一判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曲艺生态链重构已迫在眉睫。
三、中国曲艺生态衰变的基本症结
面对数字网络特别是新媒体、自媒体传播技术条件和产业环境,传统的实体经营业态确实显露出抗风险能力不足、营利手段单一等劣势。而过于宽松的“泛娱乐化”社会艺术环境,客观上凸显了与娱乐融合、以娱乐为主的所谓艺术样式,同步冲淡了文以载道、艺术养心的浓度。传统的“寓教于乐”为经济利益所绑架,正在异变为有利于“泛娱乐化”大行其道的合理借口,点缀在低俗、庸俗、媚俗令人沉迷之“乐”中的所谓“教”,成为对“向上向善”传统美德的无情讥刺。在世纪之交及至现今的一段时期,曲艺面对市场的纷乱芜杂,表现出些许“迷惘”,与“泛娱乐化”相适应的粗口俗段、搔首弄姿、生编硬造、畸形趣味则开始有所显现。
在此,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问题,即“曲艺是否在数字网络技术条件下或市场环境中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调研发现,苏州评弹在过去10多年间,不仅活跃在数百家茶馆中,即便是在包括苏州所辖各县市基层文化中心的书场中,每有演出仍然座无虚席。许多曲艺“两新”在小剧场大传媒协同建设方面作出探索,多地把优质曲艺产品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范畴,都在一定程度优化了优秀曲艺团队的生存环境。而近年来曲艺“圈粉”的成功案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曲艺这一古老的艺术样式并没有过时,艺术魅力仍然深厚,仍然拥有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
那么,导致曲艺这一优秀传统艺术总体衰退的症结何在?此前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较多相关研究,连丽如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关于文化和旅游部制定《曲艺传承发展计划》的访谈时,从茶馆等相伴行业角度考虑,提出要恢复“听众+茶馆+演员”模式,“把茶馆这种形态传承下来、光大起来” ④。吴文科从回归说唱艺术本体角度,认为“不属曲艺的歌舞、朗诵和表演唱等等,都曾被误作曲艺形式,致使‘戏剧化‘歌舞化与‘杂耍化等创演倾向一度盛行” ⑤。林玉婷从人才培养方式改进角度分析,认为“传统的拜师学艺以及口传心授的传授方法也不利于曲艺艺术的校园形式的规范教育模式的形成” ⑥。上述观点见仁见智,但若要系统性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症结,还需要把视角推移到更为宏观的层面。
关于曲艺难以替代之艺术特点和社会价值认识不足,是导致当前曲艺全行业定位不准、地位不稳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庞大的艺术族群中,曲艺寡众均可、远近咸宜的艺术特质十分突出,更兼有“短、平、快”的“轻骑兵”优势,既能登大雅之堂,亦可扎根民间、走乡串户,理应成为传播文明、教化社会、团结民众的利器。从文化艺术现代治理角度看,文化艺术客观上拥有价值、工具和对象三重属性,其中价值治理是“挈领而顿,百毛皆顺”的关键“领子”。
文化艺术的价值治理,说到底是不仅要牢固确立主流艺术的价值理性,更重要的是确立主流价值在文化艺术治理全过程各方面的领导权、主导权。在任何情况下文化艺术价值的社会体现,始终离不开特定意识形态主导,离不开特定时期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离不开增进社会文化认同,也离不开以提升民众精神文化素养为重心的“人的发展”这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治理无妨可以表述为文化艺术治理的政治维度。这一维度的丧失,必将引发艺术殿堂的崩塌、滑坡或持续下行。中国曲艺特有的“利器”功能,唯有在价值治理的前提下方能得到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倘若利器以“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握于低俗、庸俗、媚俗之“手”,则必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诚如古人所说“出无谓之言,行不必之事,不如其已” ⑦。
四、新时代高品质曲艺生态构建的路径分析
1.精准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推动曲艺事业高品质发展成为新时代赋予中国曲艺全行业的历史使命。所谓“高品质”,关键是在新时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新生态中找到中国曲艺存在的必要性,从而为新时代中国曲艺发展找准定位。自古以来,中国曲藝固有的以说唱艺术方式扎根民间、服务群众、劝善惩恶、教化社会的基本定位没有变,也无需改变,所要进一步“精准”拓展的是立足当代、反映现实,把握当今时代脉搏,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具体来说,中国曲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主动自觉地把中国曲艺作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艺术载体,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运用曲艺独特艺术方式,紧密结合当今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时俱进褒扬真善美、揭露假丑恶,正确代言民众诉求,及时引导社会舆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素养和文化认同。
2.完善政策。在中国,政策是发展的风向标,倘若政策指引不明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事实表明,以往较为单一的文化经济政策或艺术“精品”创作资助政策,对解决艺术主体走向市场面临的诸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曲艺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遭遇弱化、低俗化的现实,与相关宏观指导和管理政策、新型载体渠道扶持政策以及市场监管政策等不健全、不精准密切相关。宏观艺术环境市场化、金钱化必然导致社会艺术普遍趋向娱乐化、低俗化,在这一大背景中实施工程性重点扶持或细节性“抢救式”保护中国曲艺,实为舍本逐末、无济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艺术市场环境应同时具有政府主导和市场有序两大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特点,政府主导缺位则市场必定混乱,市场倘若陷入无序则客观上倒逼政策改革。与宏观层面相对应,微观层面相关政策对新型主流艺术主体、载体和渠道的扶持同样处于缺位状态,市场长期处于自然芜杂生长阶段,民众对所谓“艺术”是“香花”还是“毒草”长期处于无法回避又无力识别的无奈状态。事实上,“毒草”直接诉诸人们原始欲望,因而更具有诱惑力,更具有“劣币”对“良币”的驱逐力。新时代文化艺术治理的相关政策改革应当兼顾鼓励与限制两个方面:一是正向鼓励和扶持。政府所主导的社会或市场空间,应全面有利于坚持主流价值之“正能量”应用包括中国曲艺在内的各种文化艺术利器,用以对民众产生正向的引导力量,所有政府掌握的设施、资金、人才培育、传播载体渠道建设以及各种政策和管理资源,应全面倾斜于正确的方面。二是补上法律“断点”。在中国,推进现代治理的核心是“全面依法治国”,中国曲艺以及全部的文化艺术领域一概莫能置身于法律之外。所谓“宽容”,大概至多放宽至以隐私方式存在的原始欲望,任何文化艺术一旦进入传播,即同时承担起无法以各种借口解脱的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的全部责任,依法推进文化艺术治理应及时完善与这些责任相对应的法律文本或规定条文,以实质性推进全社会即每个个体“责任感”的真正确立。三是疏通道德评价“堵点”。各级党委、政府主导的对包括中国曲艺在内的道德判断缺位,是导致道德判断地位降低至以个体“良心”零碎化、偶然性存在的终极原因,也是社会上以所谓“审美判断”取代道德判断之“捣糨糊”现象的重要原因。包括中国曲艺在内的一切文化艺术,凡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即客观地负有社会道德责任。特定文化艺术服务,必须以符合特定法律底线为前提,但是符合法律底线也仅仅是获得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许可。只有符合社会道德判断准则的文化艺术服务,方能或应当得到社会道德倡导和支持。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在文化艺术服务领域加强道德评价,以政策倾斜方式,重新确立文化艺术服务的道德判断权威,采用因势利导的方式,打碎包括中国曲艺在内的各种优秀文化艺术还不能在全社会大行其道的道德“堵点”已然势在必行。
3.坚守本体。中国曲艺始于汉唐,盛于明清,是中华各民族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说唱艺术集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纳入国家艺术组织。口头说唱及辅助性的简单伴奏是中国曲艺的本体。吴文科强调,“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门类”“曲艺中的‘唱即‘说唱,与歌曲的‘歌唱和戏曲的‘扮唱有所不同” ⑧。任何艺术门类或样式存在的前提,均以其独有的艺术方式为本,“说唱”即是中国曲艺族群共同的艺术特征。“说唱艺术”可以借鉴其他表演艺术手段,也可以借用各种辅助艺术或技术,但离开了“说唱”之本,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坚守“说唱艺术”之本,是当前推进中国曲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为此应大力加强“说唱艺术”本体的研究,挖掘本质、分析特征、概括规律,为优秀说唱艺术传承建立成熟的艺术规范。
4.创新发展。坚守本体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中国曲艺说唱艺术本体有其不变的基本内核,但在特定时代,这一“本体”总是“此时此地”的,“本体”的“坚守”也总是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得到更充分地表达。进入新时代,推动中国曲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已显示出多个具体路径。如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中获得创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党委、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之一,中国曲艺的地方性、亲民性、灵活性、便利性等,较为适合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现实及长远需求特点,各级政府可借鉴苏州市政府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務的方式,在城乡社区设立公益书场,创办“苏州评弹学校”,推动“苏州评弹”等曲艺产品和服务进入基层文化服务。又如,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的方式获得创新发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打破“劣币驱逐良币”怪圈,加强社会和市场环境整治,扶持优秀曲艺产品的宏观政策举措外,还应积极顺应当下数字网络技术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全面转换的时代主潮,明确政策指引、聚焦行业主流、健全产业链条、完善支撑服务,推动中国曲艺以产业发展方式与数字网络科技及其传播手段深度融合,与城市地方特色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统筹规划、精心布局,扎实推进中国曲艺主流产业生态建构。后者在张家港、济南等城市均具备较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曲艺可在国家和相关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以“新时代中国曲艺生态试验区”建设为题,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各种优质资源,开展中国曲艺产业生态建构试点,推动“曲艺+传媒”“曲艺+旅游”“曲艺+研学”等产业和业态创新。
注释:
①②吴文科:《曲艺保护传承: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奋斗,向未来处眺望》,《中国文化报》,2018年6月20日,第6版。
③高翔:《论曲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院校曲艺人才培养模式思考》,《甘肃高师学报》2019年第3期,第109—112页。
④李晓、王美莹等:《传统曲艺“昨夜雨”,如何浇开“今日花”》,《光明日报》,2019年9月2日,第8版。
⑤吴文科:《曲艺创作生态变化启示——近年群文曲艺创演态势管谈》,《人民日报》,2016年9月16日,第8版。
⑥林玉婷:《浅谈传承和保护曲艺艺术的“三个结合”》,《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第27期,第69—70页。
⑦[宋]晁说之:《晁氏客语》,岳麓书社2005年版。
⑧吴文科:《曲艺——中华民族的瑰宝》,《人民政协报》,2019年9月23日,第11版。
(陈慰: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巫志南: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