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向的秘朵 考里斯马基的插花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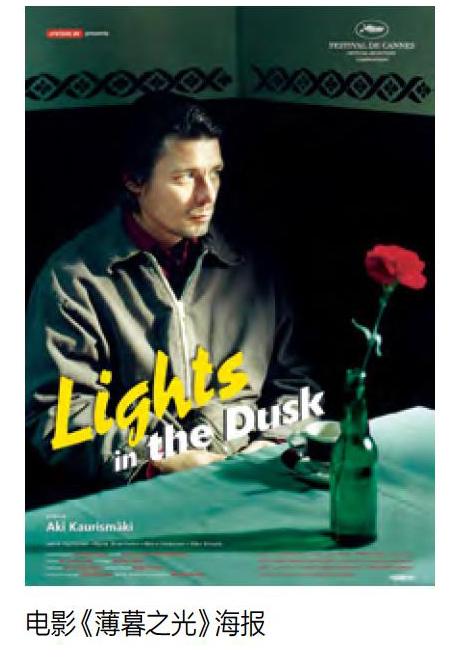

玫瑰的花期是5月,但记忆让人看到12月的玫瑰。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不仅是5月的玫瑰,也是12月的玫瑰。”他的花影投落下一句台词——缺席在他的叙事中与在场保持一致的关系。
复数附体.
据说,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每年5月份都会去葡萄牙,他和画家夫人每年一半时间住在葡萄牙自己的庄园。有电影评论家问阿基:你为何不选葡萄牙这个你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拍摄一部长片?阿基冷冷地回答:“尽管我在葡萄牙生活了20年,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葡萄牙人都在想些什么,也不懂他们的思维方式,那是我待过最神秘的国度。”阿基是那种在别的国度呆得越久,就越会热爱出发地的导演。他的热爱是没有时间性的,
比如他拍《吉马良斯》也是用阿基地缘性附体的方式,肿没有一句台词。
彼得.布鲁克3认为:“人是复数的存在。”阿基善于改编文学名著,他影片中的女性和男性都有另一个包法利夫人的面向,或者说是包法利的复数——一种日常的或喜剧版的包法利夫人。他们敢于在绝境里仍然保持自己所热爱的,不甘于庸常并沉浸在遐想中,甚至敢于为了自己热爱的事物打破既定的道德观念和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憎恶阶级色彩的阿基而言,热爱就是叛逆和放荡不羁。他热爱美国音乐,曾在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以扭秧歌的方式出现。同时,阿基的热爱也具有矛盾的一面,事实上,他更热爱于成为一名作家,但已经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超过了30年。他有些热爱是来于戒掉一些他更热爱的东西,并“推延自己的诞生”“我与我”以循环往复的语言强化了热爱的本身;在我与非我的热爱中制造了连贯性。“我热爱黄玫瑰,但我心中想的是康乃馨。”阿基的电影敢于热爱人性的所有弱点。其实,包法利已经超越了一个女性角色,她是一部收集了人性所有弱点的词典。
五月的玫瑰
欧洲抗疫期间,我收到意大利戏剧大师和诗人Giuliano Scabial的来信:‘“我的记忆保存了你的声音、手温、衣褶和眼神,房子提供了虚构的角度和此时彼刻,像颤抖的光一样活着。”他的记忆小心翼翼地收藏了我们多年前的在一起的场景,在读信时,我回想起考里斯马基谜一样的记忆与虚构。
考里斯马基的《没有过去的男人》讲述了一个失忆的男人,没有名字,亦没有过去,当他把自己找回来时,发现自己并非一个人,将面临着新的抉择。特朗斯特罗姆认为:“人受雇于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人之所以忠于记忆,在于他们拒绝杜撰生活。玫瑰的花期是5月,但记忆让人看到12月的玫瑰。即使玫瑰在6月末凋谢了,但玫瑰可以在12月的记忆中继续盛开。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不仅是5月的玫瑰,也是12月的玫瑰。”在“信息杂食”的时代,阿基坚守纯手工电影的他一直保持遗世而独立的怀旧质感。他拍当下的故事,但至今还未出现过智能手机和当今的车型。他持久的热爱就是受雇于记忆:永远忠实于流放、异化与孤绝。当下的世界,信息过剩引|发了知识焦虑和沟通路径的堵塞,但阿基依然在自己的复数中不断“完备有限”,去掉指向无限的空泛思维路径。
悉尽“一的变化”
“我也在等待着某人,但她从未出现过。”电影《薄暮之光》中的男主角坐在一株内向的康乃馨前的对白,这一幕召唤了少年时期的我朗诵诗作《如歌的行板》B的情景:“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这名过的女子随时有可能是阿基版的包法利夫人。
考里斯马基经常使用小津安二郎'式的镜头,有着日本情结的他喜欢在虚构的场景里插花,他似乎把他不理会的物哀和侘寂的要义转化到人性的层面。他的电影里总有各种花材入镜:樱花、蝴蝶兰、康乃馨、非洲菊、黄玫瑰、虞美人、花毛茛等,其中康乃馨的出镜率最多。考里斯马基悉尽放大“一的变化”之能事:他很多电影似乎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他的电影里永远不会缺少一家酒馆、一个乐队、一台唱机、一条狗、一个人、一支烟、一杯酒;他镜头中的花也是一枝花、一瓶花、一束花、一树樱花。孤独与花的强烈色彩的并置,产生了爱德华.霍普”的孤独感和丹麦隐士画家Vilhelm Hammershoi社会异化的图式,考里斯马基在复述现实的规律中解脱出来,花成为了重要的细节之一。考里斯马基说:“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面墙、一盏灯还有阴影。从画面里拿走女人,剩下男人、墙、灯还有阴影;再拿走男人,还有墙、灯、阴影;墙再拿走,还有灯和阴影;最后拿走灯,留下的只有阴影。”留下了的阴影是他的花影所投落的下一句台词——缺席在他的叙事中与在场保持了一致的关系。考里斯马基擅长以画面空白和静止镜头营造气氛,电影中的人物常常像雕塑一样沉默,演员永远保持冷面,举止僵而不硬。即使有台词,也是短句,他有意把发言的机会让给了花,盛花与投入派生出对白。世界有360度,为什么阿基要坚持1度呢?这正是阿基在更新“表象、热爱和花”要义。
偷花等女孩
考里斯马基喜欢在电影中重现他熱爱的事物,比如烟、酒和花。简约到不落痕迹的镜头中暗含考里斯马基向心的底色。在考里斯马基的“插花作品”中,《浮云世事》里的男主角在失业的时候给失业太太买白菊花,太太说:“这又是吹的什么风?”男主角夹着雪茄表示,没钱还是要出去下馆子;在《勒阿弗尔》里,马塞尔给病危的妻子带来一束康乃馨,说:“我没带吃的来。”“我才离开一会儿你就开始乱花钱了,”妻子喃喃道,马塞尔解释:“我买的很便宜,打折的那种……我说什么瞎话呢?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一种打折的)!”;在《薄暮之光》里,保安和骗子情人对着两支康乃馨吃甜甜圈状的面包和喝酒。考里斯马基的花和吃保持了上下文的关系,比如在吃一条头和尾都长着鱼头的鳟鱼上也有一朵花。片中的人物即使再困难和贫穷,家庭没有买花的预算,都不能缺少花,他们保持了对花的热爱和对季节的致意。
在《波希米亚生活》(La vie de boheme)里,考里斯马基描述过三个穷困潦倒的落魄文艺男青年,每次与女孩约会总.会出乱子,不是钱包被盗就是囊中羞涩。男主角在墓碑旁拿走祭奠死人的花准备送给她,她郑重其事地留下字条走了;从花园里采了一束花回去给她,她却不见了;女主角.说无法忍受贫穷,会无法呼吸。男的说:“要开窗吗?”女的说:“要做饭吗?”男的说:“不用,你负责从窗户看着公园(里的花)就可以了”。在其他片中,甚至还有男主角去花店里偷盗骗取鲜花,从白昼等到夜晚,他记忆中的女孩仍未出现。考里斯马基的叙事总是没有开始,无需结束,保持孩子的天性,单纯、无辜、木讷,并与当今的世界格格不入或沉浸在自己的视觉,如他片中的老人呼应了阿拉伯诗歌中的热爱信条:“梦也会长大成人,只不过是朝着童年的方向。”
蔽撼迷局
在考里斯马基第一部短片《撒谎者》里,阿基最后为了给心意的女子一束花而被枪杀。最后的电影镜头延续了戈达尔第一部电影长片《筋疲力尽》(Aboutdesouffle)里的角色,《撒谎者》里死后的男主角用眨着眼与空气交流,眼神穿过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五月天空。
此刻,我收到了秘鲁老友的来信——当今富有盛名的西班牙语诗人Renato Sandoval的来信,他说,要和我在这个疫情时刻交换居家照。于是,他发来了俏皮的室内肖像。他是在考里斯马基的居住地芬兰赫尔辛基完成罗曼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我记起了一个下午,Renato在酒馆给我们回忆起他受邀参加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的经历:一出机场就被一把枪指着……夜里,在下榻的酒店房间听到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墙身震动,门被撞开,另一把武器正在现身……但有些猝不及防的不纯动机是与人为善的,枪械如高跟鞋一样在提示着此地的危险和鲜花(麦德林有着漂亮的鲜花集市和四季如春安第斯山谷)。他笑着回忆一连串险象环生的经历,我深陷蔽撼迷局,但没有雷同陷阱。当我在阴险灰暗的叙事中走出酒馆,阳光刺眼,却领会了一种恐怖和不安全的深刻与考里斯马基式的冷幽默。Renato的回忆,是一部洗涤身心的惊险片,却与阿基的花影重合,慢慢映现了“热爱”一词中那些不为人知,鲜为人知,或以为知道却不甚了了的要义。
林江泉
Lam Kongchuen
电影导演、建筑师、作家、艺术家兼诗人,与曾东平合导的瑞典语故事长片《周日在越橘林》得到戛纳电影节评审卡普拉的助推。自2016年起,担任奥斯卡评委JetLee故事片《成人祭》的编剧。出版文学和设计著作多部,在欧美诸国举办个展超过20场,近期建筑设计项目有艾尔玛美术馆分馆、卡琳·布鲁斯美术馆,他的实践得到欧洲报刊、电台与电视台的广泛报道。
——谈《包法利夫人》的包法利
- 小资CHIC!ELEGANCE的其它文章
- 热爱和表象
- 五月,春光乍泄
- 我们的故事:独立音乐、绿皮车与冲浪文化
- 安静的人情味
- 今夜无人入睡
- 花与漆,一个热爱艺术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