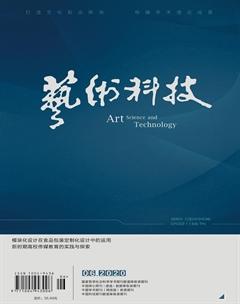浅析新故事叙事对“民间讲述”艺术的调用
摘 要:在确定了新故事的主题和题材之后,《故事会》的编辑们考虑通过怎样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道德教化的主题和日常生活的题材。由于大众阅读接受故事的出发点,一般都是为了欣赏、娱乐和调剂生活的需要,政治宣传式的故事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时期大众对故事的阅读期望。故事要吸引得住读者/听众才是第一要义,“民间讲述”传统艺术成为新故事叙事的调用资源。
关键词:《故事会》;新故事叙事;“民间讲述”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06-00-04
《故事会》从1980年第六期开始设置“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讨论专栏,并邀请“广大从事新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讨论的共识是“旧瓶装新酒”。这种在大众文艺实践中被证明能够受到大众广泛欢迎的有效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故事创作中被再次采用。这里的“旧瓶”指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一艺术形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一般具有新、奇、巧、趣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故事的情节密不可分,因此新故事能够广泛流传最主要的是调用民间故事中“奇异、巧妙的故事构思”。民间故事奇思妙想的结构特点既可以增强新故事写实性题材的情节性,[1]又可以使新故事道德教化的主题变得生动有趣,在寓教于乐中对大众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1 故事情节的传统民间取向
新故事中经常借鉴的传统民间文学中的情节有机智人物的故事、冒名顶替的故事、红娘的故事、清官的故事等等。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故事,如阿凡提智惩巴依老爷、巴拉根仓教训诺颜、巧女用智慧战胜国王、长工捉弄地主。这些传统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往往都是借助日常生活中的智慧战胜、惩罚或教戒恶人,展现人们憎恨丑恶事物、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表达了好人好报,坏人受惩罚的民间朴实的传统道德和憧憬。《三百元的故事》中,金梅运用巧计严惩贾大权,夺回300元钱的故事,正是借鉴了民间故事中“巧女”的情节构思。《巧巧三戏铲铲嘴》《急急火力挫智多星》《徐阿长巧夺欧米茄》《陈老总三搓黑田大佐》《金支书巧断猪头案》《犟姑娘巧设满月酒》《吴经理三战大篷车》等,故事的主题也都是勇敢、聪明和机智,最终战胜凶恶、狡猾和愚蠢。《患难之交》则采用了民间故事中常用的“冒名顶替”的情节结构,讲述了下乡知识青年夏博羽在洪水中救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潘义。随后却因为救姑娘薛凤莲而被洪水卷走,生死未卜,潘义却假冒“救命恩人”的身份向凤莲展开追求。死里逃生的夏博羽巧遇凤莲父女,最后真相大白,潘义虚伪搞破坏的行径被拆穿,善良肯吃苦的夏博羽和凤莲成为患难之交,“乱世年头分真伪,患难之交见真心”的故事主题也得到揭示。[2]传统民间故事中的“红娘牵线”的桥段也经常被用于新故事中。《三张失物招领启事》[3]中的男女主人公各自在单位中都是特别优秀的员工,女主人公施虹是曙光厂有名的质量检验员,男主人公李正高也是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两人第一次约会由于李正高迟到,施虹认为对方是诚意不够而不愿再谈下去,巧合的是李正高迟到是帮徒弟吴小牛校正零件,而吴小牛曾因扒窃施虹的皮夹子差点被众人殴打,幸亏施虹力排众议,让吴小牛逃过一顿毒打。正因为如此,吴小牛为师傅的姻缘当起了“红娘”,通过三张失物招领启事的妙招消除了李正高和施虹之间的误会,重新撮合了两人的姻缘。类似的红娘情节也在《书呆子恋爱记》[4](“书呆子”陈玉国和厂里的标兵模范陈玉眉的欢喜姻缘也是同事小李牵连成功)《师弟的姻缘》[5]等作品中反复出现。民间广受老百姓欢迎的还有为民除害的清官故事,也在新故事中被时常启用。《没脸的饭店》中司机野猫和个体饭店老板水壶为了赚钱暗中勾结,坑害旅客吃又贵又不卫生的餐饭,引起旅客群众的强烈不满。一个老工人站出来为旅客们主持公道,却遭到野猫和水壶的挑衅。故事最后揭示了老工人是省交通厅厅长的身份,由清官惩治了恶人。类似的现代清官故事还有《刘区长查案》《七号瓜的风波》《局长开车》等。
在情节结构组织方面,新故事中经常用到民间故事中的三迭式法、悬念法、误会法、巧合法等情节结构方式增强故事的“出奇”效果。“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故事,必须按生活的逻辑来构思,除了惊险的反特、破案故事外,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事往往比较平淡。在编写这类故事时,如何使情节构思‘出奇——奇而可信,可信而奇,就成了它拥有传诵者的生命所在。”[6]这些“传统的结构组织形式是由口头艺术发展而来的”,[7]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艺术审美接受基础。其中,中国许多家喻户晓的传统智斗故事常常结合的是“三迭式”情节结构,如“刘备三顾茅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三姐妹智斗狼外婆”。新故事里的《鬼讨债》中,阿珍分3次巧妙利用黄草纸逼着小华从矢口否认借过孙老太太的钱,到存有侥幸心理只承认借了100元钱,再到最终认错还债,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前面提到的《巧巧三戏铲铲嘴》《陈老总三搓黑田大佐》《吴经理三战大篷车》等智斗故事很多都是采用了三迭式的结构方式。悬念法是故事能够出奇的基本情节结构方式,《恐怖的脚步声》《走向“七0七”所的魔影》《五斗柜里的通缉令》《半夜奇案》等故事通过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来描写,情节惊险离奇,自然能抓住读者和听众。《书记盖房》则通过对马副书记盖房的误解展开故事情节的矛盾,直到最后误会解除,作者嘲弄一些党员干部搞不正之风的主题被点明出来。巧合法更是故事中常用的情节技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正是这个道理。例如,《九枚硬币》运用巧合来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男主人公薛亮在约会时,碰巧身边只剩9枚硬币,由于约会需要看电影、买雪糕、逛公园,薛亮一次次运用小聪明化解没钱的尴尬,一连串的巧合推进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平凡的生活小事变得妙趣横生。
故事往往采用相对完整的情节结构,一般都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同时讲求圆满性,以大团圆的喜剧方式结束。民间文学中的牛郎织女、梁祝等爱情故事虽然是悲剧的现实结局,但故事都以浪漫色彩给予老百姓积极乐观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审美及情感期待。《没有根的紫葡萄》里的主人公四嫂子以先富帶动后富的行为和思想,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真切愿望。
2 故事人物的“绘声绘色”
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多用对照法加以表现。传统民间故事里,常有两种不同心地、品格、地位的人物在同一事件上的行为对照,依靠人物在故事中的外貌行为举动来展示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例如,在《性命交关》中,作者首先运用传统口头文学中的“开相”手法,通过胖瘦对比的手法,一个是胖的“没有颈脖子,一只头是直接坐在肩膀上,当中有几圈肉螺丝连接”,瘦的“颈脖子又长又细,上面的青筋既粗又暴”。胖子夫人“也是个大块头,尺寸比丈夫还要大。她来到胖同志身边,一屁股坐下来,只听见咯吱一声,椅子脚抖了一抖”。当胖子夫妇发现得了癌症,就要求医生不仅要多开好药,而且为省被扣工资要求医生开5个月的病假,而这些要求是以自己厂里的新产品十六寸三速摇头台扇作为交换条件。当瘦老农以为自己患了癌症,首先想到的是要抢时间教村里的年轻人掌握种田的本领和窍门,教他们“富裕的日子要勤俭过”。这样通过夸张和对比的艺术手法将王副科长夫妇庸俗市侩的形象和辛勤劳作的老农形象鲜明地凸显出来。
新故事善于通过排比对人物形象进行集中烘托。如《合同队长》[8]中,“原来钱昌富过去搞家庭副业出了名,家里鸡子成群,兔子满笼,母猪一年四季不空圈,还养了两对进口良种绵羊,这是他的陆军;河里放鸭子养育塘里长菱种藕,这是他的海军;另有几箱蜜蜂,那是漫天飞舞的空军”,寥寥几句即把致富能手钱昌富的能耐进行了介绍。
故事的中心人物往往在不同思想立场的人物冲突中凸显出来,如《合同队长》中竞争大队队长的特定场景。
大队长周海平的老婆出场:“合同队长?没听说过!谁听过当干部订合同的?周海平犯了什么错误,让他靠边站?又搞文化革命啦!干部政策又不要啦!想当官也不能这种当法!点子想绝了!大家都说说公正话呀!”
钱昌富表明了态度:“我钱昌富不是来跟周海平队长抢官做的……可话要说清楚,要是大家都喜欢团在一起绑穷,对不起,把话说明了,往后我不敢奉陪。”钱昌富对公社党委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对党委有意见,干嘛要那么多干部,自己不懂脑筋,不想点子,不卖本事,光凭开会拿工分,耍嘴皮子拿钱呢?”
最后还是德高望重的老农会会长圆了场:“我看,钱昌富想为大家办点事,一年增加三个一百,不管怎么说都不坏,谁不想奔社会主义过好日子?搞四化谁有本事谁当官,不会做官的就当老百姓。就拿我来说,论党龄,跟钱昌富的年龄差不多;论本事,他那三个一百我没办法办得到。海平是我的外甥,他当队长过去是我推荐的,现在谁要是比他高明,我照推!”
生动地刻画了各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面貌:周海平老婆的撒泼和无理取闹、老会长的公正无私、公社书记思想的落伍僵化、钱昌富改革的勇敢魄力,将农村经济改革的困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3 故事语言的“民间味”
故事语言有着自己的特色,即语言的民间味。故事理论家蒋成瑀将这种民间味的特征概括为:简朴、机智、幽默和生动。[9]要口语化,顺畅,设置人物对话,创造表现人物性格风貌和情节进展的精简话语。一方面故事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另一方面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故事语言的民间特色,还体现在民间习语等的使用。习语是文化的载体,又是语言的精华。习语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协调,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俗语、俚语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精华表达的口语表达方式,它们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百家奴》[10]讲述的是生产队队长王大山经常为了大队的事情操心受到大山嫂的埋怨和误解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即用俗语点题,“俗话说,什么鼓配什么锣,什么老公配什么老婆。可是王大山和他的老婆就不是一个样,总是锣响鼓无声,敲不到一个点子上。什么原因?这得从王大山的外号‘百家奴说起”。为什么叫“百家奴”?是因为“王大山自从当上了生产队长之后,起早摸黑为大伙操心。碰上了三秋、三夏,收割、打谷、送粮,忙得饭也顾不上吃,晚上还常常在场上草堆里打呼噜,自己房里那半边床板常常是空的。老婆醒来摸不见人,恼火地骂他:你这个百家奴,还记得家吗?”开头用锣鼓敲不到一个点子上来比喻王大山夫妻关系的不和谐,不仅生动明了,而且富有民间风趣。而“百家奴”外号的由来,不仅快速勾勒出一个为了大队集体的利益而忽略了对自己小家庭关心的大队队长形象,而且故事的主题也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方式显示出来。
故事还经常在开头或结尾处使用民谣、对联等来引出故事或点明主题。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的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11]《银元祸》[12]的开头引用红山县近来流传的一首歌谣:“一块银元起风波,三家人亡家又破;汗水换钱钱是福,邪门捞钱钱是祸。”以歌谣的方式引入故事的主要情节,使人们急切地想了解红山县姓刘和姓沙的两户人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案子才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讲述的是红山县的沙大发偶然挖到了一块“袁大头”银元,恰巧被邻居刘喜财偷听,起了偷银元的心思。中间由于刘喜才的儿子刘二能也听到了有银元的事情,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故事的结尾以对联的方式回应了开头的悬念,“刘二能错杀他爹——钱迷心窍!沙大发赔钱丢娃——自讨苦吃”。综上,《故事会》中新故事的艺术风格,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曲折,生动幽默,语言采用短句,多用比喻,节奏感强,朴实上口,易记易传。
4 结语
新故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在官方群众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总要求其带有思想性,使阅读、讲述、听故事的人能从中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示。此外,由于大众的认知水平的限制和社会道德稳定结构的存在,一些独到见解、独特思想、独立个性的作品不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理解。而民间文化/文学中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和艺术形式由于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心理接受程度,从而被《故事会》上的新故事重新激发和启用。新故事一方面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能够及时反映社会动向,善于犀利辛辣地指出人們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针砭时弊;另一方面借鉴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描写现代生活,树立社会新风尚,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道德教化目的。
参考文献:
[1] 乌丙安.不胫而走的路——谈故事的流传性[J].故事会,1980(6):89-93.
[2] 欧阳德,萧金.患难之交[J].故事会,1981(3):1-9.
[3] 戴长鑫,经元度.三张失物招领启事[J].故事会,1981(6):34-38.
[4] “书呆子”恋爱记[J].小羽,搜集整理,故事会,1981(5):21-27.
[5] 周建顺.师弟的姻缘[J].故事会,1980(4):51-57.
[6] 陈勤建.故事艺术要以情节见长[J].故事会,1981(6):93-94.
[7] 蒋成瑀.故事创作漫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97.
[8] 关再兴,郁翔,肖鹤.合同队长[J].故事会,1981(1):1-6.
[9] 蒋成瑀.故事论语[J].故事会,1987(3):26.
[10] 陈堪进.百家奴[J].故事会,1982(4):50-60.
[11]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8.
[12] 王国全.银元祸[J].故事会,1982(6):16-25.
作者简介:蒋莉莉(1980—),女,江苏盐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