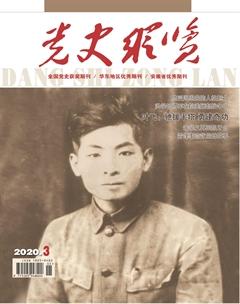解放区的抗疫运动
陈劲松



在中国这片充满苦难和辉煌的大地上,曾经爆发过无数次的疫情,从鼠疫、霍乱、天花,到疟疾、痢疾、脊髓灰质炎……疫魔肆虐时,从王公贵族到凡夫俗子,死于疫情的何止千千万,甚至是作为封建帝王的朱翊钧、福临、载淳等也没能躲过,可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无助的人们对天祷告,乞求上天的怜悯,但疫魔依然肆虐。直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切才得到彻底改变。这种改变不僅是夺取全国解放胜利之后“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开展抗疫斗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证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指出卫生工作事关红军的战斗力
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在阐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同时,也提出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卫生工作事关红军的战斗力和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积极性,要求苏区务必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全。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在军事第一的战争环境下,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何突然强调卫生工作呢?这还得从当时苏区所处的恶劣环境说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地处偏僻,山高林密草长,蚊虫孳生,且处于敌人的长期封锁下,缺医少药,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肆虐,被称为苏区的四大疾病。毛泽东曾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甚至毛泽东自己也感染了疟疾,不得不停下工作隐蔽休养,在当地名医吴修山老先生的精心诊治下才逐渐康复。
据古田会议以后成立的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回忆,当时中央苏区一年四季都有许多疟疾病人,死亡率较高,仅瑞金壬田区第一乡3个月就死亡80多人。痢疾也极为流行,每年死亡达几千人。宁都县被传染1300多人,死亡100多人,赣县的白路、良口、清溪“三区死亡极多”。下肢溃疡俗称烂疤子,就是小腿和脚溃疡流脓。得病根源主要是红军战士营养不良,血液毒素淤积,只要蚊虫叮咬用手一抓,或行军中被荆棘划破皮肤,破了一点皮就极易引起感染。溃疡面第一天只有铜钱大,第二天就能有酒盅大,第三天则有茶杯口大小了,溃烂深可见骨。此时若施救不及时,就会危及生命。1931年在湘赣苏区和红军中,有2000多人患上下肢溃疡;1932年在山上作战的红军一个团,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现下肢溃疡。由于长期行军,风餐露宿,洗衣洗澡根本谈不上,大家往往在路边和衣而眠相互取暖,疥疮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皮肤病就迅速蔓延开来。虽不危及生命,却奇痒无比,令人难以入睡,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
同时,当时人们生活陋习根深蒂固,封建迷信顽固不化,粪桶粪缸置于卧室,厕所猪圈连着水井,牛羊鸡鸭散放排污,疾病来了就焚香拜佛求神,野外叫天喊魂。加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烧杀掳掠,战死的士兵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腐烂于荒野,更是导致所过区域臭气熏天,污秽不堪。日积月累,1932年初,苏区瘟疫爆发,仅富田一带一天就死亡数十人,受传染者长则一两天,严重的甚至几个小时即死去。
红军和苏区政府高度重视“瘟疫”(苏区将霍乱、鼠疫、疟疾、痢疾等烈性传染病合称为瘟疫)的防控工作,军委设总军医处(后更名为红军总卫生部),各师、团、连相应设卫生长和卫生员,负责红军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控工作。苏维埃政府在内务部下设卫生管理局,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局长,县、区各设卫生科(委员会),面向工农群众,管理地方医院,做好卫生防疫、药品经销等工作。同时,设立红军卫生学校,按照毛泽东“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的指示精神,除培养医护人员外,还专门培养保健人才,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军地携手合作,打一场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他们张贴“瘟疫”防控禁令,刷写标语;办夜校、识字班,出版《健康报》《红色卫生》,在《红色中华》《红星》等党报党刊上刊发大量通俗易懂的疾病防控文章;编发《卫生常识》,介绍各类疾病的防治办法;宣传动员民众灭蝇灭蚊灭老鼠,住所通风通气透阳光,洗手洗脚洗衣被,喝开水吃熟食;隔离治疗传染病患者,火葬逝者,并成立卫生检查队进行督查;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引导规范民众的科学卫生生活行为。
为使疫情防控有章可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先后颁布《军委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苏区卫生运动纲要》,暂定霍乱、痢疾、天花、肠伤寒、流脑、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白喉为传染病,重点加以防范,强调开展卫生运动是为了增加革命的战斗力,是保卫苏维埃战斗任务的一部分。卫生工作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定期进行检查。这年秋,中央政府内务部要求各地设立诊疗所,免费替群众诊断开方。各县区的诊疗所、公共看病所、工农医院、药业合作社也纷纷成立。1934年元旦,《红色中华》对此作了专门报道,表扬福建才溪区的药业合作社聘请两位医生,免费为群众看病的先进事迹。鉴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严密封锁,苏区西药稀缺,医卫人员便组织群众上山采集草药,进行疫情防控,如用马齿苋治疗痢疾、常山治疗疟疾、硫磺治疗疥疮、烟叶水清洗下肢溃疡等,都起到了很好的疗效。
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效果显著,四大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阻止了流行病的蔓延,保证了苏区军民的健康。随着中央红军的长征,卫生防疫运动也在沿途各地开展。
陈毅指示给根据地老百姓看病“不要收钱”
抗战时期,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鱼水情深,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开展卫生防疫事业,保障根据地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巩固建设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因为地处江淮流域,河汊纵横,水网密布,各种流行疾病易发频发,尤其是疟疾发病率很高。由于医药匮乏、敌伪破坏,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1942年高邮和江都一个村庄,共500户死亡210多人;1943年江都又流行霍乱、伤寒及恶性疟疾,宝应流行黑热病、回归热,死亡率都极高。1945年春,淮泗、淮宝灾荒严重,又常遭日伪军抢掠,群众生活困苦,回归热、脑膜炎、雅司病广泛流行,死亡率极高。这些流行病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影响抗战大业。
新四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卫生事业,邀请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沈其震担任军医处长,动员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恽子强、江上峰、沈霁春、宫乃泉、齐仲桓、吴之理等众多高级医卫人才来新四军工作,甚至奥地利著名泌尿科和妇产科专家罗生特也来到新四军。在人才的支撑下,新四军建立各级医院,如军部医院、江南指挥部医院、江抗医院、挺进纵队医院、苏北指挥部医院等。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曾说,全军卫生机构建立后,即把保障部队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的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史沫特莱曾在《新四军的优秀的伤兵医院》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医院和救护站替军队兵士医病也替老百姓医病,平均每所医院一天总有二百个病人,大多数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求治的民众。”陈毅并指示新四军各级医疗机构,患病的老百姓“不仅要诊断,还要给药,但不要收钱”。
为支持地方卫生事业,新四军《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指示》中提出:“在可能范围内,抽调一些干部帮助政府先在根据地的大集镇内成立治疗机关。如县立医院、平民医院、卫生实验所、施诊所等,可以半施诊不求利的办法。如经济条件允许,能完全施诊施药则更佳。”淮南行署也作出规定:“门诊出诊不收费,药费比照私人药铺打8折至7折,困难户可以赊欠,抗属烈属优先诊病取药。”军地结合,华中根据地的各级医疗机构迅速建立健全起来,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皖南,新四军“1938年为驻地民众接种牛痘950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1886人次;1939年为驻地民众接種牛痘15416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4043人次;1940年为军民共接种牛痘8154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11330人次”。1945年春,泗宿县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淮泗县爆发回归热,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立即组织力量阻击施治。经过一个多月的严防死守,共诊治6135病例,扑灭了疫情。
为广泛深入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破除迷信,割除陋习,军地结合以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为主要内容,多次多地举办卫生防疫展览,以漫画、图片和显微镜下的实物镜头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讲,收到了很好效果。同时,团结民间中西医,奖励中药的改善,禁止巫医,管好游医,打击江湖骗子,严惩假医假药。第七师政委曾希圣听说无为名医何正宏思想比较进步,便把他请来,予以重用。何正宏不仅自己来到七师,还将自己医院的设备和药品全部捐献给了新四军。李步新、梁金华的枪伤就是他治愈的。鉴于部队和地方急需医卫干部,新四军先后举办6期医护人员培训班,培训近300名卫生干部,淮南行署开办了新医进修班。学员利用业余时间,向群众宣讲卫生常识,如不喝生水、不吃腐败的食物,拔除房前屋后的杂草,搞好环境卫生等。仅天长的保健堂,抗战胜利前的2年多时间里,就为群众诊治疾病6015人次,免费接种牛痘20561人,预防注射霍乱伤寒菌苗8638人次。
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核心地区,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欲除之而后快,日军为此不惜违背国际法发动细菌战。1943年11月2日《抗战日报》报道:“今春敌‘扫荡时,曾在屯兰川放了大批伤寒毒菌。入秋后病菌滋发,伤寒病蔓延各村。仅营立一个不满百户的村子,不到一个月便死了50余人。”同时,战争期间人口流动加剧,华北地区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有各级民主政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流入人口较多。老百姓长期以来的陈规陋习,封建迷信,也导致了疫病的进一步加剧。1945年5月11日《新华日报》曾刊文称:“疫病流行的原因,固然由于历年来敌人的迫害,人们的抵抗力减弱,而群众生活习惯不卫生,如衬衣很久不洗,乱吃生冷食物,茅房满街,虱子、跳蚤、蚊子、苍蝇任他繁殖,不加扑灭;好人与病人不愿隔离,小病认为不要紧,病重了也不赶快医治,个别人还请巫神祈祷,以致疾病蔓延,为害甚大。”因此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卫生防疫任务更加突出。
为深入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减轻群众的疾病痛苦,爱惜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根据地,根据地政府和部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据1944年6月《新华日报》(太行版)消息,山西林北“二区最近发生伤寒病很多,传染的(得)很厉害,害伤寒病654人,其他染病929人,平均约17人病1个,群众痛苦极深。5月23日,区署召开各村长卫生防疫座谈会,参加45人,决定各村成立防疫委员会,并介绍治疟疾、伤寒等病的方法”。贺龙曾回忆,在部队各级医疗机构的帮助下,根据地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医疗机构。同时,部队每到一地,都走访群众,遇到病人积极医治,并开展复诊送药活动。为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有效动员民间医卫力量,根据地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成立中西医救国会,组建各类医疗诊室,讨论如何应对日军“扫荡”中播撒的伤寒时疫,发动各界人士搜集土药筹集西药,义务为民诊治,折价给药。其中,民众医院和医疗合作社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都可以入股,开创政府、社会力量联合开办医卫公益事业的先河。根据地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宣传,结合具体的生动事例,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改变陋习。晋绥根据地王大贯一家6口人,其中5个人流行性感冒,2个多月都没好。行署卫生科医生张和轩听说后,前去问诊,才知他们家因为怕冷把窗门紧闭,空气不能流通,病人也没有专用的碗筷,导致全家交叉感染。张和轩对症下药,加以治疗,很快使病人的情况好转。青化区有个群众突然生病,耳朵附近发炎严重,日夜疼痛。他家花费几百元请了一个巫婆来治,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后经防疫队医生给他开刀打针,一分钱没花病就治好了。这些典型事例,给群众的启发性极大。
根据地军地共治,迅速阻止了各种流行病的蔓延,感染人群大幅度降低,树立了党和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准备了条件。
解放区的土窑洞研制出洋疫苗和抗毒素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快速推进,解放区在各根据地已有卫生防疫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传染病疫苗和抗毒素的研制使用工作。
虽然早在1933年红军即制订了《军委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暂定霍乱、痢疾、天花、鼠疫、白喉等为传染病,要求全军加以重点防范,但那时的主要措施还是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用牛痘苗作为毒种,试制出三四十万份痘苗,提供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预防天花,这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自行研制生产现代疫苗的先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独裁统治,面对其咄咄逼人的攻势,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大量的战争伤亡也将出现。同时,抗战中党领导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解放区扩大到近100万平方公里1亿人口,军队120多万。如果仅仅依靠从国统区秘密运输出来的一点疫苗,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些都要求解放区必须建立自己的疫苗研制生产机构。鉴于此,1946年冬,中央军委在瓦窑堡成立了军委卫生部试验所,主任由军委卫生部保健科科长李志中兼任,副主任周百其、翁远、姜恒明。李志中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是新中国生物制品创始人之一。
1947年3月,因胡宗南进攻延安,卫生试验所东渡黄河,迁到山西兴县吕家湾,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下设疫苗、痘苗、破伤风等实验室。就是在吕家湾的黄土窑洞里,卫生试验所生产出了痘苗、伤寒副伤寒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等生物制品。黄土高坡没有电更谈不上温箱,他们就用煤油灯保持实验室小孵箱的温度,用大窑洞里套小窑洞加烧炕的办法制作生产疫苗用的大孵箱,一次可以培养几万毫升的菌液;没有细菌过滤器,就用滤水器改制;没有测定毒力和抗菌素单位的小白鼠,就用敏感的家兔代替……克服种种困难,晋绥卫生试验所制造生产的痘苗,迅速提供给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边区;生产的破伤风抗毒素,每毫升含1000国际单位,质量远高于国统区同类产品的600国际单位。破伤风病毒最喜欢火药伤者,令野战医院生畏,在没有良药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眼睁睁看着受伤的战友感染死去。破伤风抗毒素的研制成功,为人民军队增添了必胜的信心。卫生试验所的艰苦有效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949年初晋绥军区给卫生试验所记集体一等功,授予姜恒明、周百其等研制人员“甲等人民功臣”光荣称号。此时,李志中已调到华北军区,组建华北防疫处,在河北正定生产部队和地方急需的破伤风抗毒素和牛痘苗。
解放战争后期,晋绥卫生试验所迁往兰州,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并与西北防疫处合并,成立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成为后来西北地区的免疫学研究中心。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重点经营的东北,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盘踞了14年之久的大本营。日军从东北败退时,撒播了大量病毒,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就将其做实验用的黄鼠等动物都放了出来,因此当地的卫生防疫任务更加艰巨。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进驻长春,立即按照预案接管长春卫生厂。这个厂的前身即是20世纪初期伍连德领导抗击东北鼠疫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科研实力较强,可以生产20多种医卫产品,都是人民军队所急需的。四平战役后,长春卫生厂与武田制药厂(东北制药厂前身)等7家单位一起撤到佳木斯,合并成立东北卫生技术总厂。当时,东北、内蒙古霍乱、鼠疫、伤寒等疫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从军队到地方都高度紧张,需要各种大量防治疫病的疫苗。东北卫生总厂因陋就简,用破旧的战争弃房,改造建设了大量实验室,从军队和地方招录一批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学徒工”,号召他们向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学习,一个日本“师傅”带几个中国“徒弟”,日本技术人员只有将中方人员教会了,才可申请回国。就这样,一个用心教,一个勤奋学,中方技术人员很快学会了生产霍乱疫苗、伤寒疫苗、鼠疫疫苗、白喉抗毒素等技术。为了生产前线部队急需的破伤风和气性坏疽血清,东北民主联军与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地下党组织联系,将已经被遣返的大连卫生研究所(日军侵占东北期间建设的重要细菌战研究机构)血清科长、日本医学专家贞子宪治从轮船上秘密请下来,送往佳木斯。在他的指导下,很快就把破伤风和气性坏疽血清研制出来。
东北卫生总厂生产的各种传染病疫苗和破伤风抗毒素,不仅阻击了东北疫情的蔓延,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而且被運往其他解放区,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进行。1948年长春二次解放,东北卫生总厂迁回长春,发展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成为东北地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中心。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卫生防疫事业,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新生事物,他们的发展壮大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大演习”,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