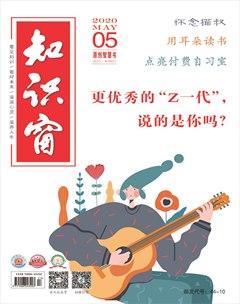入梦之梦
谭真
1.暖阳·花影
“reverie(梦幻)”“dreamlike(梦幻的)”“dream(梦想)”“strange(奇怪的)”“weird(怪异的)”“vague(模糊)”“obscure(晦涩的)”
“classmate(同学)”“panel(小组)”“cry out(大声喊)”“panel discussion(小组讨论)”“revolutionary(革命性的)”“define(下定义)”“be willing to(情愿)”
阳光透过蓝色窗帘,投射到墙上的挂钟,移动到黑板。指针指在上午八点二十分,上面十四个英语单词正在黑板上你追我赶、相互厮杀,我只能看见纯白的血在风中泼泼洒洒,像是白玉兰的花瓣在阳光下凄凄而落。
雨水节气刚过,楼下的玉兰花应该开得正好,更无须说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垂丝海棠了。可大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此时在教室中听写这些单调乏味的英语单词,其实是对大好春光的彻底亵渎。我环顾四周,想拉上一个人一同奔向楼下那一大片花的海洋。只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看清任何一个人的脸。
只有走廊尽头透出了一丝微光,我朝着背光处那个熟悉的人影走去。
2.又见故人
“这次生活艺术节的海报是哪个部门负责的?校团委宣传部,还是学生会宣传部?”
“应该是两个部门共同负责的吧,昨天我和两个部长刚在阶梯教室一起开完会。”我翻开手上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会议记录。
“那好,提醒一下他们,新增的几个项目海报一定要画得出彩。”
“OK.”我向她点了点头,准备下楼赏花。
“唐钰学姐,这次烹饪大赛和水果拼盘的食材报表也是交到你这里吗?”一个中等个子的女生向我们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扬了扬手上的A4纸。
透过玻璃窗,我终于看清了教室里老师的脸。高瘦个,干练的马尾,配上一副黑色的圆框眼镜。四五年过去了,彭老师还像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模样,一点儿也没变。
想到这里,我不禁露出了一个微笑,终于走到了楼梯口。
一楼的拐角处,“点歌信箱”还摆在消防栓上。实际上,我已经退出广播站很久了,只是一时兴起,又打开了信箱。
《考试什么的都去死吧》《稻香》《再见再见》……
果然,还是这些歌,翻来覆去地播放。
3.焱悠,焱悠
我跑出了教学楼,却没有看到任何一株垂丝海棠或白玉兰树,只是不远处有两棵小叶榕,旁边的木棉树上,一簇簇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我就這样望着那团火焰怔怔地出神,直到那火舌蔓上双肩,我才隐约感到哪里不对……
“快!紧急疏散!对面大楼发生了坠楼事故!”
“快!紧急疏散!对面大楼发生了坠楼事故……”
“砰砰砰!……”
“砰砰砰!……”
我在猛然惊醒的那一刻终于明白了哪里不对:唐钰、生活艺术节、阶梯教室、点歌信箱、榕树、木棉……包括彭老师!这些都是我高中时接触到的人和物,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大学校园?
4.入梦之梦
“砰砰砰!……”
“砰砰砰!……”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急促。
这一大清早的,又会是谁呢?
估计爸妈都还在睡觉,也好,我去开门吧。
“砰——”房门应声打开。
电光石火之间,一个棒球棍似的东西架在了我眼前。我看不清来人的脸,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一种应激反应,只能尝试拼命地高喊:“爸——妈——……爸——妈——”
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本来是大白天,楼道里却异常昏暗,只有老旧的声控灯时不时地发出一点幽微的光芒。农历年刚过,灯光映照得门上的洒金“福”字,更添了几分神异的色彩。我绕着这栋楼一直跑一直跑,拼了命地想要摆脱来人的追赶,却始终在即将脱离魔爪之时,重新回到最初的起点……
5.梦醒时分
不知道就这样过了多少个循环,我终于精疲力竭地准备放弃。目光慢慢从某户人家门前的红灯笼上收回,看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昏黄的街灯里,LED屏上滚动着一行红字,提醒着我今夕何夕:“2020年2月24日,庚子年二月初二。”
我,居家久矣。不知是梦,是醒。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