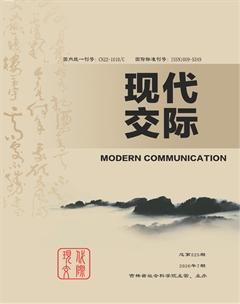索绪尔与叶尔姆斯列夫语言思想对比
费乔荣
摘要:如果说索绪尔所从事的研究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进行的普遍语言理论的确立,叶尔姆斯列夫所创立的语符学,则是以一座复杂的语言格式塔,借一套精美的语言图式来构建可能的语言关系理论。然而,追求以极简形式穷尽语言规律的语符学在国内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我们将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出发,结合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可以从二者的语言思想对比中走近语符学,进一步为现代语言理论研究寻找新的养料。
关键词:索绪尔 结构主义 叶尔姆斯列夫 语符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62-04
近年来,国内关于语符学的论著少之又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如果说,叶尔姆斯列夫是真正意义上将索绪尔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为何语符学会被束之高阁?针对这一问题,下文将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出发,进行对比分析。第一部分比对二者语言理论的产生背景和继承关系;第二部分分别从语言观、语言的真正研究对象、语言的符号结构和语言的功能/价值四个模块进行理论对比;第三部分结合二者语言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对国内对于二者的接受进行比较。
一、结构主义的真正继承
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遍语言理论一经发表就迎来了语言研究的热潮。“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方式”等重要概念的提出为语言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树立了新的时代环境下语言研究的基准。此前,语言研究经历了早期自古希腊古罗马生发的语法阶段、专注文献考订的语文学阶段、近现代的比较语言阶段。概括地说,从描写语言学到结构语言学的这一历程,人类一直试图理解“语言”这一既非物质又有形存在的“实体”的奥秘。语言学家所致力于探索的语言奥秘逐渐从单一语言描写自身过渡到了不同语言比较下的语言类型划分。然而,对语言的研究不局限于此。
早在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John Wilkins出过专著,设想了一种“哲学语言”。他的设想是存在“一套普遍適用的语言规则,使世界各民族都能够互相交流思想”[1]36;同时期的法国Port Royal学派也有过与之接近的思想,他们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上的一致性”[1]36。上述思想均体现了语言学家对于语言共同规律的探索,即从不同语言的表现形式中归纳出共性,从而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语言分析模式和语言模型本身。至此,索绪尔所树立的语言研究方法便成为一个出口。
由于索绪尔是将语言整体视为一个系统进行系统内部的结构研究,他所代表的语言理论被划归至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流派中,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而后,语言学开始结合语言的功能和心理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流派,语言研究走向了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其中,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思想。该学派主张用元数学、元逻辑的形式主义方法,建立起有限公理或公设,用以演绎语言当中的“曾经存在的现已消失的、现在存在将来可能消失的以及可能出现却永远也未必出现的各种语言现象”[2]3。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的继承人Bally在逝世前给叶尔姆斯列夫的信中曾说到“您在遵循着索绪尔的思想”,如索绪尔在讲稿结尾的那句话①:“语言学唯一的和真正的对象是在语言本身内部研究语言本身”[3]371。
索绪尔最先提出“要以结构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即通过列举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4]16,这与叶尔姆斯列夫一直以来对于语言的思考不谋而合。叶尔姆斯列夫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坦言受到了索绪尔的启示,表明他所要坚持的语言分析原则就是索绪尔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认为“把语言看作相互关系的模式来进行研究才是科学领域的主要任务”[4]16。由此,叶尔姆斯列夫为了与传统的语言研究方式划分界限,创立了语符学,专注于语言的内部形式研究。究其本质,是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一套高度形式化的普遍语言理论。
二、普遍语言理论对比
为了达成一套适用于所有语言的基本理论,索绪尔最先作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厘清了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以及同语言相关的可能的其他研究范畴,界定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两大门类。最终,索绪尔将自己对于语言一般理论的研究划定在共识语言学的平面上,认为语言的真正研究对象应该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进行的研究”,即针对他所区分出的“语言”的一般规律研究。叶尔姆斯列夫恰恰延续了索绪尔的这些语言思想,具体我们将从二者的语言观念、语言研究对象的确立,以及各自建立的符号结构模型和价值/功能系统来进行分析。
1.语言观
如何看待语言会影响语言研究所采用的方式,因此,对语言学家语言思想的了解应该先从他们的语言观进行切入,这是“语言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最基本的认识”[5]60。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符号系统,且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个维度的心理范畴的结合。在他看来,语言是社会的、具备一定规约性的历史产物。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多次提到了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丰富了这一语言的人文定义。此外,语言是一个系统,这意味着语言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分析的原则,也奠定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语言研究方式。再回到索绪尔最为人所周知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一论述,决定了索绪尔最重要的语言观念是把语言看作一种心理形式而非实体。
叶尔姆斯列夫对语言的认识更加概念化。基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他在分析过程中明确提出了语言的三个理解维度:作为纯形式的语言(une forme pure/shéma)、作为质料形式的语言(une forme matérielle/norme)和作为整体社会习惯的语言(un ensemble des haibitudes/usage)[6]32。这体现了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在关于“语言是形式”“语言具有社会性和规约性”这些基本理解上的一致。我们常看到在诸多文献资料中引用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绪论》[7]中开篇部分对语言的感性认识作为他语言观念理解的出口。事实上,叶尔姆斯列夫虽没有直接地给出关于语言比较简明的定义,但在他的语言分析中有多次强调: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念。在叶尔姆斯列夫看来,语言不能被描述为纯粹的符号系统,且这样的语言定义依然会涉及语言的外部功能。因为“根据目标特征,语言首先是符号系统;但根据内部结构,语言首先是可以用来构建符号的符号成分系统”[8]165,后者才是涉及语言真正内部功能的定义。
简单地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层级符号观”存在将语言最本质要素视为一种内部功能的定义方式,但二者对语言最小要素的理解尚有不同。
2.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研究任务是对所有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各个语言的历史,寻求所有语言的一般规律,以及确定自身的范围和定义[3]21。显然,第一个任务在索绪尔之前,不乏大量的语言学家在为之努力并卓有建树,而第二和第三个任务依然需要明确进一步探索。因此,索绪尔首先从语言材料中划定了语言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是这些形象可以捉摸的形式。换言之,人们可感受的语言的“实体”是声音,文字居于附属地位,但同时又以最有效的方式表示着语言。最终,可感的语音和可触的文字都应该在语言研究中作为基本质料。此外,索绪尔区分了集体的“语言”和个体的“言语”。前者是有限的语言规律,决定后者成为无限的语言表现形式。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作为一般规律的“语言”。
叶尔姆斯列夫同样将语言的研究对象划定在“语言”的范畴,认为语言研究应该是除物理、生理、心理等因素之外(或者至少将这些因素不放在语言研究最为重要的位置上)的本体研究。在他看来,这些现象只是“语言外部的一个层面,和语言不是直接关联”[8]122。语言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规范,表现为每一个个体对语言的应用。语言研究应该从具体的语言应用着手,再到语言一般规律的探索。因此,叶尔姆斯列夫所做的是将语篇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建立一种真正接近语言内部性质的本体语言学。
从二者的研究对象来看似乎存在某种对立,索绪尔是集体的“语言”,叶尔姆斯列夫是个体的“语篇”。但应该看到,索绪尔进行的集体意义上的语言研究也是从语言的一般表现(即语篇)中获取材料,叶尔姆斯列夫对个体的语篇研究也是以具有广泛性的语篇为代表。另外,从叶尔姆斯列夫在对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語”(Langue et Parole)这两个概念的分析过程中重建的术语“图式和应用”(Shéma② et Usage)的对应关系[6]43-44来看,二者看似矛盾的研究对象在研究目的上却是同一的。索绪尔是作为系统的语言,叶尔姆斯列夫是作为一种纯形式的语言图示,二者只是以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去探索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即更接近语言本质的、作为集体的语言的一般规律。
3.语言的符号结构
语言是一个有限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如索绪尔所言的“语言不是一个分类命名集”,以及洪堡特所言的“语言是有限域的无限应用”都说明了,语言学家们基本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语言内部存在有限的相对确定的要素,进而相互组合达成无限意义的生成。换言之,作为语言关系系统中的构成要素,符号,毋宁说构成符号的基本单位,是有限的。至此,移交到语言学家身上的任务就转化为:符号的最小单位,以及符号间的组合规律探索。从这点来看,叶尔姆斯列夫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思想,但二者对于符号的界定尚有不同。
索绪尔将语言视作一个由声音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的符号系统,符号是语词和心理上一种对应关系[3]98。这一观念提供了对于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的理解,但未能将语言的基本质料全部囊括进系统中,且没能就此析取出语言内部的最小单位。作为系统内部的组合关系,符号不单单是理解“语言是形式”这一命题的原则,符号在语言系统内部也是有语言要素作为依托的。叶尔姆斯列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将语言符号进行细分,进而抽离出更小的语言单位。
为了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符号作为语言的内部要素,需要不断生成去满足语言的发展变化。而无限的符号是需要由有限的符号成分获得,这样的符号成分便可以作为符号的局部进入符号系统[8]165。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深化这一语言原则,将符号划分为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表达平面指的是我们的语言,包涵了表达实体(可感知的语音/文字)和表达形式(语音/文字组合形式);内容平面对应的是我们的思维,结合了内容实体(事物,或思维混沌体)和内容形式(对事物的认识,或思维清晰化的方式)。这样看来,有关符号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的分析不单单回应了索绪尔最早预言的“语言学不过是符号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同时将语言符号在思维和语言两个平面上进行联系,进一步在语言平面上抽象出语言表达的形式单位。就此,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和叶尔姆斯列夫侧重的语言形式研究就联系在了一起。后者通过表达平面的分解,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分离,进一步研究语言的组合形式。
4.语言的价值/功能系统
关于索绪尔“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一论述有很多误读,我们容易从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产物时刻处于社会环境中应时代所需变化着这样一种历时的观点去考量,认为语言内部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索绪尔所言是从共时角度出发的作为一般规律的语言。就语言系统来看,符号本身具有价值,而价值是由一个符号相对于其他符号差别性的意义构成。即就是说,语言系统内部的符号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相对的,是基于差别建立的。那么从语言应用中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基本原则:语言是一个形式化的符号间的关系系统。
从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中的定义方法不难看出,他与索绪尔对语言价值的理解存在相似的地方。他认为,“在理论的形式化定义中,问题的关键不是穷尽对象的内涵本质,也不是界定对象的所有外延,而只是定出对象和其他对象之间的确切位置,这些关联的对象或被定义、或被当作前提来定义其他概念”[8]140。正如逻辑学中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我们很难直接认识孤立的事物,同样不能对其价值和性质进行单一的界定。索绪尔将符号的价值划定在差别性的意义之中,从而明确语言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价值系统。叶尔姆斯列夫则是引入了功能这个概念,进一步表示符号在语言中的作用是通过功能体现的。
概念是具有排他性的,我们只能在区别中把握具体的意义。符号的价值/功能同样是具有排他性的,而差别恰恰意味着联系。索绪尔的价值和叶尔姆斯列夫的功能都是对语言系统的差别进行描述,从而得出语言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因此,语言系统归根到底还是不同符号间形成的有限的相对确定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在差别中得以建立,经由不同的组合关系丰富其外延。
结合上文中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在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思想异同中总结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二者进行的语言研究排除了其他相关的领域,均进行语言本体研究。他们语言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的切入点)虽有不同,但从研究目的来看,都是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一种分析的原则进行探索,从而确立语言的真正研究对象,即属于语言的一般的内在规律的探寻。第二,二者均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索绪尔从语言的理解上提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一个以符号为载体的关系系统。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将符号概念进行细分,形成了更加完整的语言符号模型。此外,需要补充的是,二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是纯理性的。索绪尔所建立的语言分析原则(如音位学原理等章节)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能够穷尽的、最简理论均运用了数理逻辑试图探索语言的最简结构。
三、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对比与思考
总的来看,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从对语言符号观念的理解,到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的判断,再到作为一种普遍规律的“关系”的阐释,这样一条“把语言视作人类一切符号系统的中心,语言学作为更为广泛的符号学基础的语言符号研究模式”的道路是相通的。因此,应该肯定地说,叶尔姆斯列夫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和研究模式。这种继承,最大限度地表现在后者认同“语言是一个由有限要素构成的关系系统”这一概念。不同的是,一方面,叶尔姆斯列夫将有限要素,即索绪尔关于语言定义中的“符号”概念进一步分解,圈定了语言质料的最小单位。另一方面,关于这些基本单位的组合形式,叶尔姆斯列夫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关系模型,推进了索绪尔的语言关系理论。
综合二者在语言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理论上的突破不可置否,但距离一套切实可行的“一般理论”的实现,依然有些高屋建瓴的意味。反之,乔姆斯基所建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在当代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股潮流,便是因为理论的具体化。有人会说,乔姆斯基的語言结构图示是抽象的,但归根到底,他的语言关系思想是具体的。即语言质料可以通过相互转换的方式套用在有限的最简结构模型中。尽管乔姆斯基的这一套不断修正的语言理论在现代会受到质疑,但无疑是语言理论模型建立上的一次有效尝试。反观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主要代表的语符学,在所构建的语言结构模型中将索绪尔的一般语言理论推向了极致。但应该看到,语符学所致力于探寻的可以穷尽的最简理论恰恰体现了一个悖论:在纷杂的语言中确立一种普遍理论并达到最简本身只能是一种追求。用数学中的概念解释,最接近1的数字本身是一个无穷尽的有理数。我们无法给定一个具体的数值,但这个数值似乎又是可描述的。因此,从更高一级的概念来看,索绪尔追寻的普遍语言理论是以普适程度为前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构建的普遍语言理论却是以高度程式化的最简理论的建立为目标,实则是一种背离。同样应该看到,语言的研究视角尚且是多元的,语言学家对于普遍语言理论的探寻方式自然有别。
四、结语
本文对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语言思想的对比分析集中在基本的语言观念上,真正的理论对比不一而足。从索绪尔的普遍语言理论到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格式塔,既是基本语言观念上的继承,又是以自身语言研究目标为导向的发展性的背离。但笔者相信,若语符学不再因其内部理论的“复杂性”和“形式化”被贴上永恒的无用标签,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现代语言学提供新的养料。
注释:
①法语原文:La linguistique a pour unique et véritable objet la langue envisagée en elle-même et pour elle-même。
②叶尔姆斯列夫早期也将Shéma一词表示为Système。
参考文献: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2]王德福.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Paris:?dition Payot&Rivages,1997.
[4]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J].语言学资料,1962(11):16-19.
(下转第61页)(上接第64页)
[5]颜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观[J].渤海大学学报,2005(4):60-63.
[6]Louis Hjelmslev.Langue et Parole[J].Cac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1942(2):29-44.
[7]Louis Hjelmslev.Principes de Grammaire Générale[M].Copenhague,1928.
[8]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9]戚雨村,龚放.Hjelmslev和语符学理论[J].外国语,2004(4):26-33.
[10].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J].学术研究,1996(12):35-40.
[11]周光亚.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C]//外国语文论丛:第8辑.《外国语文论丛》编辑部,2018:63-72.
[12]David Holdcroft.Saussure,Signs,System and Arbitrarines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丁信善.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观的形成与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368-376.
[14]乐眉云.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J].外国语,1997(4):5-10.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