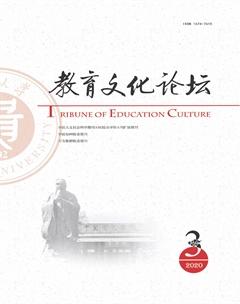越文化视域下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
华建新
摘 要: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追根溯源是受到越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孝道、易道、士道之文化内核成為阳明心学孕育与发展的丰富土壤。王阳明晚年居越城六年,虽身处逆境,但其通过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书信交流及山水游历等途径,兴起了一场以倡明“万物一体”学说为指归的王学振兴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万物一体”学说的提出,最终圆通了阳明心学体系,扩充了阳明心学的境界,标志着王学发展进入最辉煌的阶段。王阳明晚年在越城的传道活动,对于越中王门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对于彰显越文化的时代精神则是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关键词:越文化;阳明心学;勃兴;流播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3-0049-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3.007
Abstract:In the early years Jiajing era of Ming Dynasty, the rise and spread of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in Yuezhong are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Yue culture. The cultural core of filial piety, Yi Dao and Shi Dao became the fertile soil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WANG Yangming lived in Yuecheng for six years in his later years. Although he was in adversity, he raised a movement, with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in terms of scale and impact, of revitalizing ideology of mind which advocated the doctrine of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 through writing books, lectures and discussion, letters exchanges, and travel.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finally completed the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system and expanded the realm of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WANG Yangmings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Yuecheng in his later years had a huge appeal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 academic school in Yuezhong area, and injected a strong vitality into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of era in the Yue culture.
Key words:Yue culture;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rise; spread
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奏请朝廷省亲获准,自此告别戎马生涯,回到浙江老家,居家讲学,“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 (《归兴》其一)[1]784。其在越
中①
开展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通过各种讲会,专论“万物同体”之旨,并将心学理论概括为王门“四句教”,弟子盈门,蔚为大观。至此,阳明心学渐入佳境,体系完备,逻辑严密,中位圆通。其弟子编辑、刊刻其语录、著述等,心学思想大力传播,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声名远播大江南北。及至嘉靖六年(1527),广西土司叛乱,王阳明在国家危难之秋,奉命出征两广,不幸在回军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大庾(1529)。王阳明的弟子及后学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学脉绵绵不绝,“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本文探讨阳明心学在嘉靖初年越中的勃兴与流播及其与越文化内在精神气韵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希望对深化阳明学地域文化研究有所帮助。
一、越中文脉:孕育与浸润
王阳明于明成化八年(1472)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市),上推其迁姚始祖以下共十代,均在余姚生活,如果按三十年为一代计算,“越文化”传统对其家族的流脉影响约三百年
本文所指的“越文化”是基于越中风土民情之上的文化传统,是狭义的:从时间上来说,以“舜文化”传说为始点;从空间上说,以春秋以来越文化圈为界限。。具体到越文化对王阳明成长及其阳明心学思想的孕育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孝道濡化
王阳明的孝德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成为“三不朽”人物的根基所在。王阳明的孝德思想源于远古舜文化的孝德传统,应该也包含东晋以来越中“曹娥文化”的影响
曹娥文化:此指《后汉书·孝女曹娥》中所载的“曹娥”故事,延续近两千年的慈孝文化现象。。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的孝风懿德,亦是王阳明孝德思想产生的直接渊源。王阳明自身对孝德的体认和践行,是其孝德思想发展与成熟的最根本原因。
王阳明从小生活在山水秀丽的古城余姚,枕四明山而濒杭州湾,姚江穿城而东流,山水形胜,文化昌盛,素有“东南名邑”“文献名邦”之称。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相传虞舜时期,余姚为舜后支庶所封之地。因舜的孝德形象,成为历代姚人的道德楷模,舜的“孝道”精神被姚人所推崇,以至于姚江贯穿城区的一段被后人命名为“舜江”。关于舜的传说,诸如姚丘山、历山、象田、舜井等流传至今,至于地方志中有关舜的故事记载之多,无须多说。孝道源于血缘基因,其文化内核是“孝德”之伦理精神。百善以“孝”为先,形成姚地“孝悌”至上的淳朴民风。王阳明出生、成长在孝风盛行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这对其一生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王阳明《传习录》等心学著作中可找到诸多关于舜的论述,即为明证。余姚是王阳明的血脉之地,深厚的孝文化传统濡化了王阳明。据有关文献记载,王阳明血脉所系的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其祖上奉行儒家处世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忠、孝、悌、忍、信,讲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诸如王阳明之父王华,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考中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传承家族慈孝之风,以身垂范,孝道立身、立族,言行一致,忠孝两全,堪称楷模。王华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他的慈孝风范,对其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华对家族成员的教育重在孝德的训导,并内化为家族的礼仪门风。作为其长子的王阳明深受其教育与影响,并贯穿于一生的道德实践之中。
就王阳明本身的孝德践行而言,在做官与孝道之间,其往往是倾向后者的。在其仕途生涯中,王阳明因屡建奇功,朝廷多有封賞,但其总是请辞。其不恋官位,十多次上奏辞官归乡,要求照顾年近百岁的祖母和年迈的老父,以尽晚辈侍奉之责。王阳明在江西平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之时,因战情十分危急,生怕远在越城的老父担忧,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之际,写信及时禀报老父,以免老父担心、急坏身子。时至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遵旨赴京途中受阻后,随即奏请朝廷要求归乡省亲获准,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侍奉老父的心愿。从一定意义上说,回家侍奉老父这一孝行,为其晚年完善和传播心学思想提供了契机。由此可见,王阳明将人伦道德看作是人生最基本的品行,这是其道德本性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的孝德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内核,其强烈的孝亲伦理意识,贯穿其生命的始终,为其晚年居越讲学期间完善心学思想与传播学说奠定了道德基础。
2.易道滋养
在越文化精神中,始终贯穿着求新求变的文化脉络。春秋时期,勾践在吴越争霸中“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反败为胜自不必说。南宋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亦说:“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明末清初名臣、文学家绍兴人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现代大文豪鲁迅在《越铎日报》发刊词中说:“于越……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说明越文化精神中具有一种刚毅坚忍的特质,这种文化品质应该与越中重《易经》的传统有关。《易经》为六经之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石,就越文化而言,主要体现在解读与应用上。
易学在越中的传承,也可从王阳明先世治《易》家学传统窥见一斑。《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王阳明高祖),讳与准,精《礼》《易》,尝著《易微》数千言。永乐间,朝廷举遗逸,不起,号遁石翁。”[1]1 220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上》载:“王阳明曾祖王杰(清乾隆《余姚县志》案:杰字世杰,以字行)著有《周易说》四卷、《春秋说》五卷、《周礼考正》六卷。”[2]《年谱》中关于王阳明祖父王天叙的记载:“祖讳天叙,号竹轩,魏尝斋瀚尝立传,叙其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所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1]1 220王阳明父王华以“布衣魁天下”,对《易经》也颇有造诣。《易经》作为王氏家族的家学,养成了王阳明锐意进取、淡泊名利、洒脱超然的性格,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明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王阳明为救援被阉党刘瑾迫害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监察御史薄彦徽等人,冒杀身之祸,挺身而出,率先上疏救援,请求正德皇帝予以宽宥。王阳明的抗疏,激怒了阉党头目刘瑾,被廷杖四十后,投入锦衣卫大牢。下狱后,王阳明在铁窗中度过了暗无天日的漫长冬日。在狱中,其读《易》不辍,从圣贤的思想中汲取力量,立志倡明圣学。次年初(1507),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任驿丞,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谪旅之途,途中赋《泛海》诗言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684诗风超然凌空。正德三年(1508)春,谪旅至贵州龙场后,王阳明在小山洞中“玩易”,静思参悟,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由此可见,易学不仅构成了越文化的精神传统,亦是王阳明在人生之路上跋涉的精神动能。也可以这样说,易学就像流动的文化血脉,贯穿越城的历史和余姚王氏的家史,易学成为阳明心学的一股巨大的源头活水。
3.士道胸次
“越文化”中成规模的教化活动应肇始于春秋时期勾践的“十年教训”,其后教化形式发展多样,形成了官学与私学并流的传统。自隋朝开科举以降,官学为朝廷培养治国专门人才,而私学侧重于道德伦理层面的教育。在书院教育中,逐步形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同流派的价值取向。
就越中教化流脉看,儒学教育成为主流形态,以孔庙、学宫、书院为代表,贯穿于整个封建专制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官学与私学发挥的教化作用各有千秋,但官学始终占主导地位。汉以降,儒、释、道三家并存,相比而言,儒家文化总体上占主导地位。与儒学并存的道家,尽管对儒学教化影响很大,但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的教化形态。其后,道教的产生,包括道教的流播,尽管在养生方面开创了独特的哲学体系,由于其游离社会、家庭责任,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教化形态。尽管佛教产生的时间很早,但从古印度传入中国时在东汉时期,勃兴于南北朝。如同道教一样,尽管佛教对儒学影响极大,但从总体上说,佛教也不可能成为教化的主流形态,因为佛教所宣称的宗旨不可能经世致用,只能成为出家人的精神家园。南朝时期,佛教禅宗的出现,在汉地与儒教、道教并驾齐驱,对越中学风的影响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隋朝科举的产生,激活和丰富了儒教,尊孔读经,科考取士,士子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为学价值取向。
越中崇教崇学之风历代相传,诸如余姚作为“东南名邑”“文献名邦”,源于耕读传家的风气,课业之盛,不绝于代。仅有明一代,一县之学子,进士登科者近400人,其中状元3人,世称“有明一代人物甲天下”。明末清初经史学家、大儒黄宗羲在《浙中王门学案·题记》中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吾越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其儒者不能一二数。”[3]219在读书科业上,王阳明父子可谓是越中杰出的代表。
余姚秘图山王氏家族是越中教育世家,先世数代均耕读传家,不乐仕进,仅以教书为业,直至王阳明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及第,不仅其家族重光门第,而且也为乡里带来了无上的荣光。王华作为一介寒门学子,以科举进身状元,成为余姚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典范,当然世人更看重王华的道德文章。王华走上仕途后,对家族的振兴是下了功夫的。其从家教入手,传承家学,重振门风,以自己的品行影响家族成员奋发进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据《年谱》记载,弘治三年(1490),王华因为父守孝归姚,期间亲自为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牧相与子守仁讲析经义。守仁不负父望,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1]1 223。由此可见,王氏家族崇文崇教的家族氛围,对王阳明接受严格而规范的儒学教育,汲取经典的精神营养,为其日后创立学说奠定了知识基础及形成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狂者性格。
二、中兴气象:化育与广大
嘉靖初年,政治污浊,围绕“大礼议”问题党争激烈,人心不古,表现在社会伦理道德上,朝野知行分离的现象相当严重,现实与“天理”之间融通遭遇困境。晚年的王阳明在绍兴家中丁父忧及赋闲期间,为打破沉闷的学术风气,于是倡导心学,广纳门生,大兴讲学、著述之风,论道“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办讲会于余姚龙泉山之中天阁。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的基础上,专论“万物一体”学说,发“四句”之教。自此,“阳明心学”发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圆润的新兴思想体系,与程朱理学各表一枝,形成明中以降儒学发展的新流派。“阳明心学”的理论特色侧重点在主体精神,强调为学开显良知、“事上磨炼”。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勃兴的主要呈现形式如下。
1.讲学盛况
据《年谱》载,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返绍兴家居后,次月,即归余姚故里省祖坟。在余姚期间,王阳明接纳钱德洪等弟子七十余人,标志着王阳明晚年讲学论道高潮的初兴。
嘉靖元年(1522)二月,阳明父王华去世,王阳明在绍兴府邸丁忧。随后,王阳明的讲学活动日渐增多,“远方同志日至”,一时,越城成为阳明学说的传播中心。《传习录下·题记》中记载了当时盛况:“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1]118学子云集,场面空前。可见,王阳明在越城讲学始盛于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丁忧期满后,嘉靖皇帝因王阳明在“大礼议”问题上态度消极,且讲论心学,故未复其职;但王阳明超然处之,继续在绍兴、余姚等地授徒讲学。
天泉楼讲学。正德十六年末,王阳明被朝廷封为“新建伯”后,在其父王华原宅的基础上扩建成“新建伯府”,俗称“伯府”。此府邸的重要功能是作为讲学论道之所,接待来自四方的学子,其在府邸讲学最初是在“天泉楼”进行的。王阳明弟子海宁人董澐在《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中首句说:“吾昔侍先师阳明夫子于天泉楼” [4]248,另题有《宿天泉楼》诗,有诗句“高阁凝香夜色深,四簷星斗喜登临” [4]364。王阳明江西安福弟子邹守益在《赠董萝石用韵》一诗中,有“昔登天泉楼,获读从吾篇”诗句[4]482。王阳明在《天泉楼夜坐和萝石韵》一诗中,亦有“莫厌西楼坐夜深,几人今夕此登临”诗句[1]790。当年,王阳明与弟子在天泉楼讲学论道常常至深夜,由此可窥见当年讲学的情景。
稽山书院讲学与《尊经阁记》。王阳明在越城的讲学活动声传四方,因四方学子纷沓而至,以至于偌大的伯府第人满为患,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求学者需求。嘉靖三年(1524),阳明亲传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令山阴知县吴瀛拓展稽山书院
稽山书院系北宋名臣范仲淹始建于宝元元年(1038),位于府山。南宋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稽山书院讲学敷政。至元至正年间,稽山书院修葺扩建。元末,书院一度荒废。明正德间,山阴知县张焕移建故址之西。,增建“明德堂”“尊经阁”,为其师传播心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以教化府属八县弟子,有志于圣贤之道。据《年谱》记载:“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1]1 290南大吉亲自到书院讲论,并督促诸生学习。由于阳明先生应南大吉之请在稽山书院讲学,声名远播,于是四方学子闻声而来,聚集在阳明门下。据《年谱》记载:“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1]1 290由于稽山书院的容量也有限,远道而来的学子源源不绝,以至于“宫剎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1]1 290在此期间,王阳明“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1]1 290。可以说,稽山书院的修复、扩建,对于培养阳明心学专才、推助王阳明“万物一体”学说的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为其后绍兴阳明书院的建立提供了范式。
稽山书院尊经阁落成后,南大吉邀其师作记,王阳明婉辞不得,为之撰记。王阳明《尊经阁记》在写作上一反传统作“记”的套路,对建阁的过程,阁本身的形制、建筑特色只字未提,而以“尊经阁”之“经”作为阐发心学观点的论题,系统地论述了“《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的精辟观点,阐明了“经”的内涵,角度新颖,议論深刻,别开生面,对当时思想界、学界起到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极大作用。王阳明自己对此文亦十分看重,并寄呈其道友湛甘泉分享。该记后来被清人《古文观止》收录,影响极其广泛。
王阳明弟子王艮等立“阳明书院”。据《年谱》记载,嘉靖四年(1525)十月,王阳明泰州弟子王艮等门人立阳明书院[1]1 297,这是在越中大地上第一个以“阳明”命名的书院。又据《年谱·附录》记载,当年阳明先生在越讲学,四方同门来游日众,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门王艮、何秦等乃谋建楼居、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来学。师没后,同门相继来居,依依不忍去[1]133。由此可知,当年王阳明在越城讲学的盛况和影响。时至嘉靖十六年(1537)十月,阳明弟子周汝员与绍兴知府汤绍恩拓地建祠于书院楼前,取江西南康蔡世新肖师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时祀。可见,自王阳明殁后的十年中,阳明书院仍延续讲学之风,如无影响力,绝无可能延续十年之久。
余姚龙泉山中天阁讲学。王阳明晚年在越城丁忧与闲居期间,常往来于绍兴与余姚两地讲学论道。据《年谱》记载,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在余姚龙泉山中天阁授徒讲学,并给参加讲会的诸生提出要求与希望,题写于壁,明示弟子,这是王阳明晚年手定的具有学规性质的训语。其在《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中告诫学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 [1]1 294,反映出王阳明严谨治学之教,重在开导学子“致良知”,立德去傲。余姚龙泉中天阁讲会至王阳明出征广西后仍坚持办会。嘉靖七年(1528)九月,王阳明在《与钱德洪王畿书》中说:“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年不审同志聚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尔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遍寄声,益相与勉之。”[1]224同年十月,王阳明又致书钱德洪、王畿:“书来,见近日工夫之有进,足为喜慰!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1]224由此可知,当年余姚龙泉山中天阁讲会、绍兴阳明书院之盛况。王阳明晚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且大多成为浙中王门中坚、心学贤达、儒林俊杰。
游乐会稽山水,点化弟子。绍兴宛委山阳明洞天是王阳明年轻时期读书、修炼之处。据《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时年31岁的刑部主事王阳明,因病告假归越城,“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 [1]1 225。对阳明洞天情有独钟的王阳明,晚年居越期间故地重游当为情理之中。山水点化弟子是王阳明的为教之法。《传习录下》中记载了两则王阳明携弟子游南镇、禹穴、阳明洞等处随地“点化弟子”的故事: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1]101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07
王阳明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话题,寓教于游山玩水之中,将“心即理”“良知本体”等心学思想通过形象的讲解,启悟弟子,可谓阳明教法的一大特色。在游历中通过诗歌唱和阐释心学机理亦是王阳明为教的重要途径。晚年,其在越城讲学期间与弟子邹守益、董萝石等以诗论道,体悟万物一体之境界,在《王文成公全书》有关诗文中均有记载。
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期间,在府邸、稽山书院、阳明书院、余姚龙泉山中天阁、阳明洞天等地的讲学论道活动,是阳明心学在嘉靖初年再度勃兴与广泛传播的主要标志。
2.续刻《传习录》
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期间通过讲学论道,直接掀起了王学再度勃兴的热潮。从外部原因看,与其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是密不可分的。《传习录》的由来,最初是由王阳明同邑早期弟子、其妹夫徐爱整理编纂的阳明语录集,并据《论语·学而》中“传而不习乎”之意,取名《传习录》。其后,王阳明的另一弟子广东揭阳人薛侃继续整理阳明语录,将徐爱所录的残稿及另一阳明弟子湖州归安人陆澄与其新录的各为一卷,共三卷,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首刻于虔州(今江西赣州)[1]1 255,即为明隆庆本隆庆本:指明隆庆六年(1572)巡按御史谢廷杰(江西新建人)所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是为第一部王阳明全书本,后世的全书本、全集本皆由此书而出。《传习录上》之卷一。时至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因受王阳明亲炙,深契“良知学”之精髓,为弘扬师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薛侃在虔州首刻的《传习录》三卷为底本,又将其师手定的论学书信加以增补,并命其弟南逢吉“校续而重刻之”,续刻增补本之《传习录》于绍兴,即今本《传习录》之卷二
南大吉所增刻的阳明论学书信8篇,其篇目为:《答徐成之》二书(正德六年)、《答周道通》(嘉靖元年)、《答陆原静》二书(正德十六年)、《答罗整庵》(正德十五年)、《训蒙大意》(正德十五年)、《教约》(正德十五年)。其后,王阳明的晚年弟子钱德洪,将此8篇中的书信加以调整,成为今本《传习录》之卷二。。王阳明去世后,著名弟子钱德洪将自己与其他阳明弟子所录,编订为今本《传习录》之卷三。
南大吉在《续刻传习录序》中说:“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1]1 580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逆天之为,盖因当时朝廷打压王学。钱德洪在《传习录》中题记说:“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1]40由此可知,南大吉此举甚为艰险,并成为其后被朝中权贵嫉恨遭罢官的起因。南大吉对其师的著述推崇之至,才不顾自身安危,“以身明道”而续刻《传习录》,对传承、弘扬阳明心学起到了特殊作用,功莫大焉。
从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之举看,王阳明晚年居越期间通过书信阐述和传播心学思想,亦是其學说流播之广的重要标志。
3.越中王门中坚
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时,其心学思想的再度勃兴和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即越中王门的日益壮大。如果从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接纳的早期弟子徐爱、蔡宗兖和朱节算起,至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受两广之命止,越中王门真正形成气候则是在阳明晚年居越期间。据《年谱》记载:“正德二年(1507),是时先生与学者讲授,虽随地兴起,未有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者。徐爱,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将赴龙场,纳贽北面,奋然有志于学。爱与蔡宗兖、朱节同举乡贡,先生作《别三子序》以赠之。”[1]1 228正当王阳明罹难之际,家乡有学子不顾时讳,毅然投身于王阳明门下,足以说明王阳明的道德魅力之强。时至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回到家乡,已隔14年。自此,越中王门在王阳明的大旗下,弟子日增,门庭若市。其中,对王学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有两人:
钱德洪(1496—1574),余姚人,为王阳明晚年侍学弟子。十七八岁时读《传习录》,悟“与所学朱子之学不契”,遂对朱学产生了怀疑。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祖坟,钱德洪决意师事阳明,经王阳明从侄子王正心引见,力排众议,亲率侄子等七十余姚籍学子拜阳明为师。次年,钱德洪赴绍兴王阳明府邸侍学。时凡初入王门者,王阳明要钱德洪先辅导求学者,人称“教授师”。嘉靖六年(1527),钱德洪与阳明的另一侍学弟子山阴人王畿因在对王学宗旨的理解上发生分歧,遂请教其师,史称“天泉证道”。钱德洪认为先师“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阳明奉旨出征广西之后,钱德洪主持稽山书院讲会。嘉靖十一年(1532),钱德洪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因郭勋案下狱,继而削职为民。此后,钱德洪便在江浙、宣歙、湖广等地传播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长达30年。钱德洪为编纂阳明遗著不遗余力,完成了《年谱》《王文成公全书》等阳明遗著的编纂,备受王学同门和学术界的推崇。钱德洪著有《绪山会语》传世。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天资聪颖,豪迈不羁。嘉靖二年(1523),因会试下第后归乡侍学王阳明,与钱德洪一起协助王阳明讲学,有“教授师”之称。嘉靖七年(1528),王畿与钱德洪在赴京试途中闻师归,竟放弃廷试机会折回趋迎。后闻讣告,连夜奔丧江西,扶灵柩归,服心丧三年。嘉靖十三年(1534),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武选郎中。后被罢官,来往于江苏、浙江、福建、湖广等地讲学40余年,年至80仍讲学不辍。其学术思想:认为良知是当下现成,主“四无”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梏亡,便是致知,而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强调自由自在的处世态度。黄宗羲认为其学说“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 [5]。其著述被后人辑为《王龙溪先生全集》22卷传世。
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期间,越中王门其他重要弟子还有:张元冲(1502—1563),字叔谦,号浮峰。山阴人。官至右副都御史。师事王守仁。为学以真切纯笃著称,强调戒惧慎独,注重践履,对传播王学多有贡献。黄宗羲认为其:“学先立志,不学为圣人,非志也。圣人之学,在戒惧慎独,不如是学非学也。”[3]300
胡瀚(生卒年不详),字川甫,号今山,余姚人。官崇明教谕。年十八,从学王阳明,阳明称其为“吾小友”。为学以“求心为宗”,功夫以“存心为主”。黄宗羲称其学以求心为,谓其“心无内外,无动静,无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内外动静,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3]329。胡瀚对阳明心学多有阐发,作《心箴图》以自课。晚年归家30年,筑室今山。著有《今山集》100卷。
孙应奎(1504—1586),字文卿,号蒙泉,学者称蒙泉先生。余姚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在余姚中天阁从学王阳明。其将“致良知”学说概括为“学以尽性” 。有《燕贻录》传世。
闻人诠(生卒年不详),字邦正,号北江。余姚人。王阳明姑表弟。官至右副都御史。阳明在江西任职时,闻人诠与兄闻人訚多次致书问学于阳明。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知宝应县,后升御史,巡视山海关,修城堡四万余丈。嘉靖十一年(1532),与钱德洪共订《阳明文录》,并刻印行世,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思想超越:圆通与开新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伴随其生命过程的展开而不断地发展、日臻成熟的。阳明晚年居越期间,在理论上最大的成就是提出了“万物一体”学说,尽管宋儒已有类似的说法,然而,阳明学说的逻辑起点与内涵并不相同,是各具特色的思想学说。
1.完善的体系
自古以来,相当多的学者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主要理论结构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即:正德三年(1508)在贵州龙场悟道,即悟“心即理”之道;次年,在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之说;及至正德十六年(1521),在江西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心学思想体系即告大成。然而,由于一些学者对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整整六年中所进行的思想创设和完善并没有很好地关注、梳理,尤其是对这一阶段及其重要的思想创设“万物一体”之论没有深入体察,认为仅仅是对宋儒“万物一体之仁”的阐发而已,从而导致未能全面、系统地审察阳明心学体系的内涵,一定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人们对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深入研究。王阳明晚年居越期间,在“致良知”学说的基础上专论“万物一体”学说,在理论形态的完善上有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阳明心学完整的思想体系,标志着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之最终确立。
2.复杂的背景
“万物一体”学说的确立。明嘉靖三年(1524),朝中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大礼议”事件,满朝文武被迫卷入了旷日持久的议礼斗争。据《年谱》记载:“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1]1 292《年谱》又载:“(嘉靖三年)四月,(丁忧)服阕,朝中屡疏引荐,霍兀涯、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1]1 292王阳明在朝的弟子亦分为两派,王阳明对道友、弟子所提出的问题“竟不答”,表明了王阳明对“大礼议”走上邪道是非常反感的,这便是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的政治背景。
3.丰富的内涵
王阳明晚年在越城闲居期间,讲学论道,将其前期的思想学说发挥到极致。据《年谱》记载:“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岁,在越。正月,门人日进。”[1]1 289二月,王阳明在越城讲学。“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1]1 290此处特别强调了“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这一表述。此“同体之旨”是王陽明将“致良知”学说上升到境界论的高度,突破了以往思想的局限,深刻地阐述了“万物一体”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揭示了“万物一体”的内在关系,从心体上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于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撰写了《答顾东桥书》长文,其中说道:“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54在《答聂文蔚》中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1]79意思是,生民须心存敬畏,视“万物”为己身,从内心体认万物与自身的相互依存关系,自身、社会、自然世界才可能安定、和谐。晚年的王阳明居越期间,寄情越中山水,体悟万物同体之乐,便是明证。
如果说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学说主要侧重于个体内在的道德修炼与践行,那么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学说,是将上述思想推及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之中,是心学思想在人生观、社会观和宇宙观上的扩展和升华。此说,既传达出王阳明的人生、社会理想和普世情怀,也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至此,其心学思想体系方可说真正地完善。故此学说是其心学体系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学说与宋儒所论“万物一体之仁”在逻辑起点上是不同的,王阳明是从“良知”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思想创设,是对“致良知”学说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此说,使阳明心学理论体系阐释更为严密,内容上更为丰富,说理上更加透彻。
王阳明晚年居越城期间,其心学思想的勃兴和传播,还表现在阳明后学对其思想的持续发力。明末,越中王阳明后学继往开来,为传播阳明心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因为阳明后学的坚守、弘扬,才使得自明末以降,阳明心学在越中一直流播不息,代代相传。
四、结语
王阳明晚年在居越城的六年(1521—1527)中,以授徒讲学为主要途径,以揭櫫“万物一体”学说为主要教学内容,其所掀起的王学振兴运动,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学子,直接触发了嘉靖初年王学的再度勃发及大规模的传播活动,奠定了越中作为王学传播大本营的历史地位,并对阳明后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因故返家、丁忧和闲居这些偶然因素外,究其文化渊源,则与越文化的传统精神有天然的联系。自古以来,越中士风洒脱、坚守根本、不畏艰难、乐于进取的文化内涵,为阳明心学体系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精神支撑。阳明晚年在越六年中,是其心学思想发展日臻完美的阶段,是对以往心学理论创设的全面总结与开新。长期以来,学界由于受到历史上学术定见的影响,对王阳明在居越六年中所从事的讲学论道活动及“万物一体”学说创设的意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对阳明心学的完整体系缺乏深刻的解读与归纳,影响了对阳明心学深入的研究。故研究王阳明的这段历史和其心学思想的发展圆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唯有对这段历史作全面、完整、深入的挖掘,才有可能持续地推进阳明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藝文上:卷十七[M]//(光绪)余姚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M].钱明,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沈善洪,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70.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