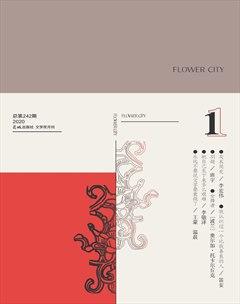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金理(学者):人必须借助多面镜子、多重视野才能认清楚自己。我们不妨以世界文学作借镜,与当下中国的青年写作对照,从出版、阅读、创作、文学生态等角度,来进行比较,尤其要照见我们自身的“长与短”。这样的比照是有充分现实依据的。那些年国外青年作家打着某某国家“80后”的名义,如抢滩一般涌入国内文学市场:意大利“80后”保罗·乔尔达诺(《质数的孤独》),英国“80后”乔·邓索恩(《潜水艇》),美国“80后”黑利·特纳(《到莫斯科找答案》)、蒂亚·奥布莱特(《老虎的妻子》),加拿大“80后”伊恩·里德(《一只鸟的选择》),法国“80后”阿尔玛·布拉米(《无他》),日本“80后”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绵矢莉莎(《梦女孩》)、金原瞳(《裂舌》),韩国“80后”金爱烂(《老爸,快跑》)……当然我也很好奇,我不知道人家文学体系内确实也有“80后”这样的名号呢,还是有点像概念返销,借助国内一度形成的市场热点而重新“组装”、贴标签。
那么有了这样一面镜子之后,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我们可以照出共同的地方,也可以照出差异的地方。关于共同的地方,日本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早就开始进行研究,比如千野拓政教授、藤井省三教授,分别都以村上春树为核心,研究他在东亚的文学流通。还有那段时间里日本作家青山七惠走红,她写出一本,我们这边马上翻译一本,简直是同步态。这是否意味着某类文学主题、技巧、格调已经成为跨国界共感的因素?关于差异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举嘉宁的例子。据说邓索恩到上海跟跟嘉宁有过一次对谈。嘉宁摊开一张成绩单——20岁左右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两年之后出版第一部长篇,接下来五年一共出版了七本书。这样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让邓索恩惊羡不已:“在20岁时出版第一本书,这种情况在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嘉宁后来对这个也有所反思,我觉得这是差异的地方,写作是马拉松事业,中国的“80后”不乏一夜成名却小成即堕的例子,很多年轻人一度成为热点人物现在已不知去向;国外的同龄作家不像我们这样在起步阶段发猛力,却有可能收获长线成功。
何平(学者):“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我和金理设计这个题目,基于中国的“新文学”或者说“现代文学”。如果没有世界文学维度,无论是作家的写作实践,还是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基本是没法展开的。我们说的“世界文学”是个特别开阔的东西,并不等于欧美,而是中国文学和它之外的一切文学的总和。为了表述的方便,一般而言,我们说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是指中国和减去中国文学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比如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改革开放”我们往往只理解成文学展开的背景,很多时候没有理解成文学自身的“改革开放”。如果认识到改革开放也是文学自身的改革开放,几乎所有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写作现场的作家都有这样面对世界文学的震惊感,尤其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现在看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况,余华也好,格非也好,苏童也好,他们都会对阅读和写作过程中的震惊时刻,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我把这個震惊时刻描述为走出写作的蒙昧年代和至暗时代。我们看苏童、余华、马原和格非,以为他们一出手就是《桑园留念》《十八岁出门远行》《拉萨河女神》《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他们这些作品发表之前,他们都有漫长摸索的“黑暗时代”,然后忽然被照亮,这个被照亮的时刻常常是他们读到某一个某一些外国作家。比如余华,早期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忽然有一天读到卡夫卡,意识到文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格非和马原,原来读的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1985年前后接触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打开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不只是先锋作家,比如说陈忠实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你看他早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十七年文学”柳青那个路数下来的,到他写《蓝袍先生》前后,他读到马尔克斯和卡彭铁尔。所以他的《白鹿原》是有拉美文学谱系影响的。
徐晨亮主编的《中华文学选刊》做了一个青年作家写作调查,调查了117个3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他在中国作协北戴河会议上提供了部分调查结果。这个调查有一个是关于作家受到哪些中外作家的影响。调查结果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一些有市场也有影响力的作家,比如昆德拉,没有一个人选。昆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对中国作家影响那么大,但今天的青年作家没有一个提及,这里面发生了怎样的时代和审美之变?不被提及,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昆德拉是老一代作家,因为他们列的作家里面,排第二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克斯,第三位是福克纳,第四位是卡夫卡,然后是契诃夫、福楼拜、海明威,都是比昆德拉更老的作家。再比如在我们想象中村上春树应该对新世纪青年写作影响很大,但村上春树在117个作家调查中只得到三票;很多年轻作家在其他场合提到的东野圭吾也只得到一票。我不排除,青年作家也许有各自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书。
这个调查样本即使可能存在局限,但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当今“青年写作”究竟跟“世界文学”怎样发生关系?他们这样一种关系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作家,以及更早的作家,甚至1949年之前的作家关系方式有什么差异性?同时我们也关心,国外青年写作状况是怎么样的?
方铁(翻译家):如今的写作,外延已经非常宽广了,而这正是青年写作者更为如鱼得水、更为擅长的部分。当下文学生态的这些因素,导致写作者对现实生活以及故事的外壳特别重视,现在的小说很注意能够讲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或者把生活热点吸纳进作品里,比如AI,比如楼市,比如聊天记录,比如各种闲鱼、淘宝订单,等等。我相信很快垃圾分类也会成为创作中的热点题材。《我是范雨素》,已经是一种介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创作了,这篇作品的一夜成名,说明受众对物质生活本身的注重,也体现在对文学阅读的指向中。青年写作者或许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尝试前行,更深入地沉浸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不拒绝被编辑和市场类型化、“贴标签”、进行一句话概括。像大家都很喜欢的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后,你能看到他有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还有一以贯之的对“犹太大屠杀”“亲子伦理”等主题的反复探索和呈现。
当然,这类探索是不是一定能够成功?也不好说。比如我翻译菲茨杰拉德的遗作集《我愿为你而死》,他当时已经意识到影视化、好莱坞的介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提升知名度和销量,他写了很多画面感、影视化可能性很强的剧本,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素材,但最后这些东西都失败了,他的尝试并不成功。大家希望他继续一直忠实地做一个类型作家,写那些灯红酒绿的生活,大家愿意给他贴这个标签,但他自己始终想突破类型化,不断努力“挖掘新的灵感,开掘新的井水”,但这些作品被退了稿子,说明他的尝试并不太成功。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青年写作者无论从眼界、受教育的程度,还是对世界宽广度全面的认识来说,是史上最好的时期,没有一个年代的中国写作者能够像现在青年写作者这样接触到那么多信息,那么丰富的生活,海量的纷繁的物质、现实世界。我相信最终,青年写作者会找到“去标签化”的路径,从市场化的困境中突围,找到属于新时代的新的创作风貌。
黄德海(学者):去年书展期间,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问我们这两年哪个小说比较好,她可以翻译到国外去,我就提了两个小说。他听了之后说,这两个小说不行,美国人看不懂。那么问题来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小说是非常好的小说,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小说背后的复杂性,对我们来说,这个背景就在身边。把小说翻译到美国去,或许需要带着无数的解释才能让美国人看懂。那么问题是,我们要拿什么给美国人看。我们经常说,美国在看待我们的时候,还是按照奇观化的思路在看我们,可是等到我们展示给美国看的时候,仍然不自觉会把奇观拿给他们,因为觉得这易于辨认。
我一直在想今天的主题:青年写作。歌德有篇文章叫《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而我们现在往往鼓励的是作风,而不是风格。风格是要把所有的自己看起来一下子就能变成的什么东西收敛起来了,然后变成一个不能够去掉的东西,才叫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说青年写作的时候,最好加上一个“成熟的”。就是不只是区分年龄,而按照作品的成熟度来看作品。我觉得,一直鼓励青年的姿态会造成一个问题,矫揉造作的作风会充满我们的视野,因为作风特别容易显得不一样。而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起作风。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对青年不一样的鼓励太多了,因此造成青年发表和出版太容易了,也因此造成写作不会遇到真正的障碍,从而延迟或阻断了对自身问题的思考,妨害进步。最后,弄不好我们就参与了我们自己非常讨厌的同质化进程。
我非常讨厌鼓励一个人非得干什么。写作只是所有工作中的一种,你干不好,就离开,干别的,这是很好的行为;而不是说这个人很有才华,应该大篇幅鼓励他。不需要,写的人会写下去。并且我们现在所谓的年轻写作者看着有点样子的,很快就会消失。因此不要给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虚荣,这样会把人带入火坑。一旦社会关注点降低了——因为不停地会有新的年轻人出现,他会觉得时代对不起他,他会焦躁、忧郁、生活不踏实,这是不好的,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得到不当的鼓励。所以针对青年写作,我说两句这样的话,希望我们在推一个青年作家的时候,他是成熟的写作者。
黄荭(翻译家):我同意不要用年龄和代际把作家分老中青,作家只有好的作家和不好的作家之分。从整体来看,法国也算是文学生产和输出的大国,从古典时期到当代,法国文学一直都属于比较强势的国别文学。当下法国文学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国别文学的疆界被打破,“法国文学”的概念越来越被外延更宽广的“法语文学”所替代。从每年几个大奖(龚古尔奖、费米娜奖、勒诺多奖、法兰西学院大奖)获奖的作家来看,很多都是外国裔的,尤其是非裔作家特别多,有时干脆颁给用法语写作的外国人。“世界文学”似乎越来越成为法语文坛的“第一原则”,评委明顯青睐来自“别处”的作家和描写别处生活的作品,如果说过去的文化口号是“法国的,就是世界的”,如今似乎倒过来也很贴切,“世界的,就是法国的”。
英美比较流行创意写作班、作家进校园等现象;法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潮流,也有几个作家曾经尝试过在大学里搞过写作班,做了一些尝试,但没有流行起来。可能是因为法国认为写作更多是个人思想的成熟、风格的形成,是不可以(批量)规训的,这和强调个性和个体的人文传统有关。不过法国创作的土壤和群众基础特别好,首先是国民从小就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喜欢写作的人很多。此外法国每年有几百个文学奖,从几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大奖到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奖,从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很多文学爱好者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不过大多数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已经成名的作家都不会把文学创作当作职业,法国也没有作协这样的机构把作家养起来。大多数法国作家都有自己的职业,教授、法官、医生、护士、工人……各行各业都有,专职以写作为生的并不多,这一点跟翻译行业一样,专职的译员很少,除非是商务等非文学类的,因为法国的纯文学翻译稿费相对也很低。
法国有很多奖会倾向于颁给年轻人或刚刚投身文学创作的人,比如最著名的龚古尔奖,一般都颁给50岁以下的作家,近些年也几次甚至是直接颁给出版处女作的新作家,比如196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祖籍波兰的犹太裔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在2006年以处女作《复仇女神》一举夺得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2011年法国里昂圣马可中学48岁的生物教师阿历克斯·热尼(Alexis Jenny)以处女作《法国兵法》拿下龚古尔奖。这对青年写作(或“年轻”的写作)显然是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的,年轻或刚起步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也可以是成熟的作品,是传世之作,像兰波,像加缪。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文学奖应该颁给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应过多权衡作家多年积累的名声和影响。
范晔(翻译家):我想了一个题目“boom”到“paf”,其实这两个词是象声词,boom是英文,就是爆炸,大家知道是“文学爆炸”。paf是西语里面的词,这在一些漫画里面用到。
我先说爆炸。至少在我有限的目力所及,西语文学界基本上不存在80后这样一个说法,至少我没见过,唯一我能想起来跟这个有点关系的是“波哥大39人”,哥伦比亚有个文学节,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每年都会评一次,会选39个40岁以下的拉美青年作家。为什么叫39人,因为据说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是39岁,这跟80后写作有关系。除此之外我很少看到有青年作家、青年诗人的说法倡导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西班牙文学史上有代际的倾向,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洛尔伽是“二七年一代”,乌那穆诺是“九八年一代”,但是1927年也好,1898年也好,都跟作家出生年代没有关系,跟文化大事件相关。1898年西班牙失去最后的殖民地,美西战争失败,引发他们对自己国家命运的重新反思。1927年主要是纪念巴洛克诗人贡戈拉,他们挺喜欢用时间来做这个代际划分,但这跟作家出生年龄好像没什么绝对的关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说到“文学爆炸”是西语文学在国内译介比较集中的时段。按青年标准来看文学爆炸几个主要的人物,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39岁,富恩特斯写他那几个著名的代表作《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时候也就30出头,略萨写《城市与狗》的时候是26岁,科塔萨尔年纪比较大,他写《跳房子》的时候不到50岁,他30多岁的时候,博尔赫斯已经给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被占的宅子》。“文学爆炸”可以从青年的角度来评判,我还真是没有这么考虑过。确实我看到西语文学没有“媚少”,用另一个名词叫“青春崇拜”。我觉得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点进化论的影响,觉得有一种线性、单性的失败发展论——越新的越好,可能跟这个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在西语世界没有这样隐藏的思维范式。
从“文学爆炸”来看,boom是象声词,有些拉美裔评论家对这个词有点反感,因为这个boom,好像之前什么都没有,突然爆炸一声,石头缝里蹦出一大批人,这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这样一个说法对作家不是很尊重,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抵制“文学爆炸”这样一个标签,这都是你们西方出版人、经纪人的推手,营销的需求。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里面出版机构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有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另一方面,“文学爆炸”固然把整个拉美作家当作一个群体放在世界舞台聚光灯下,但其实它对拉美作家来说,或者对拉美创作者本身来说,其实也有一些益处。2012年,他们举行了一个“文学爆炸”50周年纪念。为什么选择2012年呢?也没有什么定论,因为2012年正好是略萨《城市与狗》出版50周年。略萨说他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同代人都不在世了。他自己就说,实际上在所谓的“文学爆炸”之前,他们这些拉美作家也不大看拉美文学作品。他作为秘鲁人,可能上学的时候读一些。他们读法文、英文都没问题,所以他们读的都是欧美作品,“文学爆炸”也给他们重新看待自己的机会,不管是自己的国族文学,还是大陆文学,这是西语文学的特点,它有一片大陆。同一个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之间作家的关系,有时候我感到非常羡慕、嫉妒,那种同气连枝的感觉,有点表兄弟一般的感情,当然现在已经没那么明显了,但“文学爆炸”期间非常强烈,这也是他们的特色。等于“文学爆炸”让他们看到自己大陆,自己表兄弟写的东西,这也是整个“文学爆炸”的好处。
周嘉宁(作家):我说一些具体的阅读体验,先从两本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国外青年作家小说说起。一本是科林·巴雷特写的《格兰贝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其中一篇《倚马而息》。这本小说集涉及的背景与我个人经验毫无关系,它关注的是爱尔兰乡镇一群生活与未来毫无希望的年轻人的故事。巴雷特自己其实已经脱离了他的成长环境,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完成学业以后居住在大城市,于是我疑虑,引起我共振的是故事本身的残酷,还是巴雷特处理过往记忆时的技术和手段?哪一点更打动我?但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想起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有位华裔导演的作品叫Minding the gap。导演是华裔青年,在单身母亲与再婚家庭的环境下长大,工人阶级背景,因为他很热爱摄影,从中学时代开始拍摄记录同社区滑板伙伴的生活,之后他考上电影学院,离开了故乡,展开自己的人生,但他继续着纪录片的拍摄,持续关注朋友們的人生境遇。而他的朋友大多是被困在原地的年轻人,面对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毒品、未婚先孕、失业。能感觉到导演本身在回到这个群体时所怀有的深厚情感,以及谨慎地确定自己的思考边界。这当中有很多创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选择,我觉得跟我们国家青年写作者的情况相似,有很多可以共同去思考的地方。
还有一本书是萨利·鲁尼《聊天记录》。我把书借给了比我小十岁的朋友,之后书又被借给了朋友的朋友,这样继续漂流着。我曾在朋友圈读到年轻女孩写的读后感。她说一方面觉得千禧一代的文学有一种被工业制造流程化的感受,这本书被责编修改的痕迹很重;另一方面,她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被不断吸引,觉得自己是书中主角,没有办法停止阅读。
但我今天主要想说的并不是在文学当中容易被理解、容易被传播的故事。恰恰相反,我所想说的可能是《聊天记录》的反面。我自己最近几年做翻译的过程中,唯一愿意去谈的一本书就是美国女作家米兰达·裘丽(Miranda July)的作品,我在2012年翻译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感觉既震惊又心碎,今年这本书要重新出版,隔了七年我再次校对的时候依然是同样的感情,非常震惊、非常心碎。2017年我又翻译了裘丽的第一部长篇《第一个坏人》,当时与编辑一起下了很大的决心,觉得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也要让这本书被更多人看到,可是它的传播过程是受阻的过程,没有办法在流通中得到更多的认可,没有办法成为一本被一个个人转递下去的书。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
美剧Girls的主创兼主演莉娜·邓纳姆对《第一个坏人》的评价是:“So heartbreaking, so tender,so dirty,so funny.”心碎和温柔是裘丽风格中始终存在的词语。这里的心碎区别于被碾压之后的破裂,甚至相较脆弱,反而有无畏的伤感。温柔也是出于一种庞大的明亮的爱,是绝对的暖色调。我觉得这两个形容词是比较容易传达的情绪,或者当一部外国文学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如果它是心碎的、是温柔的,这两种情绪是很容易用中文传递到中国的读者这里来的。但是它后面紧跟着另外两个形容词。dirty这个词语令我非常迟疑,仿佛任何一个现在有的中文词汇都无法解释邓纳姆在此处的定义。有哪个与性相关的中文形容词在某种语境下可以同时具有天真和调侃?以及最后一个词语,funny。在中文的转述中一定会缺失的funny。不是好笑,幽默,有趣,不完全是。更接近于不无好笑,不无幽默或者不无有趣,以此来减轻所有这些形容词的重量,因为这里有一种过分轻盈的东西让我甚至都不舍得用稍微确切一点的词语去损伤或压抑。
2014年裘丽做了基于社交软件的项目Somebody。宣传语是“发短信差劲,打电话尴尬,写邮件老套”,所以她设计了一个非常裘丽风格的社交软件Somebody。简单来说,注册登录以后,你如果想发送信息给你的朋友,这条消息不会直接传递到她那里,而会传递到她附近同样使用这个软件的人的手机上,这位附近的陌生人如果点击接收,就得负责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你的朋友,而且你还可以备注以什么的语气,神态和姿势去传递这条信息。这个项目是与服装品牌Miu Miu合作的,之后拍摄成了一个10分钟短片,讲述了几段信息传递的故事。人类交流中的尴尬、错位、缺失,因为信息无效率的传递和延误而被进一步放大,却没有一丁点讥讽,反而因此觉得所有人的孤独与快乐都以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以及被传递。那些在文化与语言的缝隙中消失或者跌损的东西,卡顿和无穷无尽的误解,或许也应该被我们接受。
张定浩(学者):当“世界”作为形容词去修饰“文学”,所谓的世界文学,也就是可以轻易打破语言阻隔的文学,是在翻译中损耗最少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我觉得有两种,第一种是最肤浅的,比如冒险、推理、情色等各种类型文学等,它们诉诸人性最表层的感官欲望,不需要什么理解的门槛;第二种是最深刻的,比如《圣经》和《神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它们直接面对人类生活的终极和核心问题,这使得一些人即使不懂,也会报之以敬畏。我觉得这两种文学构成“世界文学”的两面,而这两面都有可能产生杰作,但这两面构成的世界文学,只是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小于文学,而非大于。因为文学触及的人类情感,除了最肤浅和最深刻的,更多的是暧昧含混和复杂的,是具体某个时空内的混沌。
那组涉及一百多个年轻作者的调查,据说在回答谁对自己写作影响最深这个问题时,只有三个人提到村上春树,我很好奇这三个人是谁。我觉得不管他们现在写得如何,至少是比较诚实的,而诚实是唯一能让年轻写作者走得更远的方式。现在很多写作者,嘴里说着热爱卡夫卡,偷偷模仿的却是村上春树;张口闭口契诃夫,其实写出来的却是莫泊桑式的。因为莫泊桑好学,契诃夫难学;卡夫卡很难学,但村上春树相对好学。另外,我印象很深的是两个被访者的回答,一个是沈诞琦,她提到蒲宁和纪德,这就跟我刚才说的第二种世界文学有关系,她关心的是那些谈论最重要问题的作家,他们也许不是最好的作家,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更多的潜能。另一个是费滢,她区分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和自己最受影响的作家。我覺得很多年轻作者都没有区分这个,把最喜欢的当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费滢谈影响她的作家时提到了蒙田,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美国汉学家,我觉得这特别好,一个年轻写作者要有能力破壁,不只是学习现有的文学大家,而是能从文学之外吸收文学,这才能丰富现有的文学。她们俩因此成为我非常看好的青年写作者。
接下来谈谈青年写作。所谓的作为形容词的“青年”,也是两方面,首先是意味着新的文学。这一百多年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家慢慢觉得是新的就是好的。上海最近在搞垃圾分类,大家都知道,最新鲜的东西是最容易腐败的,所有的厨余垃圾都是最新鲜的但无法保存。我们需要警醒,到底何谓真正的新鲜,是接通源头活水的新鲜,还是一种难以保质的新鲜?
其次,我觉得青年就意味着对抗性,他始终是跟意识形态对抗的。这种对抗,不是要夺取权力话语,相反,恰恰是自觉地疏离于权力话语体系,永远跟权力疏离,跟主流话语疏离。现在的青年似乎特别不容易建立这样的姿态,我们各个方面对青年都太好了,而青年本来也就特别容易被腐蚀。最近我很喜欢一个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的诗,这个诗人第一本诗集就获得耶鲁青年文学奖,但他随后就隐居了,跟情人一起去希腊待了八年,后来又去日本,总之一直在世界上认真地生活,而非在文坛认真地投机。又过了20年,他才出版第二本诗集,又立刻引起轰动。你说他到底是青年写作呢还是中年写作?我觉得对好的作家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种主动的疏离感是产生青春气息的很关键的东西,因为青年就意味着对抗和拒绝这个被中老年人把持的话语体系。
再说最后一点,关于青年小说写作,我自己的几个判断依据。我有两个粗暴的标准:一、是这个小说写作者是不是热爱生活。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写作者太阴郁愁苦,动不动就抑郁症,非要获个鲁迅文学奖才能把毛病治好。我觉得好的小说家应该是热爱生活的,他要对日常生活抱有热情,而不是对日常的名利抱有热情。二、是这个小说家能不能写好对话——能不能写一场对话,比方说饭桌上的对话,或者超过两个人的对话,这特别考验一个年轻写作者。很多年轻写作者就回避这一点,就不写对话,越是搞实验性,越是不需要写对话。我觉得这是逃避。乔伊斯是写完《都柏林人》才去做他的文学实验的。写对话,是考验你能不能听清楚另外一个人在说什么,小说是要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话,而不只是听你自己在说什么。这也是抒情诗和小说的差别,抒情诗是倾听诗人自己的声音,而小说是倾听世界的声音。
默音(作家):国内大家都知道芥川奖、直木奖。芥川奖和直木奖都是一年两次,有不同的侧重面。芥川奖是针对上一年在期刊发表的新人纯文学作品,直木奖是针对上一年出版单行本的新人和中坚作家的商业小说,也就是通俗小说,两个奖项一个偏文学性,一个偏通俗性。
日本没有青年作家的概念,为什么?在日本,要成为作家很简单,先去参加各种新人奖,日本有五大文学新人奖,还有其他很多奖,一旦在任何一个新人奖项目上获奖了,就是作家了,所以每个作家的维基百科都会写他某某年以某某作品在某个文学奖出道。怎么看这个人是新人作家还是老作家,就看他出道多少年。
最新一届芥川奖五个提名人都蛮年轻的。有时候会有年纪很大的作家出现在芥川奖候选名单上,因为主要是看出道多少年而不是作者的实际年龄。这次五个提名人,一个是75年,其他四个都是80后,这些作家都是2010年之后出道的,最晚的是2016年出道的。
青山七惠是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在日本是销量一般的作家,但在中国畅销。她拿芥川奖的时候很年轻,23岁。青山当时写小说的契机是读到萨冈的《你好,忧愁》,这也是世界文学写作的例子,其他作家影响了新的写作者。
何同彬(学者):“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在我《钟山》编辑身份这里,几乎一直是一个无法展开的,过于广阔、过于当代的图景或尺度。尽管我每天都要花费很多时间面对海量的当代原创文学作品,但正如米兰·昆德拉把大部分的小说排除在“小说的历史”之外,我所面对的作品也基本上在“世界文学”之外。所以,我每天工作时间中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巧言令色地退稿。但是这些热情的作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被“世界文学”抛弃了,即便他们的写法很拙劣,仍旧被“十七年文学”或者“新时期文学”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风格所笼罩,但仍旧不影响他们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或者鲁迅来阐释自己的创作理念;正如我们现在能见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主要的才华都体现在给作品起篇名和写“创作谈”上了,张口闭口都是“世界文学”的各种“高级”经验,但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却经常乏善可陈,跟他所娴熟讨论的“世界文学”没有关系。我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有意讥讽,而只是想让“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变得复杂一些。莫雷蒂说,“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或者套用达姆罗什的看法:“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所以这就注定在这样一个“难题”之下,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处理自身与异质性文学经验关系的“形式”,那种被宇文所安批评的“可译性”很强的北岛的诗歌,也是这样一种形式之一;而且北岛所处的语境,以及他在那样的语境中必须面对的世界和现实,也注定他只能写出那种想象出的、尴尬的“世界诗歌”,这并不影响他在“世界文学”里拥有自己的位置,产生自己的影响,因为“世界”不过是我们自身经验在汉语世界的“虚构”,“世界文学”对应于各种不同的阅读模式。
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青年作家的世界视野越来越广,对一个或多个语言门类的“世界文学”的理解越来越透彻,这种理解和这种视野也反作用于他的写作,但这种理想状态也仅仅是中国当代青年写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理想的“世界文学”的功能的一部分,那些不理想的翻译、不准确的“世界文学”的内容给我们的文学带来的某种野性的、不合常规的、野蛮生长的东西,同样是青年写作、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我们对“世界文学和青年寫作”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被一种有关知识和观念的理想状态限制住思维。其实歌德当年在讨论“世界文学”的时候就曾经提醒过我们:“若随着交通越来越快而不可避免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那我们对这样一种世界文学不能期待过多,只能看它能做到什么和做到了什么。”“世界文学”这样一种想象性的观念建构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作家思维的方法论、基本的背景,在这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世界文学”更准确、更先进似乎就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什么,现在的“世界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显然比80年代更便捷、更繁茂,但我们是不是能得到比80年代得到的更多的“世界”呢?
方岩(学者):所谓“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幻觉。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境遇来想象这个世界的。我们对母语的基本理解,外语掌握的熟练程度,对现状的感知及其关于未来的愿景,基本的政治立场和相关的专业背景等,都是想象世界的基本维度。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说,我们与世界隔着一堵墙,“世界”在那边,而“我们”在这边。我们在魔幻的历史语境中眺望那边的真实诉求及其行动。这会让我时常想起略萨与马尔克斯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对话。马尔克斯回答得很直白,大意是说,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技巧和叙述的问题,而是关于拉丁美洲现实的摹写。所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愿直视我们的“魔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聊聊我心目中的“青年写作”。所谓“青年写作”未必与年龄直接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对“美丽新世界”幻觉的自觉抵制,直面“魔幻”的及物书写。因此,它应该呈现某种粗粝、新鲜、异质的经验书写方式及其审美形态。所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对“青年写作”抱有期待。但是这种期待也不是没有问题,正如刚才已有老师对“青年崇拜”提出了批评。但是,只要我们还想改变生存处境,还想向未来迈进,“青年崇拜”便依然有其必要性。虽如此,作为常年在文学现场的职业批评者,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近些年“青年写作”的乱象和颓势。很显然,这些年体制性回报越来越丰厚,写作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成为获取荣誉和利润的捷径。乔治·奥威尔从未掩饰过写作与名利的交换关系。但是当名利与写作的意义发生颠倒的时候,事情就变得难堪了。很多青年作家在短时间内横扫各大名刊,用习作或未及格的写作换来名利双收。这样的情况会倒逼职业批评家不得不去谈论它。事实上,当我谈论它的时候,谈的不是写作本身及其实绩,而是某种被强行制造出来的现象或话题。职业批评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却是“内伤”。好在总有些优秀的“青年写作”给人带来希望和安慰。
何平(学者):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对于青年作家而言,显然不一定是前辈作家相同的现实处境和问题意识。现实处境和问题意识变了,写作者的构成发生变化,媒介也发生变化,青年人再去面对今天的“世界文学”的时候,他如何去想象他的“世界文学”,去选择他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文学”,如何发明自己的写作,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世界文学是一个现实的构成——由出版家、翻译家、批评家、写作者等等共同建构出来,此刻的世界文学和此刻的青年写作正在发生着关系。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三期·“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地点:复旦大学;时间:2019年7月)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