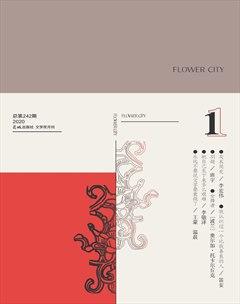余墨
石舒清
王夫之先生说:“作诗但觅好句,已落下乘。”
已过中年,这话是要听听了。
作文但觅好句,正如同女子往脸上涂胭脂一样,年轻时涂涂倒无妨,一大把年龄了还一心一意弄这个,弄得自己一个大粉脸出来,确实不好看的。一个准确的說法是:不是涂什么样的粉才有什么样的脸,而是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脸。
下午去西塔旧书摊,十块钱在小马的书摊上买到余华小说《兄弟》上下卷一套,余华小说我不是很能领会,但这样一个作家总该了解到较深的一个程度的。另买到一幅手工裱牡丹图,50元,画法寻常,不知收这样的东西干什么。然而画到这个程度,没三五年的画功是不能达到的。
在小马的书摊上挑书时,听到后面有两个老人在闲话,一个说,大夫见到他,惊讶于他还活着。大夫以为他早就死掉了。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的血压高到了220mmHg,大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血压高到这个数。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确实还活着。他说有一天他的血压掉到了120mmHg,算是正常了吧,但是他却一下子头晕目眩,视物不清,于是得到一个结论:他是和他的高血压互相适应了。现在他的血压高压是170mmHg,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有些不能相信,问老人家他高压到了220mmHg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没必要撒这样的谎。可见人是有个体差异的。共性里面总是有个性的。老人坐公交车走了。旁边的人都议论说,90多岁的人了,还乘公交车来去,真是不得了。这样一类顽健的老人,总是给许多胆怯的生者以特别的信心。我这般容易被大夫的一言半语吓得不成样子的人,倒是该和这样的老人多交流交流的。
买了书回家时,路过一个字画摊点,卖的都是名家字画,贾平凹、吴三大、张贤亮等,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都是假的。老板穿得倒阔气,一副江湖上历练久了的样子。见我手里是一幅画,便让打开来看看。打开来看着,问多少钱?50元刚买的,还没走出30米呢。老板不信。又说如果真是50元,那么我就是捡漏了。我知道这画若是搁在合适的地方,两三千也能卖出的。日光在最高的楼层上也只余了一星半点。摆摊的人都开始收摊,看着他们的忙碌,也会想,这么多的人设点摆摊一天,劳动所得攒集一处,不及某个大亨一分钟的收入吧。这是让人感慨的。但生活的滋味并非全部体现在收入的多寡里。一天就这样没什么计划似的过去了。我的生命里又少了一天。
今天看到一篇小说,系小说名篇,记得大学语文里好像收录了的。
说的是两个病重之人,住在医院的同一病室里,都病重到不能自理。二人常常谈心,关系不错。其中一人病床靠近窗口,他常常给不能到窗口看看的病友讲述着窗外的所见,听其讲述,窗外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美丽的世界。常听病友讲述自己所不能见,他对病友是很感激的。但是后来却慢慢变了看法,他想:凭什么我只能听他讲,而不能临近着窗口天天看呢。听人讲毕竟是过水面了。因为有这样一份心思,所以一天晚上当病友咳得喘不上气来时,他没有按应该做的那样帮他叫护士,使病友因此离开了这个世界。过了两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把自己的病床安排在窗口,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看到窗外的美景了。但是如愿搬到窗口那里时,他只是看到窗外冷冷的一面墙而已。
这样的小说历来被当作小说典范。这是容易成为典范的小说。我现在忽然觉得容易成为典范的小说其实是不妙的、不幸的,和人里面那些容易成为模范的人一样,总难免些许地涂脂抹粉。我忽然有些不喜欢这样的小说了。这样的小说全部的心机和努力都在于要抖一个包袱。就是说,现在,对抖包袱的小说我不喜欢了,成为我写作上的一个禁忌了。怎么写,写不抖包袱的小说,写没有包袱的小说,写找不到包袱影子的小说。这应该是我在小说观念上的一个变化。
如果强调性地说到少数民族,说到回族男子,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会戴小白帽的。
然而我这个回族人戴白帽的时候很少。不只是我,如我一般的回族人,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有一份公家性质的工作的,都几乎不戴白帽子。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机缘,让人来辨识自己是否回族人,不大容易看得出来。除非戴上白帽子,这就一下看出来了。我的朋友梦也,他和我同时戴上白帽子,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戴上白帽子我也一眼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回族人。有一次和朋友陈继明去马知遥老师家,马老师家请了阿訇来,给他亡故的儿子做一个纪念活动。我和陈继明都戴了白帽子参加。一些宗教细节,比如端着双手接杜哇抹脸等,继明兄也照做无误,毕竟他是回族区域里生活了很久的人。然而,真切的印象是:继明兄即使戴了白帽子,即使和回族人一样的动作行为,也看得出他并非一个回族。其中微妙,难以言传,却屡试不爽。我的一个连襟,在某乡任财政所所长,他的容貌是有些霸气的,但是他戴上白帽后,会有一个奇异的变化,好像戴上白帽后,他的霸气弱了,面相柔和了一些,甚至让人觉得,戴上白帽的同时,他换了一张脸。这些都是我很真切的感受。
我作为一个回族人,一年戴白帽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天,这就是遭逢了回族的两个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这两天回族人是要去寺里的。我戴白帽,也限于这两天内。戴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天。一个很有意味的习惯是,白帽子在口袋里装着,快到清真寺门口了,这才拿出来戴上,一会儿从清真寺出来,走出清真寺没几步,又从头上摘下白帽子,装回口袋里去,还要把头发整理整理,使自己好像不曾戴过白帽子的样子。如我这般的回族人,所在多多,可谓用手指随便一指,就可以指到黑压压一大片。许多回族人平日里并没有这个小白帽的,等到两大节日,需要戴一顶了,就得现买现戴。所以每临这样的时候,清真寺门外总有临时卖白帽的摊点。如同一次性餐具似的。我想:比如说,让我戴着白帽去单位,这好像需要某种勇气的。其实也不必。然而如果不是戴白帽,那么戴任何一种帽子,比如礼帽、鸭舌帽等等,均无妨碍。回族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不常戴白帽的,和那些常戴白帽的回族人,其身份和心态其实是有着微妙而又重要的区别的。
闲话休讲。主要来说说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极少戴白帽的人,有一次竟因为没有一顶白帽而极显尴尬,竟是那样地想得到一顶白帽,事情过去许多年了,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事情是这样的:著名回族老画家曾杏绯先生归真了,得寿一百又三岁,大家都去银川的某清真寺送葬。我去得晚了,去时清真寺里一大片炫目的白,全是戴白帽子的人,不妙的是,来人太多,白帽子没有了,我只能光头站着了。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顶白帽子,独你没有的时候,那神情是很不像樣子的,那心情是很古怪很别扭很仓皇的。好像你是一个闯入者,好像你是一个异类而非同道,好像你是良苗里的一棵杂草,好像你是混进鹅群里的一只投奔无门的野鸡,好像每个人都领到赏了,单单搁下了你一个,好像你怎么着都难以融入,怎么着都被排斥在外似的,好像你不是来帮忙的,十足是来坏事的。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戴着白帽子的地方,你不戴白帽子来干啥?极度的尴尬与不适使我都很有些后悔来这里了,悄悄溜走的心思都有了。我看见张贤亮先生戴着白帽子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看到罗丰兄戴着白帽子站在人群里神态自若。他们都不是回族人啊,此刻却戴了白帽那样自然妥帖地融汇在一大片白里。我确实就是一个回族人,却落在如此一个尴尬的境地里。偏很多人都是认识的。他们一律同情我头上无一顶和他们一样的白帽,告诫我应该早点儿来,埋怨我来得迟了一步,混不到一顶白帽子了。中国人总是好面皮的,这次第,一顶白帽子纵然贵到不像样子,我也会买一顶来戴的。后来一个叫王根明的朋友,他是宁夏大学回族研究所的,认识住寺阿訇,从阿訇那里给我搞到一顶,救火一样搁在我头上,我头小,帽子却是大号的,只能松松垮垮地勉强戴着,这样子给人来看,我显然是一个冒充的回族人了。
参加完葬礼,坐在公交车上回家时,那顶大号的白帽子已经在我的口袋里了。我说不清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心里则像搁了一碗过期的稀粥似的,不大好受。我想我这个回族人和白帽——这个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民族象征的物件——之间的关系,是有些过于复杂了吧。
看到一首黄灿然的译诗,原作者辛波斯卡,诗的名字叫《赞美姐姐》。
在诗中,诗人说她的姐姐除了不会作诗,其他一切都可以做得很好,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很好。
黄灿然先生在译文后有一个点评,点评说,诗人写诗到一定程度后,都有一种想做回普通人的愿望,或者说,对普通人的生活抱有歆羡之意。黄先生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普通人的生活总是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和感召力。因为普通人的生活是全部的生活,而诗人的生活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生活。
黄先生还说出了辛波斯卡诗作的一个特点,可谓中的之论。黄先生说,辛波斯卡的诗,是对生活的概括而不是对生活的描述,说辛波斯卡诗的细节从不拖泥带水。确实如此。是让我有强烈共鸣的观点。辛波斯卡好像有一种能力,可以从无数假的中一下子就给你指出那个真的。虽然她的诗是一种对生活的概括,但生活中的那些细致的东西和有滋味的东西,却在她的诗里面丝毫也不见其少,比如一个迅疾简单的动作,当你用了慢镜头来看它时,才发现它是那么复杂多变的一个动作,可能有的变化和曲折,在里面一个也不少。
诗人像古庙里的和尚一样,青灯木鱼的生活过久了,对世上热闹的生活会有特别的感受。虽然命运使然,他只不过是当和尚而已,却觉得和尚端着的这个碗里,食物未免是太清淡了一些。虽然他也并不希望自己的碗里油腻腻的。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陆续读了不少,当然不错,但比较于另一位老作家孙犁,我是觉得孙犁先生更适合我的口味一些。
如果可以拿着装来作譬,那么我就觉得汪先生穿的不是生活装,而是戏装或者礼服,觉得总有几个佩服的观众看着老先生耍手艺,觉得老先生的观众总是和他的手艺同在的,没有观众,则他耍手艺的兴趣也会减去不少。也许这和老先生写过戏剧有关吧。台子总要高出地皮一些,才好演戏。台前也还需坐满了观众,这戏才可以演起来。想一想,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员怎么可以演起来呢?
汪先生的小说好像是在茶馆的静室里写出来的。小屋子很静,适合于写东西,但这小屋子就是在茶馆里面的。茶馆总是热闹。没有茶馆里的这个热闹和小屋子里的这份清静,老先生都是无法写东西的,或者说写不好东西的,或者说写出来就不会是这个味道。老先生写毕小说,是马上就可以从写东西的小房子里得意地出来,读给一众茶客听的,是马上就可以在台上演出来的。
汪先生的小说场面不大,但是极尽热闹。螺蛳壳里大道场。他的小说都是具备大道场的小说。写小说的汪先生是得意的,也是自负的。我一直不大响应老先生那不动声色的得意相。老先生的得意是不动声色的,几乎只能在眼神里些许看见,但那实在是足够了。老先生这一得意时,就会使得天下别的文字几乎都不在他眼里。他的得意当然有着一些孩子气,但更多的还是阅历精深的老年人的得意。
我更喜欢孙犁先生的不得意。孙犁先生好像不需要多高的戏台,不需要太多的观众。好像他只是聊遣寂寞的自写自画罢了。
说了这么多。说得有些乱。
乱比较这个没多大意思。
文艺总是各有各的好,各说各的好。
今天着意想说的是,又读了汪先生的一组小说,这组小说是对《聊斋》的一些篇目的重写,看了几篇,写得好。使我对汪先生的过往看法有所修正。毕竟一代大家,总有可看之处的。
孙犁、汪曾祺,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论的两个人,两人同一时代,名声相仿,都具有真正的文人气,都是有显赫起来的资历却终于淡泊以终,都长于写篇幅不长的文字,都在文艺行当里有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但是,一个下完蛋不知哪里去了,只把蛋留在那里;一个却是刚刚生了一个好蛋下来,蛋还热热地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嘴里却就禁不住满足和得意地咕咕叫着了。一个是秋果挂满了枝头,一个已经是把果子下在了筐子里,树上空空地清净着。两位老先生有特别一致的地方,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或许很难谈出什么来,然而两人想必都清楚,无论做人还是为文,对方都是不可以小瞧的,也是不可以轻论的。
当汪先生写完一篇得意之作,正心境很好地给客厅里等着的朋友们做菜弄汤时,另一位老先生在天津他的寓所里,正戴着他的袖套儿,孤身只影地给他的书穿衣服,那么多的书,但是老先生穿给它们的衣服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