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朝晖:译者当如钟表匠
孙凌宇 杜莉华

讀者遇到好书是一种缘分,对译者而言,更是。过去十几年,德文译者强朝晖对这种缘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最早是2006年,她那时还在国内为德国的《时代周报》打工,隔壁《商报》的驻中国首席代表、同时也是记者的弗朗克·泽林与她相识多年,关系要好,一次送了本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新书。强朝晖接过时开玩笑说:“你要是想翻译成中文就找我呀!”
过了半年,弗朗克真的找过来,特地请她到一家特别高大上的西餐馆吃饭。他拿出和上海三联书店签的合同,说我这书真的要翻译成中文了,你要不要翻呢?这时,强朝晖嘴里嚼着牛排,碍于自己一时客套的承诺,只好接了下来。她用了一年时间翻译完这本《中国密码》,但出版过程十分不顺。先前的出版社最终取消出版计划,她不愿就此作罢,各处找人,直到辗转找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才得以出版。
“牛排宴”之前,强朝晖从没想过会去翻译书。强朝晖初中便开始在北京外语学校学德文,先生是职业外交官,作为家属,她经常要随之驻外,一去就是三四年,然后回国呆三四年。在国外的时候,由于她学德文出身,经过了外交部的考核,也有外交官的身份,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的使馆或领事馆工作,回到国内就为德国的媒体工作。
2009年开始,她觉得外交并不是特别适合自己的事业,更多还是为了先生,于是开始把翻译当作兼职。那段时间,只要有出版社找,她什么样的书都不挑,经济、哲学、生活、小说甚至连童书都翻。
经多年积累,到了2020年2月出版的由她翻译的《书情书》时,缘分更是积压式地倾倒而来。首先,书的封面配图与她家中书房陈设几乎一样;开篇,作者悼念在近代生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却很快被淘汰的马匹,进而感叹纸质书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而强朝晖属马,社交平台上的头像一直都是马;最神的,书中的插图是各式各样的读书人场景,其中一张摔断腿打着石膏还继续躺着看书的,跟此前她因滑雪摔伤腿、手捧读物的照片如出一辙!
同时做两本书,“完全是两股劲,而且还不同方向”
《书情书》的责编之一、世纪文景的沈宇在一次新年酒会上遇到强朝晖,当时她翻译的《世界的演变》刚刚出版,引来了许多关注与赞誉。同时手边在翻的,是同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写的《中国与世界社会》。沈宇问她:“强老师,你是不是只翻译学术书啊?”她回答:“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不拒绝尝试。”这一次,又是出于礼貌。强朝晖后来回忆说,“实话说,我也翻得挺慢的,这方面的都够我翻的了。”
听者有意,沈宇记住了这个“不是特别负责任的约定”,一年后去找强朝晖,第一句话就是,“强老师,我终于找了一个机会,让你来试一试翻非学术类的了。”接着循循善诱:“我知道你手里面有大部头的学术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作调剂。你先看一看,我觉得适合你。”强朝晖翻开第一篇文章便爱上了,“就觉得它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为了不影响原有的工作,这本不到150页的小书,沈宇给了她一年的时间。虽然时间宽裕,但同时做两本书,还是“蛮痛苦”。一边是“百米冲刺”,另一边是严肃的学术“马拉松”,“完全是两股劲,而且还不同方向。”《书情书》一共40篇,她几乎每隔一个星期才能翻一篇,“每一篇的文字都是一千多字,短的可能还不到一千字。我要是翻得特别顺的话,可能两个小时,长的可能也就半天,但它是特别消耗人的,脑子就像是发动机转速过高的那种感觉,起码5000转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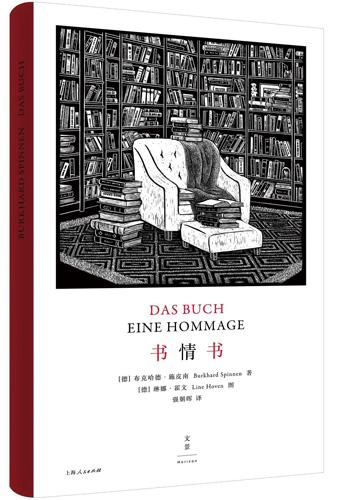
翻译《书情书》的时候,除了“脑袋要燃烧起来”的感觉,强朝晖还深刻感受到“这么好的书,不要把它翻坏了,我就特别的小心谨慎,颤颤巍巍生怕把它翻坏了。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幸亏这书落到我这样一个书痴手里面了,要是落到别人手里翻坏了,怎么办呢?”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专属中文译者
七岁前她随母亲住在河北邢台,市中心有一条东大街,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这条街上,包括一间新华书店。每到周末,母亲都会带强朝晖去街上采购物资,她不要玩具,也不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闷在书店里看书。很多年后,母亲回忆,每次中午去逛街都会和她去吃水煎包,那边的水煎包很好吃,但她对此毫无印象,只记得书店有几个台阶,和每本书摆放的位置。
长大后,除了每天健身,她花最多时间的爱好依然是读书。最爱卡夫卡,大学毕业论文也关于他。看《城堡》中译本时,用了一天的时间,饭也顾不上吃。后来看北大德语系教授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也特别地迷恋。以至于她下决心做翻译后,还想过翻文学书,但对照着看完德语原文和张教授的译本后,彻底灰心丧气,“他那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是你完全达不到的。”
不轻易翻文学书还有一个原因,她自认从小到大学得好的都是理工科,母亲是数学老师,她也更擅长数学型思维,而不是文学书的发散性思维。“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学术翻译的一个原因,翻译学术的书,能用到我的逻辑思维。”
与历史类学术著作结缘是在2013年。此前,甲骨文丛书创始人之一段其刚在北京国际书展上接触到德国歌德学院翻译资助项目,《世界的演变》作为资助的推荐书目之一,一眼就被他看中。他做过五年历史老师,研究生读的是国际政治,在甲骨文期间出版过许多历史学术书籍,个人尤其偏爱宏观通识类,看到那本1600多页的大部头,他断定“肯定错不了”。

强朝晖的书房
之前他与强朝晖合作过一次,留下的印象一是“翻得好快”,只用了半年;另外就是“德语水平非常高,语言好流畅”——她在报社工作多年,语言简洁,呈现出报纸化的语言风格。基于第一次的愉快合作,这一次他也放心地把这本巨著交给了她。
这一翻,就翻了三年。如今回想起来,强朝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作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为一个全球史学家,非常博学,视野很广,《世界的演变》列出来的参考文献书目就有三千多种,因此翻译时要做的研究工作就“特别特别的大,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棘手的是他的文字不太容易懂。“他喜欢用比较复杂的长句、从句,这也是德国学者经常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我的德国朋友们也都说他的文字不容易读,比较晦涩。他自己在某一次的一个中文版序里面还特意道过歉,说翻译他的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参与过英文版的校对工作,发现要理解他的德文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得向译者道歉。”
吸引强朝晖坚持下去的,除了可以享受查资料、研究琢磨问题的时刻,“人会变得非常安静,会忘了其他所有的烦恼和喧嚣”,更因为这位典型的德国教授非常严谨,和她的思考方式非常契合。她曾跟段其刚分享:常常翻完一句,心里暗暗觉得下一句应该这么说,一看原文果然是。
与朋友2016年合译完《世界的演变》后,她就辞掉工作,决意专职做翻译。之前她一直把翻译视作一种爱好,经历了这本大部头后,开始觉得自己有了一种使命感,“就觉得学了那么多年的外语,而在学术这一块真正愿意做的人、有能力做的人又太少了。”
此后,她几乎成了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专属译者,虽然“太难了”,但当编辑把40万字的《中国与世界社会》递过来时,她还是很痛快地接下了。“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非常非常辛苦,但最后我自己还是满意的。”
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
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大概推出2000种新书,会在其中评出十大好书,强朝晖的译本曾三度当选,这在段其刚看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强朝晖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她从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从不给读者签名哪怕是好友相求,如果不是碍于国内的出版规则,她甚至希望把自己的名字从书脊上拿掉。
她认为自己不过是编辑、出版、印刷等加工环节中的一部分,最多是比重占得较大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改变加工的本质。她十分认可本雅明所说的,译者应当是透明的,“我希望大家看到一本书,会说书写得真好啊,或者真烂啊,忘记译者的存在。极端点说,如果一本书读者觉得翻译太精彩,或者太烂,全是译者的失职。”
探讨译者的身份认知时,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钟表匠。“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表的后盖打开,摆弄里面的齿轮,看每个齿轮之间咬合的关系,思考怎么能带动整个机械装置走起来。换到文字上,就是字与词之间的关系,德文的长句子特别有逻辑,像无数个咬合着的小螺丝钉,翻译的时候,就关注每个螺丝和螺口是不是拧对了,关注这些细微的东西,相当于工匠。”
早期她会一遍遍打磨,打磨的过程就是从译者走向读者的过程。现在,一稿时她就会产生读者意识自我监督——“这句话好不好懂啊,是不是人话啊。我比较注重读者体验,一定要让读者看明白。”为此她常常较劲,有时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逞强。翻译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中国革命》时,书里讲的是从五卅运动到共产党怎么获得胜利的过程,她担心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特别清楚,因此很可能被挑错。而且除了德译中,还涉及中译中,得还原那个时代的官职和一些名词概念,“你要渗透在每个句子里面,把中文再翻译成更恰当的中文,这个就非常困难。”
段其刚也觉得她“挺强迫症的”。她从不拖稿,但时常会在交稿时表露出一种不自信,自我要求太高,总觉得是不是翻得不够好。这时,段其刚就会一次次地安慰她,“没事儿,可以了,我很放心的,读者一定看得懂的。”
在强朝晖看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是两个行当,对翻译的要求很不一樣。“文学书要是字字精准却没有文学味,是一钱不值的,没有意义。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自由度更大。”《书情书》里有一章叫《美丽的书》,在结尾的地方说到书的包装问题,就像人的衣柜里的那些衣服一样,再丑再破,你出门的时候总不能光着。她当时用的原话是,无论如何,光屁股上街,不是个好选择。
有朋友读后建议,“你这个‘光屁股上街是不是不雅呀?你该说赤身裸体。”强朝晖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四个字的成语式的东西,就觉得“光屁股上街”很有画面感,“好痛快呀!”
而学术不一样,学术要尽可能精准、贴近原文。她认为,“学术这块做到信达是非常难的,前提是对原文看得非常非常明白,得把所有理论吃透。”德文里宗教和地区就差一个字母,如果翻译不准确、读者看不懂,强朝晖同样会“直接把这本书扔了”,“没有意义。”
疫情期间,她待在欧洲小国斯洛文尼亚,紧邻意大利和德国、奥地利,都是疫情严重的地方。不能出门,最直接的影响是没法去健身房或者泳池锻炼,更多的还是对心理层面的影响,“你会感觉比较压抑,就是整个空气里你躲不开的这种压抑”。
如今,她已经在刻意屏蔽这方面的信息了,除了追踪大的趋势,也不会看太多疫情方面的新闻。每天依然在做翻译,从2006年到现在,她基本都处于一本书还没有翻完下一本书就已经签合约的状态。1月份从北京回去到现在,已经翻了约八万字。
她工作时非常有规律,一般上午、下午各干一点,一天不超过四小时。“其实我干专职以后,每天翻的量并不比以前多。这个还是和精力有关的,现在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了,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但是翻译必须是有规律性的,不是说我高兴就翻译很多,不高兴就扔在那儿。一点点地往前走,有自己的速度,像跑马拉松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