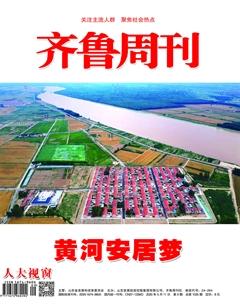龙应台的母亲物语
由卫娟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龙应台著,58.00元,湖南文艺出版社。
如何做一个母亲,如何做一个女儿,龙应台以一部《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提供了一个典范。
对于母亲,龙应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孝顺范畴,将母亲作为趟过大时代河流的女性个体去探寻,企图将母亲的一生从时代的洪流与日常的琐碎中打捞,还原一个叫做“应美君”的女子。
母亲的100年进化路径
民国女子应美君的读书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十岁的她这样跟父母谈判:哥哥功课不好不是我的错。如果我自己挣学费,你们让不让我去上学?
美君就到佃农的田里去挖花生,然后到市场叫卖。当然是卖不了几个钱的,但地主家庭的父亲让步了,母亲还让木匠给美君做了木头书箱。美君24岁离乡后,美君的母亲一生颠沛,却一直守着这个书箱。2007年,龙应台在大陆的表哥把这个书箱交还,她发现里面有母亲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到台湾后,美君只能在水泥地上编织渔网补贴家用,却坚定地宣布:我的女儿要上大学。在美君看来,如果不上大学,应台的将来就和她一样了。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可以说,龙应台的今天,是站在美君母女两代人的开明与努力上。
美君给母亲请的外籍护工,再辛苦也坚持要国内的女儿读完大学,这位母亲也说了同样的话:不上大学,我的女儿就跟我一样啦。
而龙应台这一代,又为母亲的形象和能量丰富了什么呢?她的记录,就是她的价值指引。
一位母亲到了晚年,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美君在70岁那年,一口气做了3件令孩子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而大大“嘲笑”的事情:隆鼻、纹眉、纹眼线。80岁的时候,丈夫开玩笑捏了一下“章鱼太太”的脚,美君怒而把他锁在门外。
龙应台的好友安琪拉65岁的时候去登广告,邀请一位男士一起从德国波昂骑单车到波兰华沙。这个年龄,她依然天真热情,不肯和一个瘫在沙发上看球赛和喝啤酒的笨男人无聊凑合。
另一位妈妈玛丽亚,82岁时一个人驾驶帆船在湖上游荡。她的丈夫从退休后就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她一个人去学德语、上菜场、看画展、去作家的演讲签名会……后来,她和新结识的女友同居住了,两人一起驾船、露营、看展、登山……
龙应台的另一个记录意味深长:葡萄牙一位50多岁的已有两孩的女人控告诊所,要求赔偿诊所失误造成的性生活缺失。法院同意了关于医疗过失的赔偿,却以50岁以上女性性生活不太重要为由,将赔偿金缩减。这位母亲再次告上欧洲人权法院,法院判决葡萄牙法官不但女性歧视,还犯了老年歧视。
这100年来,母亲们先是为女子争取读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再重复自己单调困苦的生命。然后,母亲们不肯放弃自己,不管是六十岁还是九十岁,都可以在阳光下的公共空间里坚持:“我老,我美,我能爱。”
龙应台的女友冰娜的母亲,在85岁时去苏黎世选择尊严地死去。这位母亲曾是一位跋扈的导演,“她骂人的时候,像山洪大爆发,声音大到剧院外边的狗都收起尾巴趴下。”这位母亲在罹患渐冻症后,渐渐拿不动碗、剪不了花。在花园里晒着太阳闻着花香时,她轻轻跟女儿说:带我去苏黎世。这是一位母亲的自主选择,也是她身体力行的生命教育。
而龙应台本人,作为母亲,在这本书里剖析如何接受儿子的女友。儿子说:“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容易,但是你必须学习接受。要不就是我和她一起来,要不就是我也不来了。你决定”。她由此总结了“绝对不要做”的十件事,并想到:如果伦理变成了压迫,亲情变成了绑架,你就应该是那个站起来大声说“不”的人。这是龙应台本人,为母亲形象进化的重大贡献。她甚至实行了一种亲子交流的方式:每年单独和孩子们一对一旅行一两次——不论长短,都是最醇厚的相处、最专心的对待。
这一代母亲,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课题——对孩子的生活保持界限,让彼此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幸福着各自的幸福,不缠绕、不侵犯。从《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和焦仲卿棒打鸳鸯的母亲,到尊重安德烈菲利普的母亲龙应台,一代又一代母亲就是这样进化而来,伴随着血泪,伴随着自省。
所以,龙应台会希望回到20年前,她想送给73岁的母亲一张奥基夫的美人蕉,代替卧室中的四君子图。每一代人都能活出自己、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欲望,才能真正地成人、成全。
对母亲的陪伴、打捞与创造
对于天下儿女而言,母亲节给母亲送花、陪伴等等固然可喜,但更深层的爱与尊重呢?
龙应台在母亲失智后,搬到乡下和母亲一起居住,和看护一起为母亲洗浴,不忘洒上母亲惯用的花露水。龙应台后悔,没有在母亲认得自己的岁月里,把母亲当作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去看日出看大河结冰。但令人动容的是,她从母亲的日记、自己的记忆、公开的史料中去还原母亲——从三岁的“妹妹”到九十三岁的“妈妈”,所经历的大时代和小生活。
美君生于1925年。她的老家淳安,在1928年迎来一位在全省县长考试中获得第一的人当县长。这位县长需要连考5天,十个科目包括了历史、经济、民生、法律、地理、国际政治等等。他到任后,创办了淳安中学。所以,美君才能在这样渐渐开化的民风里生出读书的志气。美君18岁的时候,14岁的赫本遭遇荷兰饥荒——因盟军的轰炸,长达半年的围城中,大约两万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去。美君关于1942年的记录里,一位轿夫的母亲被炸伤,疼了七八天才死去;一位在轰炸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天天抱着包袱当儿子,在街上神智不清地跑来跑去。到台湾后,母亲可以和渔村妇女一样坐在地上编织渔网,但出门时就要穿上合体的旗袍并在衣襟里塞上有花露水淡香的手绢;即使被孩子的学费逼得四处奔走,她还在家里教女儿顶着一本书练习走路。
龙应台尽力复原经历山河破碎、背井离乡的母亲的一生,她怀着“温情与敬意”,“感恩他们的江山、他们的烟尘,给了我天大地大、气象万千的一座教室,上生命的课。”
很多人把这看作是龙应台的付出,但在《天长地久》的序言里却写道:在大武山的山径上,在菠萝田和香蕉园的阡陌间行走九个月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来自泥土的召唤,是美君在施舍予我。
到底是谁在施于谁呢?
中国的梵高奶奶和摩西奶奶或可作为旁证。
65岁的时候,秀英奶奶在儿子和媳妇的帮助下,开始做自然笔记,并重新识字学习画画。秀英奶奶由此出版了《胡麻的天空》。其子吕永林这样写道:“作为已经成年的儿女,我常常在想,什么才是我们对父母最大的孝敬?关心、爱戴,让他们吃好、穿好、住好,只要能力所及,此乃理所当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为父母亲创造一片能够属于他们的天空。说句大不敬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父母创造儿女,儿女也要创造父母。”
75岁,姜淑梅开始在女儿张爱玲的指导下学习写作,《乱时候,穷时候》得以问世。短短4年,姜淑梅出了4本书。
这样的儿女成就了这样的母亲,他们在晚年得以亲自记录自己,将自己从暗淡的天光里抢救出来,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样的生活和创作让这些母亲从晚年的低价值中解脱出来,活得更完满自信,也给予亲人们更有质量的相处。她们的生命本身及其作品,是对儿女们的又一言传身教,也是对人类生命样式和精神财富的丰富。
對母亲的珍重,其实是对自己的珍重,也是对所有生命的珍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