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防疫策略背后的三大偶然性变量
徐英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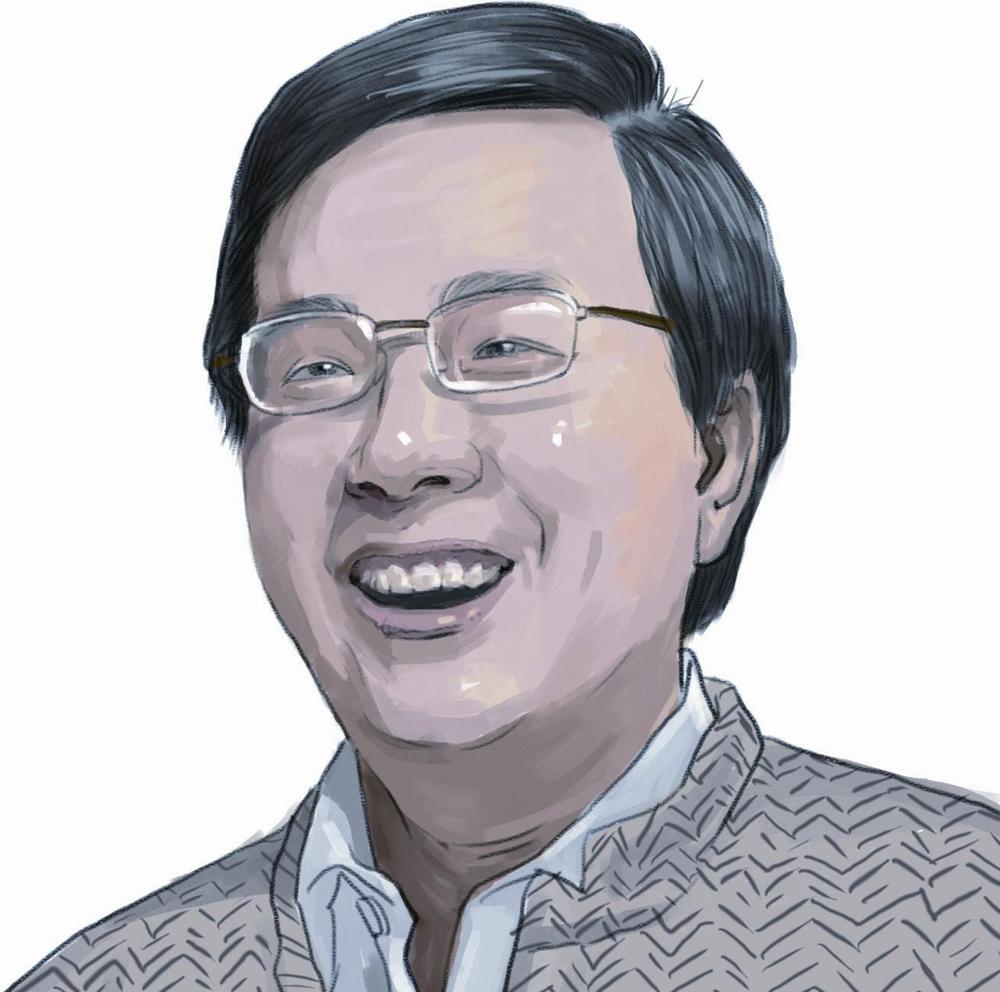
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麻烦,似乎还没有到头。但就各国的防疫措施、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相关的防疫措施之间的三元关系,舆论场中似乎已经有不少讨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一个国家的特定防疫成绩如何,会受到大量的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很难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出发,对一个国家的特定的防疫成绩进行先验的演绎。譬如,抽象地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对防疫有利还是不利,便是大而不当的。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其实起到了比高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问题更关键的作用,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考察:
第一个变量是领导人本身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以及其执政能力。应当看到,西式民主制度所选举出来的特定领导人的能力如何,是一件具有极大偶然性的事情。譬如,日本与韩国虽然都具有彼此类似的政治制度,但是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对防疫工作采取的是比较积极有为的防疫策略,坐镇大邱进行指挥;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则采取了比较“佛系”的防疫策略,东京首都圈的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得到官方的刻意干预。在欧洲,意大利总理孔特使用的策略是在北意地区进行大规模封城,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采用了备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策略。笔者本人对于文在寅的防疫态度是相对比较赞成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与韩国的制度安排可能没有本质性的关联,因为如果換了一个总统,他或她可能就会换上完全不同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变量是特定国家的民众的卫生习惯与民族性格。在这里可以作对比的乃是意大利与日本。与意大利相比,日本离中国更近,人员往来更密集,自身的人口密度更高,而且官方的防疫策略更为消极,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意大利的疫情远远比日本严重。唯一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便是意大利人民与日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卫生细节方面的不同。譬如,意大利人见面的时候是用贴面礼的,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手都不握,只是互相鞠躬。这就等于从根本上减少了病毒通过身体接触进行传播的机会。另外,根据我在意大利与日本的旅行与学习经验,意大利人多话唠,公车上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与之相比,日本人则是典型的沉默民族,地铁上都几乎没人交谈。这客观上减少了病毒在密闭空间中通过飞沫进行传播的机会。
第三个重要变量乃是参看国内的政治因素是否会对防疫产生不利效果。应当看到,虽然几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制度安排下的政体采用的是多党制,但多党制是否会削弱政府的防疫策略,则取决于该国当下的政治形势。以韩国为例:在该国,虽然亲美与反美的政治力量长期彼此角逐,但是,面对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总体上来说全国人民还是团结在了文在寅总统周围,采取了积极防疫策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之构成鲜明反差的是政治制度与韩国类似的美国。在今年1月底,亚洲的疫情已对西方构成明显预警的背景下,美国民主党依然在国会全力推行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严重分散了国家领导人对于疫情的关注精力,而各州州长也以维护个体自由为名,对联邦政府提出的“维持社交安全距离”的倡议阳奉阴违。耐人寻味的是,目前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恰恰又是与联邦政府对抗意识最强的城市之一,纽约市长白思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也很差。换言之,与韩国相比,美国遭遇疫情的时机,恰恰是在全民共识分裂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很多无辜的生命就在这些无聊的党派争执中失去了。但这一不幸,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无本质联系,因为韩国的制度安排恰恰是与美国类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