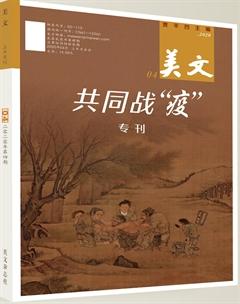2020,让我如何停止对生命的热爱

邵丽
整整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我才最终下定决心。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会说点什么。我首先拨通了一位叫李端的小学教师的电话。后来拨通电话的那位女士,叫刘云仙,身份是农民。我知道她们会哭。我知道我会在她们的哭声里羞愧不已,因为我什么都帮不了她们。我知道不管如何表达,我的电话将会再一次揭开她们尚未结痂的伤口。我听她们哭,听她们叙说。然后我说,你一定要保重,一定!
何其苍白无力的安慰,我连自己都安慰不了。
放下电话,我哭了长达半个小时。年龄大了,感情脆弱得像风中的芦苇,稍有风声就觳觫不已。
是恐惧,也是伤心。
就在前天,我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说是希望能够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写一点文字记录下基层抗疫一线的故事。说真的,当时我有些抵触。我说,我们是紧靠湖北、全国排名第三的重灾区,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被控制在家中,交通阻断,四面楚歌。去一线采访的半点可能性都没有。难道仅靠翻翻朋友圈、靠道听途说的一星半点材料就可以写出报告文学吗?
昨天他们再次电话,恳切地改换了口气,问能不能通过微信和电话采访的方式了解一些基层情况。并且再三告诫,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如此,方让我感觉到一丝安慰。
这很难,电话采访很难。对方无法确定你的真实身份,他们也像我一样,陷身在一波接一波的恐惧中。纵是有朋友引荐,他们也往往不愿意开口。他们有纪律和各种禁忌——你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到了战役的关键时刻,这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否则,各种传言会改变事实。
得感谢我那些在地市做主要领导的朋友们,感谢他们信任我,否则我将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三门峡市的安伟市长在全国疫情等级区域划分图表出来的第一时间微信转发给我,并且骄傲地发了一个拳头紧握的表情符号:三门峡——河南最棒的城市!他说,增加一例就彻夜不安,情势好转就兴奋异常。所有的地市都是一样的状态,他们就这样严阵以待,对疫情的防控揪心到寝食难安,每天都如临大敌般的警醒着。网上一直有关于河南严防过当的负面消息。可这些段子手知道吗?河南是湖北近邻,一亿多人的人口大省,南部几个地市从武汉返乡回家过节的各类人员,每个县都有数万人。武汉封城后,还有不少人从湖北下面的地市县通过各种途径返乡。若不是地方政府一级警戒严防死守,对返乡人员彻查隔离,后果将是何等的不堪设想!
驻马店是河南省的重灾区,960多万人的大市,湖北返乡人员76000多人,其中武汉市57000多人。这数字不让人触目惊心吗?我曾经在驻马店挂职两年副县长,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惦念。我拨通了指挥长陈星书记的电话,他爽快地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关于一线因公殉职人员情况,“有四名同志累倒在一线岗位上。”他沉痛地说,“基层是防控的最前沿,也是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严防死守,人心都是肉长的,心疼他们啊!”河南城市广播媒体联合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个“黄河说”,河南全部省辖市呼叫武汉,每一个地市都图文并茂向长江呼叫,上了热搜榜,感动了无数人流下热泪。注意,说的是全部的省辖市,可细心的人却发现,喊话者漏掉了驻马店——960多万的大市,疫情重灾区。一时间网友纷纷留言,怎么少了驻马店?驻马店人更是纷纷留言,几乎有些懊恼了。我问陈书记,您对此事件怎么看?他笑了笑说,“看到了。漏就漏吧,都是黄河儿女,不消计较!”驻马店全市确诊病例139人,治愈111人,零死亡,零院内医护人员和其他病患交叉感染。结果最能说明问题。说真的,我本不太喜欢这个严肃到近乎傲慢的地方长官。但他对待疫情的用心、用情、用力,还是让我深深感动了。他再三告诫,不要表扬我们。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的,否则那些不该发生的意外或许可以避免。他的声音低沉、疲惫。白天要下县区看情况,听汇报,晚上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疫情研究防范对策,每天都要熬到十二点以后。

图片来自网络
这就是基层一线干部的真实工作状况。我再拨通了另一个地市指挥长的电话。他正在开会。我发微信询问基层一线值守干部的工作和健康状况。他没有直接回答,只回复了三个流泪的哭脸。他不愿说,我亦不再问。在河南,十七个地市,每一个地市都在防守——严防死守。在一场猝然临之的灾害面前,我们主要还是靠人,而不是靠技术解决问题。武汉距郑州乘高铁不足两个小时,封城前,两省的流动量每天可装满无数列高铁。封城后,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逃”回来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武汉封城数日后,新冠肺炎感染者骑摩托车与自行车一路跑回来的现象,仍时时在发生。
那个叫李端的小学教师的丈夫叫陈申,是駐马店泌阳县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1980年12月出生,未满四十岁,农历正月十六倒在工作岗位上。李端说,他懂电脑,负责收集统计各种情况和数据。从初一到十五,他只回家了一趟。开始在卡点值班,后来又主动请缨到隔离点当防护员。正月十五晚上和妻子最后一次通话,9岁的女儿在电话中嘱咐爸爸,你要小心别被传染了。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家闺女长大了,知道操爸爸的心了。谁能想到,这竟成为他对亲人最后的遗言。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李端照例拨打丈夫的平安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一个小时后,单位一男二女三位同志来家里敲门。李端说,是陈申发烧隔离了吗?单位的同志说,没事,你和我们一起去一趟,看看他吧!李端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怕就是像电视上那样,让隔着玻璃和丈夫打个照面,话都没法说。车子开到中医院,却不让她下来,说人还在急救。二十分钟后,两个女同志才扶她下车进去。她看到的,是已经被白布罩得严严实实的丈夫。他没有被感染,死于劳累过度触发的心梗。她如何能不悲呼?这个文弱的女子,奋力挣脱陪伴她的人,一下子扑倒在丈夫身上,哭得肝胆俱碎。晚来的女儿看爸爸躺在那里,便附身在爸爸的胸口说,我爸的心脏可有劲,跳起来总是嘣嘣嘣的,现在咋没音了呢?单位让李端暂时不要给陈申的父母打电话,他是家里的独子,怕父母听到了再出意外。李端说,不让告诉他爸妈,好好的一个人没了,我怎么做得了主?最后领导让她带着医生护士一起去了陈申家里。陈申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的惨状,李端哽咽了半天,伤心得不能详述。
李端说,我一直到今天都还觉得我是在看电视剧,我看到的是不是别人家的故事?她在电话那头哭,我在电话这边泪流满面。我知道,她现在还处于心理应激反应期,被突然而至的打击撞懵了。等她清醒过来,会有一波一波更大的痛苦加倍地袭击她。
刘云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接通我的电话,她从头哭到尾。像发烧似的,我颤抖着,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和她一起哭到无法开口。陶红涛是她的丈夫,驻马店高新区古城办事处五桂桥居委会的干部。他从年初二开始值班,每天要忙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农历正月二十二,陶红涛中午返家,他说今天特別累,浑身不舒服,想趁中午换班回来睡会儿。这让妻子很意外,刘云仙说,你别睡,好歹吃点东西。她匆忙给丈夫下了一碗面条。陶洪涛面条没吃完就去睡了,临睡前安排妻子,两点半喊醒我,不要误了值班。还不到两点半刘云仙就去喊他,他脾气不好,喊得晚了怕他生气。她哪里会想到,她再也唤不醒这个睡着的人了。陶红涛1979年春天出生,202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死于心梗。刘云仙说,我最安慰的,就是最后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否则他就得空着肚子上路了。陶家两兄弟,哥哥病故,父母跟前就剩下这一个儿子,白发人要两次送走黑发人。刘云仙是个农民,没有工资收入。两个儿子还在上学,大的18岁,小的才13岁。她说,陶红涛走了,家里的天都塌了。
面对她们,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何其无用的人,我没有任何办法安慰她们以缓解她们的悲伤,也没有任何能力伸出援手拉她们一把。我告诉她们,相信政府,政府和社会不会忘记英雄,不会让英雄的家人流血再流泪——除了这些毫无温度的话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李文亮走了,全中国都在哭泣;导演常凯一家人病逝了,无数的人为他们点燃蜡烛……陈申死了,陶红涛也死了,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平凡的人,就这样默默的没了。除了熟悉他们的人,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看到胡锡进转发的博主阿部部的微博:“我不想看到一线抗疫人员流汗还流泪,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足足打动了我,让我的泪水一次一次地充盈眼眶。是的,如果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会有足够的敬畏改变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欢呼战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冲到火灾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对于陈申、陶红涛们,我不想赞美他们的荣光,更不想将他们贴上英雄的标签而丢失常人应有的欢乐和幸福。他们是普通父母的儿子,普通女人的丈夫,普通孩子的父亲母亲。他们的亲人只想他们平平常常地活着,不想让他们的名字永远印在疫情资料里被更多的人记住。他们希望上天把儿子、丈夫、父亲还回来,他们要他欢笑、发脾气、贪玩贪吃贪睡、犯各种各样普通人的错误……但一切都在此时此刻戛然而止,他们走得无知无觉,他们只是因公殉职者,甚至称不上英雄。
就在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无以言说的恐惧》,这篇文章被《当代作家评论》公众号推出后,又被好几家报刊转载。我不期望产生什么影响,仅只是两次遭遇大疫的个人,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点浅薄的思考。我同意,作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不必对所有公共事务指手画脚。我更同意,我们需要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时差”。时差能让我们沉静下来,进行有距离的思考,从而更理解生活中的真相,以及那些真相对当下和未来意味着什么。就在今天,又有一位作者在朋友圈呼吁,我们作家要写一写多难兴邦,写一写苦难辉煌。我在上一篇的文章里谈到,多难兴邦是一个很能鼓励士气的正能量口号,也是我们民族屡仆屡起的精神支点。但我们不能以此大而化之,要看到大难之中那些默默牺牲的受难者,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并与他们同此凉热,否则就是对生命的藐视。我们也必须从灾难里悟出点什么,得到点什么,改进点什么,否则我们所有的牺牲都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遭遇大疫是我们的不幸。毋庸置疑,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中华民族迅速战胜疫情也是指日可待。但我想说的是,在灾难和胜利之间,我们的作家将置身何处?我们会将思想的标记,刻在哪个等高线上?
铁凝主席说过:“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我写下这些,是想我们活着的人,需要思考些什么并做些什么。面对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患、那些为抗击疫情而奋不顾身的医生护士、那些为控制疫情蔓延而不舍昼夜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所有这些人,我们无法任由他们白白的奉献和牺牲,我们也不会永远侥幸逃离灾难。惟其如此,我们只有这样设想:我们要努力推动社会一点点的进步,哪怕完全是为了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