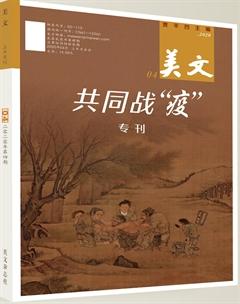人类,从血泊中站起

刘汉俊
一向英雄的武汉,忽然成了一座教人心疼的城市;一向聪明机灵勤奋敢拼的九头鸟,真的受伤了。
“你此刻的心,像一个泪包,一碰就是汪洋一片”,这是我的长诗《给武汉的一封信》里的一句。这种感觉,是这些天来我在同家乡众多亲友的密切联系中得出来的。写下“泪包”二字,我已然是泪包了。
武汉封城,春节无法回家,我只能通过手机客户端的“强国直播”看武汉。八个摄像头直播武汉的街景实况,其中一个正对长江边上的江汉关钟楼。画面里的长江依然浩瀚,但南北穿梭的轮渡停摆了,孤零零的趸船泊在岸边;对岸的建筑春笋般矗立,偶有一两艘货船队从东往西逆水而上;往日里人车挤挤密密熙熙攘攘的沿江大道,此刻鲜见人身车影;旁边是著名的江汉路步行街,此刻空荡寂寥。画面的主角,是江边那座已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钟楼,嶙峋骨立昂然倔强,楼顶一杆鲜红的国旗依然迎风飘扬。

江汉关大楼

江汉关
欧洲风格的江汉关是英国殖民者设立的海关,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见证,也是汉口开埠、武汉走向近代的标志。早已收归国有的江汉关曾是武汉海关的办公地,现在是武汉海关江汉关博物馆,收藏着中国海关的风云沧桑。不知道茕茕孑立的江汉关目睹百年未有的空旷,是否觉得孤独而怆然?大钟的指针是否依然坚定地前行,在寒风冷雨中还能否发出深沉浑厚而悠扬飘远的钟声?
每每看到这个画面,我都为之心动。那天清晨,一位身着桔红色工作服的保洁工进入了画面,在空落落静悄悄的江汉关街面,这个踽踽独行的身影认真地打扫地上的落叶枯草。几乎在每天的早晚时分,这个生动的画面都会出现,让我鼻子发酸。全城封闭,万人归巷,他们依然顶着寒风,冒着风险,维护着这个城市的容颜和尊严,坚定而执着。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坚守,他们的身影是一种力量,有了他们你可以长舒一口气,这座城市还在正常运转。
江汉关上空阴云笼罩,像武汉城此刻的心情。新型冠状病毒有如魔鬼,暴虐地攫取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威脅无处不在,死神随处藏身,城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这恐怖的足音,都有认识的或拐几个弯认识的人被感染、被确诊,甚至罹难,提前没有预约,中枪没有前兆,对象不加选择。几十例,几百例,上千例,数据不断攀升,像是开发互联网产品进行的灰度测试,比灰度测试更可怕的是,下一个是谁,什么时间,程度怎样,结果如何,扩大到多大范围,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院士、教授、博导、医院院长、医生护士、工程师、董事长、警察、画家、诗人、导演、飞行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长江救人者、出租车司机、健美冠军、农民工人兄弟,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孝顺的儿女乖巧的孩子,是我的老师、学长、熟人、同乡,同学的朋友、朋友的同学。看到那一个个在猝不及防中倒下的身影,我一阵阵地心疼。心有时候是会疼得落泪,甚至会滴血的。
我对武汉,没法不牵肠挂肚。我的祖籍是湖北赤壁,距武汉一小时车程。武汉是湖北人的中心,是湖北人工作生活的坐标指向。父亲当年从赤壁山沟里考入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位于汉阳的军工厂工作。我在汉阳的龙灯堤旁边上的幼儿园,3岁起跟着擅泳的父亲在汉水里学游泳,所以才有了我后来多次参加7·16横渡长江活动。读小学时我回到赤壁老家的山村莲花塘刘家,每年的寒暑假回到武汉,两次读大学都在武汉。第一次参加工作在武汉,在长江边上度过了我人生最浪漫最具印记的五年。我曾经工作的办公大楼距江汉关钟楼百步之遥,到我曾经住了三年的汉口洞庭街只需三分钟。虽然我现在在北京工作,但一年总要回几次武汉看望年迈的父母。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一直困在家中不敢出门,我每天几个电话和视频查父母的岗,检查平时就在家中憋不住的老父亲是不是擅自出门了,是不是听话了。在武汉,还有那么多亲人,数不清的来自武汉的信息,向我诉说着难过、痛苦、愤懑、悲伤、祈盼。
不光是武汉,孝感、黄冈、荆州、咸宁等,还有我的故乡赤壁,湖北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牵扯着我。

叶温疫论曳 揖明铱 吴又可
湖北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现在它是一只受伤的九头鸟,一个曾经聪明勤奋、能闯敢拼、顽皮活泼、重情重义,此刻却是满心伤楚楚、满眼泪汪汪的孩子。如何教人不心疼!
令人心疼的,不仅仅是今天的湖北、武汉,还有我们这个在多难中兴起的民族,这个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国度。
关注古代文学的人会发现,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们的生卒表中,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五人的生命定格在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是的,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峰,却齐刷刷地倒毙于同一场瘟疫。史料记载:“冬,是岁大疫。”他们的文友曹植是这样描述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文心之殇,如泣如咽。
瘟疫一直伴随并威胁着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大头瘟、虾蟆瘟、疫痢、白喉、烂喉丹痧、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麻风病,有如蝗虫般疯狂撕噬着一条条生命,仅麻风病在中国就流存了2000多年。有人考证,中国古代发生过多次重大疫情,秦汉出现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另一说,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这2154年间发生重大疫情352次,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每6.1年发生一次,而到了清朝发生频率加快,平均每2.4年就发生一次。1644年明朝末年始发于中国北方的一次鼠疫,使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丧生。这些数据很难说是否精确,但能大致勾勒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成长中的心电图。
800年之后,瘟疫刷新了它重创人类的纪录。1347年9月,源起中亚的黑死病随十字军登陆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经水路到达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的马赛,1348年1月攻入威尼斯和比萨,随后占领意大利重镇佛罗伦萨。从这里,黑死病通过水陆两路四面出击,直抵维也纳,抢滩诺曼底,横扫巴黎,攻克伦敦,越过莱茵河,辐射巴塞尔、法兰克福、科隆、汉堡、不来梅,以吞噬7500万人的“战绩”疯狂肆虐,之后一路狂飙烧向东欧,俄罗斯大草原不幸接着了这个死神的接力棒,立即被死亡阴云笼罩,交战中的鞑靼人竟将病死者的尸体抛入城中,导致瘟疫流行,逃往地中海的人们又导致黑死病更大范围的传播。欧洲中世纪的这次大瘟疫,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规模灾难,也是最惨烈的一次。
此后300年,巨大的瘟疫阴影,一直笼罩在欧亚和美洲上空。
公元1492年10月,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发现了新大陆,也给这片大陆带来了灾难。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欧洲病”,对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进行了不费一刀一枪的摧毁,数百万原住民死去,史学家称之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公元1521年,西班牙派两路殖民军进攻南美洲,一路600人马进攻墨西哥土著帝国阿兹特克,久攻不下后的某天,阿兹特克人忽然停止了顽抗,西班牙人冲进城堡一看,发现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帮他们横扫了对手,满城腐尸,恶臭难闻,一场莫名其妙的瘟疫以大大超过火枪弹的速度袭击了这个一度辉煌的南美帝国;而另一路180人马进攻印加帝国,在他们到达智利之前,一场瘟疫已经帮他们瓦解了这个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南美帝国,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继承人尼南·库尤奇先后殒命,内讧暴发,社会动荡,因此西班牙人以极少的兵力拿下了这个拥有8万兵力的帝国。大航海带来的大瘟疫,使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创造了两大战例奇迹。
有人推测,一度辉煌的玛雅文明突然消失,是不是也与西班牙军队有关,因为几乎在攻打上述两大帝国的同时,他们也踏进了玛雅这片南美丛林。为解开玛雅文明消失之谜,学者们列出了人口爆炸、粮食匮乏、能源紧缺、震灾风灾、外敌入侵、疾病传播、逃往外星等多种可能,是不是西班牙人同样也把瘟疫带进了玛雅王国?很多人支持这一观点。同样,位于东南亚的柬埔寨吴哥文明,在兴盛600年之后,于15世纪初突然消沉了,是不是与瘟疫有关?有学者这样猜测。

《病毒地球》
瘟疫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肆虐的脚步,时常在没想到的地方制造想不到的灾难。公元1665年4月的某天,两个法国海员晕倒在伦敦西区的街口,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爆”了伦敦。人们把染病者封在门里,用红漆涂上十字,无数人在孤独凄惨中死亡。店铺关门,市声若噤,街上空无一人,路旁杂草丛生,城里唯一行驶的是运尸车。伦敦大瘟疫导致7.5万到10万人丧生,直到一场神秘的大火才结束了它血腥的征程。
人类历史上记录的第五次大规模瘟疫灾难,起始于19世纪末,持续了半个世纪,波及中国的南方和南亚、北美洲、欧洲、非洲60多个国家,上千万人死亡。这次大瘟疫离现在最近,所以记忆更深、影响更大。除此之外,1918年源自美国军营、发作于西班牙的大流感,其症状虽然不像瘟疫那么恐怖,但传播速度之快、传播面之广不亚于瘟疫,全球10亿人感染,4000万人死亡,仅西班牙就有800万人丧生,所以这次流感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其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说:“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病毒改变生活,也改写历史。
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薄伽丘在他的名著《十日谈》中,记录了瘟疫袭击佛罗伦萨的惨景,有的人在大街上突然倒地死去,有的人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死去无人知晓,到处是荒芜的田园、洞开的酒窖、无主的奶牛,送葬的钟声几乎没有停止过哀鸣。瘟疫还穿越法国,搭乘帆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使得英国的村落、庄园、城镇到处是尸体、垃圾、污水。情急下的人们想出了各种荒诞的治疗办法、各种滑稽的祈祷方式,人性善恶毕露,世相百态尽显。
文化为历史留下记忆,现实为文学提供素材。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英国诗人琼斯·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戏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面纱》、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委内瑞拉小说家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的《死屋》、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小说《饥饿的狗》、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极度恐慌》《惊变28天》《死亡录像》《感染列岛》《流感》《传染病》《大明劫》等等,都是瘟疫大灾的切片,是疫情与人性痛苦绞杀的精彩呈现。
文学,为人类的抗灾史留下斑斓的碎片。
即使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类仍然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疫灾。2003年初发生的“非典”,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病例8422个,病亡919人。2009年的H1N1流感持续16个月,波及214个国家,163万人受到感染,28万人病死。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寨卡病毒疫情、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2018年刚果埃博拉疫情,给这个世界留下累累创痕。美国流感自2019年9月29日以来,全美至少有2200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2000人,至今还没有探底。灾难的渊薮,是人类的黑洞。
人类无可选择地承受着大自然的各种打击,也通过各种神谕预言,试图解释或者预测灾害的发生,试图找寻某种规律或者祈求某种灵验。这是人类的努力,不管有用还是无用。

《瘟疫年纪事》
譬如,关于“大洪水”。整个北半球民族的上古传说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试图假设和推想:大约在一万年前,一场持续了100多天的滔天洪水,席卷了北半球,所有低于1000米的山峰都被淹没,只有生活在高原和山区的人们才幸存了下来。《圣经》甚至这样描述:“在2月17日,天窗打开了,巨大的渊薮全部被冲溃。大雨伴着风暴持续了40个白天和40个黑夜。”无论有否考证,据此可以推测,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洪水,是人类的朦胧记忆。
譬如,“世界末日”。玛雅文明曾预言,公元2012年12月21日,将是第五个“太阳纪”结束的时候,是“世界末日”。那一天全世界有许多人在等待预言结果,一些人甚至有引颈自刎的悲壮。当时我在上海的一家宾馆,凝视着窗外的黄浦江想象着这一刻的到来。马后炮也是炮,有学者事后解释,所谓“末日”是玛雅历法中重新计时的“零天”,表示一个轮回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玛雅历法中,1872000天算是一个轮回,即5125.37年,据此,到2012年冬至时分,当前时代的时间结束,一切归零。
神谕也好,先知也罢,与自然相伴,与灾难为伍,亦敌亦友,人类似乎无可选择、无法逃避,“三灾九难十劫”是人类的坎,只能昂首面对,悲壮相迎。
灾害的形态千奇百怪,人类一直在无奈地承受各种重创。1912年4月10日英国“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1513人命丧大西洋;1940年6月17日英国“兰开斯特里亚号”游轮在法国卢瓦尔河口海域被德军击沉,3500人葬身海底;1945年1月30日德国“古斯特洛夫号”游轮被潜艇攻击,在波兰格但斯克港附近海域沉没,9343人遇难;1987年12月20日菲律宾附近海域“多纳·帕斯”号渡轮与一艘油轮相撞后沉没,4300多人殒命;2002年9月26日一艘塞内加尔客轮在冈比亚附近海域沉没,1863人被淹死;2003年12月26日的一场地震,使伊朗巴姆古城连同5万条生命消失;2005年8月23日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导致1800多人死亡;2006年7月印尼海啸,伤亡2500多人;2011年3月11日发生日本海啸,近1.8万条生命被吞没,造成福岛核电站泄漏,方圆30公里成为无人区。飞机问世100多年,火车发明200多年,还有数不清的事故夺走了数不清的生命。在中国,1920年12月16日发生宁夏海原大地震,28万人死亡,30万人重伤;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这两次大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今天,灾难还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细菌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核武器、金融战争、互联网战争、环境污染、太空威胁等渐露狰狞,可以预想和难以预测的后果将一遍遍刷新人类的已知,一次次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也一次次激起人类抗灾的斗志。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关注地球自身的安全,无数个天文望远镜在密切追踪地外星体,天体重叠会不会毁灭地球,800多颗具有潜在威胁的行星会在什么时候什么位置撞击地球,太阳风暴袭击地球会造成怎样的伤害,等等。“中国天眼”的问世给人类擦亮了观察宇宙的眼睛,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投入使用不久便已发现多颗脉冲星,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这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冬天固然阴晦,春天依然明媚。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的考验,是对科学的挑战。病毒肉眼看不见、源头难查证,特征奇异诡秘,路径错综复杂,来势汹汹滔滔,其生物特性、致病机理、传播机制、易感人群有待科学探究。这不是一个城市的尴尬,是整个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不是医学的无能,是全部科学面对未知世界的共同难题。
在血泊中诞生,在磨难中成长,在抗争中壮大,灾难成为人类进步的砥砺石、垫脚石、试金石。大灾就是大考,是对底线思维的冲撞,是对极限思维的挑战,是对动员能力的极限式测试和防御系统的破坏性试验。灾前的任何模拟演练,阵前的所有应急预案,都显得苍白无力和漏洞百出,必须接受实战的考验和修补。不单要记住肝肠寸断的悲痛,还要有背水一战的勇气,更要有决战决胜的信心。
人类历史上因灾害导致政息国亡的前鉴不少,能否渡过难关,是对政治动员能力、经济应对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科研攻关能力、国际合作能力、全民抗灾能力的大检阅。阻击战枪声一响,全国模式启动,应急系统响应,防控手段日见其效,防治效果日益明显。一手抓防控防治,一手抓复工复产,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超强的执政本领正在书写满意的答卷。
突如其来的病毒,如冰峰雪崩,每一片雪花落在哪里都是一个寒冬。一枚病毒就能打倒一个人,毁灭一个家庭,葬送一个美好的梦想。疫情是测试剂、试金石、温度计、体检表,测试人心、人性、人格,检测国家的力量、社会的温度、人心的距离,也观测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真是假、是冷是热、是实是虚。国家的距离不在地理而在心理,人心的温度不光看平时更看患难时刻。中国对世界负责,共同命运需要共同打造。中国文化向来是投桃报李滴恩涌报,对幸灾乐祸投井下石者心中有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唯有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大疫需要大医,大灾呼唤大爱。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诗文是抚慰心灵的药剂。一些人用文字记录下这些个难过的城市难过的日日夜夜,那些难过的人难过的事难过的心,就像病人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甚至述说自己的隐私,说出来比憋着好;不少人无论身处疫区内外,无论是否有亲友受困,都在用文字用声音用图片用视频,表达自己的忧心同情焦虑赞美敬佩祝福;许多人在读诵这些诗文或泪流满面或热血沸腾,用或悲怆或凄美或激愤或豪迈的表达,安抚那一个个汩汩淌血的创口,激励那一颗颗疲倦消沉失望的心灵,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是那么情深深、意浓浓、热乎乎。诗文也是一把尺子,能测试灵魂的高度和心底的温度。我把草拟的小诗第一时间发给了身处湖北的几位朋友,一位官员读后说,建议把“在惊恐中煎熬,在焦虑中翻炒”“此刻你的心就像是一个泪包,一碰就是汪洋一片”删掉,武汉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市民的心情也没有那么糟糕;而一位艺术家朋友则建议把那句“摆一桌酒,煨一锅汤,炉上的日子慢慢熬”删掉,说此刻全武汉城没有人能有这样轻松的心情。我后来知道,他的亲弟弟终于挤进了医院,但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单。同一首诗,测出温差,冷暖自知。
这是一个悲情满满的日子,也是一个温情浩荡的季节,更是一个激情涌动的时刻,人类史册将记载这武汉一页、中國篇章。大地已经回暖,枝头正在泛青,只要不被自己打倒,英雄的武汉一定会从血泊中站起,江汉关钟楼顶上的国旗,依然昂首挺立,迎风飘扬,猎猎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