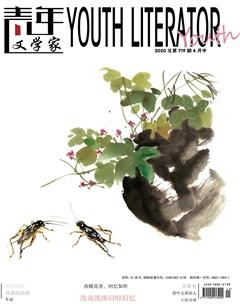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探微
肖尊烨
摘 要: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咏史诗创作高峰上两颗光彩夺目、不可忽略的明珠,是晚唐众多咏史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代表,两人也因此并称为“小李杜”。在咏史诗的创作方面,二者既有共鸣之处,同时又各有千秋。晚唐咏史诗的发展是应时之势,是反映时代变迁的作品,作为晚唐咏史诗创作的引领者,杜牧和李商隐由种种因素导致的创作核心的不同,使得两人的创作目的、创作思想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杜牧;李商隐;咏史诗;创作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背景
咏史诗起于东汉,至晚唐时,盛世衰颓,国家积弱,民生凋零,也正因此,在诗歌创作本就兴旺的唐代,怀着对前代的追思和对现世的激愤,晚唐诗人借古讽今,以史喻今,创作了大量富有艺术性和思想的咏史诗。在唐代之前,历朝咏史诗存留不过五十首,创作者仅三十人。终唐一代,咏史诗创作竟达一千四百余首,留名诗人二百有余,堪称空前;而晚唐又为其中之最,咏史诗十之占九,创作过千,诗人近百。单咏史诗之创作,晚唐堪称历代魁首。
(二)科举推动
科举制的发展,奠定了晚唐咏史诗空前兴盛的基础,是晚唐咏史诗繁荣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据《唐会要》载,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在谏议大夫殷侑的奏请下,晚唐科举恢复了史科,并且设立“三传科”,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纳入科举,并且史科及第者在优于其他科。在这一时期,不仅《尚书》《春秋》等作为儒家经典的史书受到重视,《史记》《汉书》等历代史书也因为“惩恶劝善,亚于六经”而被奉为“亚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史学得到极大重视,从而为唐代学子中涌现咏史诗人打下了创作的根底。
另一方面,晚唐科举中,策试几乎是各科的常设项目。以“三传科”为例,该科的考试即要求,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才予及第。在晚唐科举中,策试所致士人进行大量相关的学习,极大地锻炼了士人们的辩证思维。对考试主题的多角度思考,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士人们敏锐的洞察力,运用到实际当中,在咏史诗的创作方面,形成了晚唐诗人们独有的,对历史深刻而独特的思考,从而使得晚唐咏史诗在黯淡的乱世中熠熠生辉。
(三)体裁变化
中晚唐以前,诗歌创作,尤其咏史诗创作多为古体,律诗、绝句少有运用。自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提高了使用绝句的频率,为创作七绝、七律咏史诗探索了前路,开启了门扉。及至晚唐,杜牧成为晚唐首个大量运用七绝形式创作咏史诗的诗人。自此以后,七绝咏史诗大量涌现,成为咏史诗创作的常用体裁。而与杜牧齐名的李商隐,在七绝诗歌乃至咏史诗的创作成就也尤为突出。可以说杜牧与李商隐,在漫漫诗歌创作的长河中,对于诗歌以及咏史诗体裁变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
(一)创作背景
杜牧与李商隐同样身处晚唐大厦将倾的时代,面对国家凋零、内忧外患,两人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使得两人在同样渴望施展自身抱负、改变社会现状的同时,其社会理想、入仕追求乃至看待社会的心态都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辐射到咏史诗创作中,也使得两人的作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
杜牧出身于世家大族,其祖父是编撰中国第一部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通典》、开创史学新体裁的杜佑。杜佑不仅史学成就斐然,仕途也位及顶端,官至宰相。也正是承此荫庇,杜牧始终抱着天才的自信和坚定的政治志向,并且极好论政于军事方面,他坚信自己能够大展宏图,挽救衰颓的大唐,并曾作“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经世入仕的渴望。而另一方面,杜牧家至其父时,家道已经开始衰败,生于官宦世家,自小受到的教育培养和入仕志向与其坎坷不平、无处施展才华有所作为的仕途,一生立志救国却报国无门的矛盾,这些在杜牧的人生中形成了极大的影响。
杜牧博古通今,二十三岁便作出千古雄文《阿房宫赋》,明为论史,暗则借史讽喻当朝统治者唐敬宗沉迷于声色犬马,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这种以史论笔、针砭时政的做法,不仅仅体现在《阿房宫赋》中,更贯穿了杜牧咏史诗创作的脉络。现实的不平和理想的坚持,仕途的挫折的和内心的坦荡,充沛的自信和无处发挥的才干,种种碰撞汇聚,尽皆挥发于杜牧咏史诗的表达之中。
李商隐则与杜牧不同。李商隐的家世一般,尽管他曾宣称自己与唐朝皇室同宗,但这种既难以证明,且即使真实也因年代久毫无意义的关系,并没有为李商隐带来丝毫的益处。李商隐的祖辈虽然也紛纷踏上仕途,但大都官职低微,曾祖李叔恒官至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其父亲李嗣,先后任殿中侍御史、获嘉县令,因此这些并没有为李商隐带来什么荫庇。在李商隐十岁时,父亲便于浙江幕府去世,他的生活从此陷入困顿,处境微寒。成年之后,李商隐步入仕途的门槛也步步坎坷,考取进士多年才成功;而李商隐考取进士的当年,因自身婚嫁,妻子家世的缘故,无辜卷入当时的“牛李党争”,结果在考取进士的第二年,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复审中遭到除名。数年后,李商隐刚刚再入中书省,意图支持当时宰相李德裕的主张,结果又遭遇母亲逝世,李商隐不得不回家守孝三年,而这三年近乎彻底毁灭了李商隐的政治前途——三年之后,宰相李德裕随着武宗去世而失势,新帝宣宗李忱坚决反对先帝的大部分政策,并且极其厌恶宰相李德裕,李党的势力被迅速清除,牛党逆袭上位,李商隐自此再难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因李商隐一生挫折的遭遇,相比杜牧,李商隐对夕阳下的晚唐,对无力的时局,抱有着更加悲观的态度。如果说杜牧更强调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内心更加强硬,那么李商隐则相对要阴郁许多。李商隐从底层一步步走来,他贫困的出神和不幸的经历使他更深入地看到了晚唐社会种种弊病愈演愈烈,而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却从未切实解决过这些弊病顽疾,甚至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无情地毁灭了。这种面对现实的无奈、仕途受挫的苦闷,和其内心仍然抱有的、挽救这个朝代的政治愿望融入到一起,使得李商隐的咏史诗之中,更多的是融入个人对理想的解构,以及人生情感的发散。
(二)创作目的
正因杜牧和李商隐经历不同所致的,二人对晚唐的社会现状的认识和看法有所不同,政治愿景有所不同,而落在咏史诗的创作方面,二人的创作目的也有所不同。
杜牧的咏史诗,虽然也不乏讽刺之意,但其根本,在于“鉴”。杜牧深得“以史为鉴”的精髓,并通过咏史诗将这一作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比如其《泊秦淮》中流传甚广的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借南朝后主作《后庭花》沉溺于享乐,最终沦于亡国之君来比拟当世,后来的人又沉沦于这靡靡之音,却不知这实在是亡国之音。这其中,讽刺之意固然辛辣,但诗歌的根本目的,还是以史论史,以史警世。像另外一首《江南春绝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通过凭吊南北朝时建造的寺庙,不禁使人联想到晚唐相似的形势,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借古喻今的意味。因此可见,对于杜牧而言,“讽”只是一种手段或形式,即使诗句中蕴含了的讽刺意味,也只是为了推波助澜,加强“鉴”的作用。
相比杜牧而言,李商隐则更偏重于“讽”。如果说,杜牧咏史诗中的讽刺是为了突出警示意味,表达更庄重,更遵守“怨而不怒”的诗歌传统,那么李商隐的咏史诗,则更加直接,因事而讽,甚至不加修饰。同样针对唐玄宗因宠好女色,耽误国事以至大唐由盛转衰,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提到此间有关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往事,就以“为尊者讳”的态度,婉转地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其中的态度十分隐晦。而对比之下,李商隐在《龙池》中却没有丝毫避讳,直接写道:“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通过薛王畅快饮酒和寿王苦痛难免地对比,毫不遮掩地把矛头指向唐玄宗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却也引发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李商隐的咏史诗其讽刺意味的浓厚,还引得后人评价其“大伤诗教”,这其实就是诗人自身苦闷之下积蓄的情感太过激烈,对现实的表达太过深刻,以至于一部分文人难以接受而已。
以杜牧和李商隐咏史诗中题材交汇的作品对比,这种区别会更加直观。同样写《过华清宫》,杜牧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人路过华清宫抵达长安,几分感慨之下,依旧是借由“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的历史来发挥主题,警示当世君主;而李商隐却写“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运用反讽手法直白地针对唐玄宗进行贬斥。这首诗因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语调太过尖刻,以至于清代纪昀评价此诗“尖酸苛刻”。同样过华清宫有感而发,同样是念及昔日唐皇唐玄宗,杜牧和李商隐作诗却大相径庭,这首先是因为,两个人的创作目的完全不同的缘故。
三、艺术特征
作为晚唐诗人的顶峰,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并非毫无相近之处,但以两人高超的诗歌创作技巧,即使运用同一种手法,也能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一)诗歌用典
杜牧的咏史诗,常通过某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典型事件、标志性物品等进行发散式表达,引入宏伟的历史变迁,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如《赤壁》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歌开头便以沉没在泥沙中折断的铁戟为引,又通过这件古物,联想到数百年前风云变幻,赤壁之战令人怀想,再通过对东风、周瑜、铜雀台、二乔之间命运的构思,不觉间表达作者意味深长的思虑。表面上在问,假若东风不与周瑜方便,赤壁之战失败,那么二乔便要困锁于铜雀台中,强调东风的作用,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自己善于用兵,却无用武之地的困顿之心。这样的以小见大,以细微展开历史的宏大,是杜牧咏史诗中极为独特而精妙的艺术处理手法。
李商隐也善于将诗歌用典以小见大,但与杜牧借由细微的历史形象深入展开不同,李商隐常借由历史典型人物或历史事件,大胆而深刻地进行揭露并挖苦讽刺君王昏庸误国的表达。如七绝诗《隋宫》中“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同样是和杜牧一样写到“后庭花”的典故,李商隐就更为辛辣的以隋炀帝和陈后主两位亡国之君的地下相遇作为讽刺,看似问史,实则直接把这两位亡国之君比作朝堂上的那位君主;在《齐宫词》中,李商隐写到“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以“金莲”“九子铃”这些前朝君主淫乐玩耍的物件,突出亡国之悲、亡国之凉,进而指代现实。这种以前人喻今人,无一言以论,却以小题及大论,正是李商隐咏史诗创作的独到之处。
(二)比照形象
杜牧的咏史诗中,常以诗人构想的鲜活的历史形象来增强诗歌的渲染,强化诗歌的表达。如上文提到的《过华清宫》,进贡荔枝是史实,而一骑绝尘、妃子一笑,则是诗人对史实的艺术性表达。通过“妃子笑”这一镜头,表面上描写的是宫廷之中歌舞升平,实际上结合那段历史,以及之后的现实,这一形象背后,是大唐自此盛世转衰、山河凌乱。又如《台城曲二首》中“整整复斜斜,隋旗簇晚沙。”“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诗人通过描写国破之时,激烈的战争形势,对比陈后主逃命之时尚且不忘美人,共避井中这一狼狈而又荒唐的景象,既将亡国之君的面目丑态真切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又使人在感到可笑之余,对现实中晚唐危亡的形势产生警惕。
而在李商隐的咏史诗中,这种形象特写则又产生不同的效果。相比于杜牧构造历史形象,更多得是为了讲述道理,产生警示作用,李商隐将历史形象立体化,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如《北齐二首》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君王宠幸妃子之时,北周的军队已经侵入晋阳,作者通过同一时间段内,截然相反的两个场景,辛辣地讽刺了亡国之君的丑态;再比如另一句“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被攻陷的晋阳也已经被远远抛至脑后,君主竟然还在任从妃子的请求,去猎场围猎。作者通过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直接令人構想出亡国之君的荒唐与可悲。
(三)视角独特
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中,都十分擅长对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构。在杜牧的《题商山四皓庙》中写到:“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商山四皓是记载于《史记·留侯世家》的四位隐士,受吕后之邀出山辅佐太子。这一典故历来被人们评价颇高,而杜牧却超出常人,以更深层次的视角看到,这一事件引发了吕后专权,祸乱一时的后果;而在另外一首《题桃花夫人庙》中则这样写道:“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该诗首句转化息夫人的典故,末句又引出晋代富豪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古来多美色误国之见,而杜牧却超脱这个狭隘的角度,认识到息国灭亡,又岂是拘束于美色的缘故呢。
李商隐也极善于这种历史再解构的形式,如《梦泽》中,“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这首诗和《题桃花夫人庙》同样化用到楚王好细腰的历史典故,创作视角却完全不同,李商隐把批判的目标从君王转向拼命挨饿只为拥有细腰吸引楚王的宫女们,他并不是仅仅流于表面地批判这些人投上所好,而是揭露乱治之下,小人物麻木不仁、无力抵抗,只能随波逐流的状态。与杜牧看待事物的视角往往高屋建瓴不同,李商隐则是更为冷峻深入,这也是两人的经历所致。
正是由杜牧和李商隐支撑起晚唐咏史诗创作的两根擎天之柱,引导并推动了晚唐咏史诗的创作高峰,而也是在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带动下,晚唐咏史诗呈现出对历史的理性思考,这其中或含激烈,或含热忱,终究都是为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刘秀芬. 试论李商隐与杜牧咏史诗的异同[J].戏剧之家, 2018(27):221-222.
[2]叶颖.李商隐与杜牧咏史诗思想内容之比较[J].新西部(理论版),2016(11):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