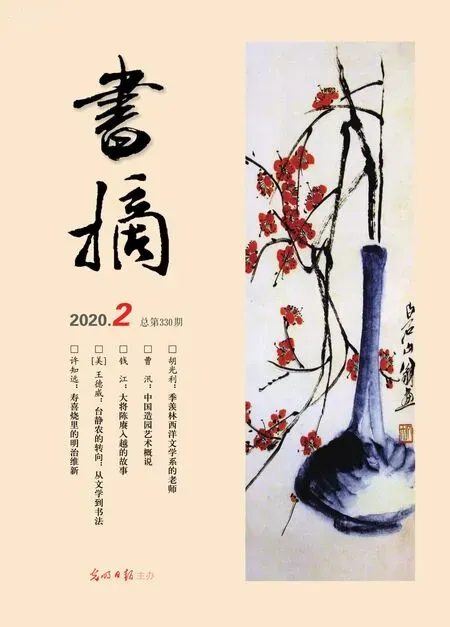谈谈废科举的影响
☉罗志田
从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义和团开始,中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了中央最高的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明当时朝廷上主政的一部分人认为正统的思想资源已经不起作用了。过去历史上也有一种常见的反智说法,就是所谓“读《孝经》以退黄巾”,说的是读书人没有用,遇到农民起义只能口诵《孝经》,希望这样就可以应对武装和暴力。但那只是民间的言说,到了朝廷真正用“怪力乱神”的东西作为政策依据的时候,表明主政者也认为类似《孝经》这样的正统思想资源已经无法解决当时的问题了。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想要了。义和团是近代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思想里找资源,不过找的是比较异端的“怪力乱神”的部分,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义和团最后也失败了,但这次的失败不仅仅只是一次打仗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就像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不满。所以义和团运动之后,大量读书人就不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政府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体制或结构问题。中国的传统政治,至少在唐中叶以后,是小政府的政治,接近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种社会大于政府的概念。我们常说过去是中央集权,那只是在中央所在地这一区域才体现集权;到了地方上,则大体是一种比较放任的政治。这是一种管理成本很低的模式,资源需求不多;也只有采取这样的管理模式,才不需要大量征收赋税。清政权能较稳固地存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清初那句“永不加赋”,让很多读书人认同了外来政权的统治。而加不加赋,重要的就在于你的管理需要支出多少钱。只有减少支出,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才能做到“永不加赋”。近代改革中提出了所谓“富强”的概念,这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强调的是国家不与民争利,对外不能多欲,才能够内施仁义。
小政府模式最怕的就是“天下有事”,这种资源匮乏的政府就连应付天灾都感乏力,更不用说打仗了。而近代的一个新形势,就是康有为强调的从大一统变成了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外来的压力接踵而至,中外的竞争既严峻又迫切,迫使中央政府一定向一个有作为的大政府转变。大政府的观念在中国是很晚才出现的,现在讲可能是正面的,在当时绝对受到诟病。对今天改变了思想方式的人来说,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向人民收钱;就像人民在议院里要有代表,政府才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一样。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典型的大政府观念。晚清的困窘在于,一旦中央政府选择了富强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在政治伦理和统治模式上做出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但当年的政府,以及关心国是的多数读书人,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就以废科举为例来看这个体制或结构的问题。废科举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办新学,而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钱不够。以前从民间的私塾到半官方的书院,都是一种低成本的教育。学子看的书可以是五百年以前的,甚至是两千年以前的,后来都还可以继续看下去;一家人买一套书,可以传到好多代以后。但新学堂是跟外国学的,教科书要随时编随时改,很花钱;又要设相当于校长的监督,还要教唱歌,教体育,教外国文,这些都是以前的私塾和书院的老师教不了的,必须以高薪从外面聘请。
钱不够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关键是不够的钱从哪里来。对政府来说,办学的大部分经费是要从民间出的。可是到底谁出?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除了更早与今日所谓国防相关的办理制造局、办海军、练新军外,清末新政,大体以学务为先。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筹款还相对容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会”,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费”(晚清的“公”在官与私之间,这不是今天所说的“公款”),大致可以从中募到办新学的钱。但过不了多久,其他新政又来了。随着学务而来的一整套面向富强的新政,样样都需要钱,都是需要政府投入或者政府引导投入的项目。
而当年的清政府并未改变其政治伦理,因而也不打算改变其政治模式。当时与新政相关的政府公文中常有一条很重要的内容,叫作“官不经手”。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类似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模式的一种延续。过去我们这些习惯了大政府模式的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条文。问题在于,官既不经手,又要推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出钱而“给政策”,事实上会让真正出钱的人很不舒服。而且各种“会”里的“公费”总数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于是款子就逐渐转向相对富有的绅,并进而转向一般的民。这些款项和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外债等,最终都落实在老百姓身上,成为不小的负担。
与废科举同时,还有一个过去注意不够的事件,就是北洋新军的演习。那次演习花费了一百万两银子,在当时受到了中外的关注。过去一直指责慈禧太后挪用的海军军费,也只是号称八百万两;而这次不过操演一下,就要支出一百万两,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中央政府没多少钱,又不怎么主张收钱的状态下,能进行这样的演习,体现出一种观念上的大转变。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不是很在意,但当年在华的外国人却很关注。那时的外国评论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过不了多久,中国军队会成为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这与现在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是一样的——正是西方引导和推动了一个“尚武”中国的兴起,但其又不愿看到一个这类中国的兴起。
那次我们不太注意的演习,也是在1905年,所以废科举和新军演习都是一个大事的不同面相,都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的体制转变。在我看来,这是最后导致清政府崩溃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那时的经费来源,要么加征各种临时性的费用,要么就借债,两者都是当时所采纳实施的。后来借债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卖国”的行为,其实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这可能是最合适的一个办法。借债总好过加赋,加赋就立刻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了。但对当下出钱的人来说,临时性的征收与常赋差别不大;而借钱要还,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基层的百姓身上。所以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个让人非常不爽的时代。
同时,上面的政府也很无奈,不论是外国要求改革也好,还是中国自身寻求改变也好,只要以富强作为目标,并以西方的做法来进行,就每一样都要用钱,而且从过去的观念看,其中不少是当时一般人眼中未必急需的支出。最显著的,就是增加了一个管理的费用。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最体现西方优越性的就是管理,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擅长的;其实中国过去不重管理,是节约了很多开支的。以私塾为例,假设以前办私塾十两银子可以运作一年,现在新学堂增加一个管理人,他一年可能就需要十两的工钱。教育还相对简单,其他方面的管理费用,还会更高。这样的支出,是地方无法承受的。
所以,这基本就是一个不归路——不改革则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花钱;且多一项改革举措,就增进一步经费的窘迫,直至破产。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想,对清末的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和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废除一个实施了上千年的制度,体现出政府的决心有多大。同样重要的还有清末立宪的决定,这是否定皇帝自身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决策,表明当时政府寻求改变的决心的确很大。一旦实行,皇帝就真成虚君了。过去有人把这一举措说成是欺骗,可能把清政府想象得过于高明了。清廷是否认识到人民是可以欺骗的,并有意将欺骗人民诉诸朝廷政策,我是比较怀疑的,因为那简直清醒得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了。当年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新政背后的体制或结构问题,以及义和团运动对读书人产生的根本影响。
实际上,科举制的废除,其影响远超过辛亥年的政权鼎革。
过去的人,可以通过读书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制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只要你书念得好,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多人说这是对地主有利的一种体制,其实不完全是。当时的农村,一个人书念得好,可能全家族全村的人都会出钱供他念书。以前有公田制度,公田在中国的乡村里曾占很高的比例,其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当然,公田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把持;很可能当初公田的形成,也是这些人付出较多。而公田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资助家里没有钱但能读书的人。考中秀才可以领到多少米,考中举人可以领到多少肉,一直到毛主席做调查的时候,还是这样,不过那时领米领肉的也包括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了。
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废科举只是最后的一步,废之前还有一个改科考。例如以前要小楷写得好,后来不那么注重了。重要的是科考的内容改了,以前考四书,后来考新学考算学。又如把经学放到后面较次要的场次,把史学提到前面更重要的场次,这对于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当然很满意,但是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那么继续练毛笔字,继续念原来的书,最后到了考场才发现都不一样了,连考试参考书也变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就改变了考试的公平性。以前每个人可以预期自己在考试中有怎样的表现,就能进入某一级优秀的行列,但是废科举之前的改科考,已经把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部分修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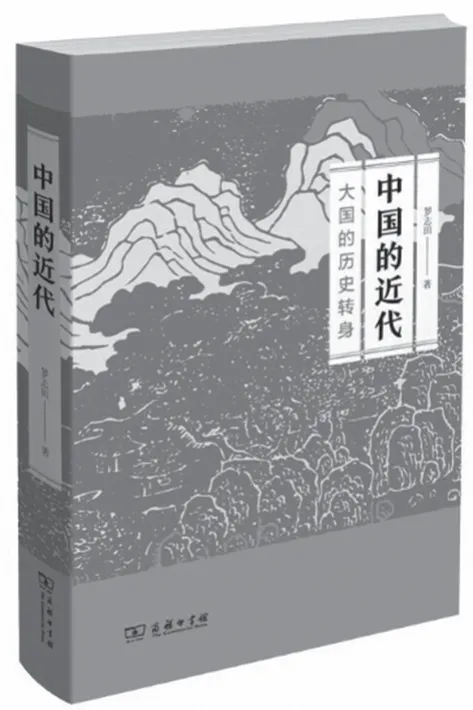
科举制的废除,当然是更彻底的变革。在那之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