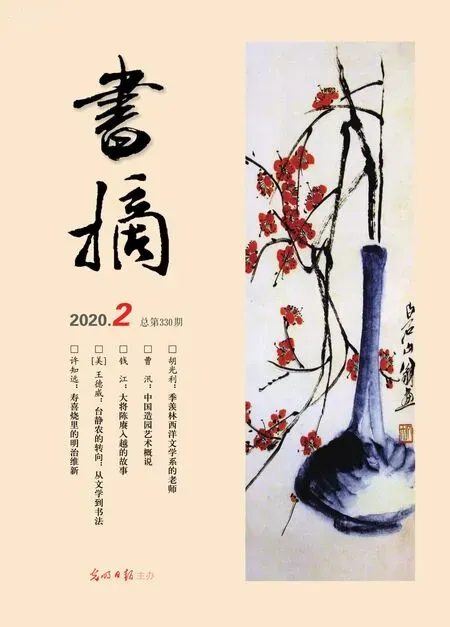乡村是我们的老家
☉刘亮程
对一根木头的尊重
前不久,我在喀纳斯景区,一个山庄老板告诉我,说他那里有一根奇异的大木头,让我过去看一看。我对大木头一向好奇,就跟了去。一进山庄,果然立着一根非常高大的木头,头朝下栽在土里,根须朝天张牙舞爪,我看了非常生气,对老板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大的一棵树头朝下栽着呢?”老板说:“是棵死树。”我说:“死树也是树。它有生长规律,它的生长是头朝上,像我们人一样,你不能因一棵树死了,就把它头朝下栽到地上。假如你死了,别人把你头朝下埋到土里,你肯定也不愿意,你的家人也不愿意。”
这个老板显然不懂得该怎样对待一根木头。谁又懂得这些呢?我们现在做什么事都普遍缺少讲究,我们只知道用木头,用它做建筑,做家具,但不知道该怎样尊重地用一根木头,我们不讲究这些了。但我们的前辈讲究这些,我们古老文化的特征就是对什么都有讲究。有讲究才有文化。没讲究的人没文化。我们的祖先把传统文化系统建筑到房子里,人住在里面。
记得几年前我装修一个酒吧时,买了一根长松木杆,要安在楼梯当扶手,木工师傅把木头刮磨好,问我:“这根木头该怎么放?”
我说:“你说该怎么放?”
他看看我说:“应该是小头朝上,大头朝下。我们老家都是这样做的。”
木工师傅的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显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他知道最起码的一点,木头要小头朝上,大头朝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树活的时候就是这样长的,即使它成了木头,做成一个楼梯的扶手,也要顺着它原来的长势,不能头朝下放。这是谁告诉他的呢?就是我们乡村文化给他的。在乡村,老人都是老师,好多事情他们懂,知道讲究。老人按讲究做的时候,年轻人就学会了,文化就这样一代代往下传。
我小时候看大人盖房子,大人干活时我们孩子都喜欢围着看,尤其是干技术活,因为这些活我们一长大就得干。干的时候再学来不及,只有小时候有意无意去学。大人们盖的是平房,房顶的椽子一律大头朝前。檩子横担着,没有高低,但也有讲究,要大头朝东。房子盖好了,一家人睡在一个大土炕上,睡觉也有讲究,大人睡东边,睡在房梁的大头所在的地方。小孩睡西边,大梁小头所在的地方。我从小就知道了盖房子木头该怎样放。有的人家也不讲究,看到不讲究地摆放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
中国人讲究顺,这个顺就是道。道是顺应天地的,包含了天地万物的顺。我们干什么事不能只考虑人自己顺,要身边万物都顺了,生存其间的人才会顺。木头的顺是什么?就是根朝下,梢朝上,树活着是这样长的,死了的木头也是树,也应该顺着它。我想,即使一个没讲究的人,看见一棵大树头朝下栽在地上,心里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不顺。我们住在一个木头摆放不顺的房子里,生活能顺吗?
有讲究的房子
好多年前,我陪母亲回甘肃金塔老家,母亲1961年逃饥荒来新疆,第一次回去。老家的居住环境和我们在新疆的差不多,村子也在沙漠边上,靠种地为生,刮起风来黄沙满天。耕地比新疆少,收入应该也少。但是老家村里的房子跟新疆的不同,每家都住四合院,正门进去是一块照壁,照壁对着是正堂,堂屋里面摆着祖先的神灵,那是一间空房子,平常的时候什么都不放,只放着祖先的灵位。家里做了好吃的,先端一盘过去敬献祖先,祖先品尝过了,再端回来自己吃。
新疆农村汉民的房子,四合院没有了,一排平房,后高前低。我走过许多乡村的许多人家,没看到哪一家会留出一间房子给自己的祖先。不管有多少间房子的人家,所有的房子都是住人的,盛放物品的,没有一间房子空出来留给祖先和精神。祖先被我们丢掉了。
现在新农村的房子更不讲究了。新农村之家的设计者在设计房子的时候,只考虑到大卧室小卧室、客厅厨房,只关心电视机放哪,冰箱洗衣机放哪,他们考虑到把祖先放哪了吗?没有。当这一切放置好了,一个家就算安置妥当了,哪都是东西,祖先的位置没有了。

汉瓦当中的“家”字
而在老家农村的家庭,大都有两个居所,一是人居住的房子,一是供奉祖先的高堂。家家都知道给祖先留一个房子,家和家产都是祖先留下的,走了的祖先被安置在正堂里,逢年过节,有灾有难,会过来求祖先保佑,祖先让人们心安。如今我们有三间或十间房子,都不会想到有一间给祖先和精神,那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之家。
万物共居的家
甲骨文的“家”,是屋顶下面一头猪。这个最古老的象形汉字在告诉我们,“家”是天下万物和谐共存的家,我们的家园不仅有人,还有其他的动物,我们不仅跟人相处,还要跟人身边其他生命和睦相处。
我理想中的家,有一个大院子,家里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三代同堂,最好还有太爷、太奶,四代、五代同堂,就更圆满幸福了。人住的房子边是牛圈和羊圈。房前屋后有几棵树,树有小树大树,小树是父亲栽的,长得不高也不粗,大树是爷爷太爷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祖先栽的,这棵树应该有几百年的岁数。我们在这样的树下乘凉,自然会想起栽这棵树的祖先,也曾经一样坐在树荫下听着树叶的哗哗声,在夏天午后的凉爽里,他也听着树上的鸟叫,也曾年复一年看到春天树叶发芽,秋天树叶黄落。我们坐在这样的一棵老树下,自然会把自己跟久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这些时,其实就看到了祖先,感觉到祖先的气息。在一棵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就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家里一棵老树的意义。

《说文解字》中的“家”
在一些乡村,还能看到这样的院子,院子里的人家,三世或者四世同堂,院子里有鸡鸣狗吠,菜园里每年长出新鲜的蔬菜,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家园啊!而这个让我们温馨自在地生活了千百年的家,也正在广大农村逐渐消失。
我去南山采风,看到那里规划的一片新农村,红色的屋顶,彩色的墙面,每家每户都整整齐齐,院子全是水泥地,房子里全是现代的家具,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但是看完以后我还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少了什么呢?牛羊不见了,狗不见了,鸡不见了。问当地的负责人:“这个农家院子里怎么没有家禽和家畜?”负责人说:“那些动物都被放到外面集中饲养了,我们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标准就是要让人畜分居。”
在接下来的座谈中,我对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说,新农村不应该只是人的新家园,我们和家畜和谐相处几千年的生活,不能在新农村这里中断了。应该赶快把赶出去的牛羊请回来,把鸡和狗请回来。
中华文明的“家”,是从屋顶下面一头猪开端。如今变成屋檐下面只有人的穴,一个万物共居的家里,只剩下孤单的人。
弯曲的乡土路
乡村土路大都是弯曲的,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这样笔直。然而就在弯曲的乡村土路中,蕴含着别样的乡村文化和哲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样的人就会走出什么样的路,人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在土地上踩出什么样的脚印。
乡村土路就是村人在大地上行走的一种方式,那些弯弯曲曲的乡土路,总是在绕过一些东西,又绕过一些东西——绕过一棵树、一片菜地、一堵土墙、一堆坟、一湾水坑。不像现代高速公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乡土路弯曲的本身蕴含着人走路的一种谨慎和敬畏。它不强行通过,不去践踏,尽量地绕,绕来绕去,最后把自己的路绕得弯弯曲曲。但是在它的弯曲中,保留下土地上许多珍贵的东西。
好多年前,我去伊犁昭苏,看到一棵大榆树立在路中间,感到非常惊奇。当地人说:“路修到这里的时候,要通过这棵大榆树,当地政府和包工头要把这棵榆树砍了,因为一棵树立在路中间不好看。为什么没砍呢?这棵树是当地的神树,附近村民多半有信仰萨满的传统,有病有灾了,会在树上系一个布条,在树下许个愿,灾病就过去了。听说这棵树灵得很,前来祭拜的人终年不断。当地人不愿意他们的神树被砍,大家联合起来保护这棵大树。”
最后这棵树留了下来。但并不是村民们保护了它,而是修这段路的包工头突然出车祸死了。老板是主张砍树最卖力的人,推土机都开到了跟前,要把树推倒。树没倒,老板先死了。这件事把人们震住了,大家都害怕了,这棵树就这样留了下来,它就立在公路的中间,高大无比,几人才能合抱住。好多车辆经过这里,会自然而然停下来,在树边拍照,树上挂满了当地人系的各种颜色的布条。我们也在树下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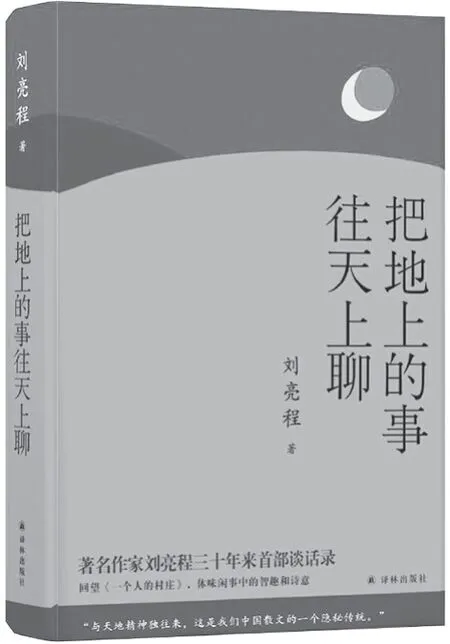
又过了好几年,我再去昭苏的时候,那棵树不在了。什么原因呢?说是有天晚上一个司机可能开车打盹了,没看到前面的树,一下子碰到树上,树把人撞死了,树犯法了,所以树被砍掉了。你看人多么不讲道理啊,树又不动,怎么会把人碰死呢?明明是人碰到树上死了,却说树把人碰死了。中国人都知道杀人偿命,树撞死人了,所以必须把它砍掉。当地人曾经视为神树的一棵大树就这样被砍掉。
难道人在修这条路的时候,就不知道稍微让一下,绕过这棵树吗?不能。这是现代高速公路的原则,它追求最短的距离,追求运输成本的最低化,当它绕过一棵树的时候,路程增加了,修路成本增加了,运输费用增加了。所以不能绕。
但是我们的乡村土路会绕,懂得绕。乡村文化中有“绕”的理念,现在人没有这个了。我们看到新修的高速公路,几乎都是笔直的,见山劈山,遇沟架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在高速公路经过之地,多少房屋被拆掉,多少农田被侵占,多少树木被砍伐。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住现代人走直路,追求最短距离、最低成本的心态。
但是,弯曲的乡土路告诉我们,世间曾经还有这样一种走法,还有这样一种弯来绕去,不惜耗费时光,总是绕过一件事物,又绕过一件事物,把自己的路程无限地拉远,尽量不打扰践踏大地上的东西。这样一种绕行的方式,是乡村文化中非常珍贵而现代人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