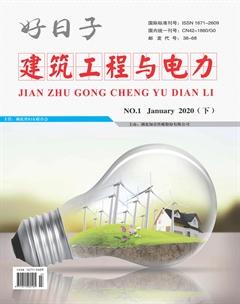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完善
王小英
一、医疗纠纷与行政调解的概念辨析
我国立法长期对医疗纠纷并无明确的法律定义。学界对此也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的理解。广义的医疗纠纷指病人及其亲属在诊疗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发生的争议。主体上既包括患者(病人)也包括其家属,范围上既包括病人在医疗机构就诊过程中因诊疗行为与医疗机构发生的纠纷,也包括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过程中非因诊疗行为发生纠纷。例如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医务人员态度不佳而发生的争执,因医院地板打滑而摔伤发生的索赔纠纷。狭义医疗纠纷指医患双方对疾病的治疗后果及发生了除原病灶外的损害原因认识不一致发生的分歧与争议。12018年10月生效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2条首次在立法上将医疗纠纷界定为: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可见,立法采纳了狭义的医疗纠纷概念,医患双方非因诊疗活动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医疗纠纷的范畴。但此定义中的医患双方中,作为纠纷主体一方的医方是否包括医务人员,而作为另一方主体的患方是否包括患者的近亲属似乎并不明确。本文认为,虽然直接对患者进行诊疗的是医务人员,但其诊疗行为是职务行为,其法律责任由其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因此医方的主体应为医疗机构。同样,由于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发生纠纷时往往由其亲属代为主张,但其亲属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代理行为,其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是患者而非其亲属,因此患方的主体应为患者。
在实践中,与医疗纠纷相近似的概念还包括醫疗事故、医疗损害、医患纠纷等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规范和诊疗护理规范,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2医疗损害是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3可见,医疗损害是医疗事故的上位概念,医疗事故只是造成医疗损害的原因之一,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但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医疗差错和医疗意外同样构成医疗损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医疗损害赔偿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只有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意外由于是客观因素所引发,医疗机构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从医疗纠纷的角度看,医患双方对是否属于医疗意外往往各执一词,因此,不论医疗事故、医疗差错还是医疗意外,均应纳入医疗纠纷的范围。医患纠虽然经常与医疗纠纷混用,但从语义上看,医患纠纷可以包括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各种争议,不局限于诊疗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其含义相当于广义的医疗纠纷。与立法上对医疗纠纷的定义不符。
对于行政调解,目前法律尚无明确的定义。学界的观点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行政调解是由国家行政机关主持,以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从而消除纠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4还有的认为行政调解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是与行政活动相关的行为。5还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调解是一种事实行为。6本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调解并非是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机关只是以中立者的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因此并非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不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达成的协议也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因此不应称其为事实行为。从本质上看,行政调解既不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也不是与行政职责相关的行为,而是行政机关服务行为,它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也是行政机关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行政服务。明确行政调解的性质,有助于明确行政调解的定位,改变目前以行政管理为导向的调解模式,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
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一)行政调解的优势未能发挥
与其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加油独特的优势:一是高效便捷。诉讼需要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等诉讼阶段,加之医疗纠纷中医疗损害的原因和程度的认定往往依赖于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导致医疗纠纷通常需要漫长的诉讼周期才能最终解决纠纷,当事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且诉讼过程中举证、质证、辩论中浓厚的对抗性,也往往导致败诉的一方当事人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与此相反,在行政调解过程中,不受严格的程序限制,调解员可以更为灵活地运用调解规则,根据案情发展把握调解进程,通过调解员的因势利导和说服教育,在双方当事人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及时妥善地解决纷争。二是专业性。医疗活动涉及深奥的医学知识和复杂的诊疗过程,因此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对于不具备专业背景的人士难以胜任。医疗卫生行政机关拥有丰富的专业人才资源,调解员依靠其所掌握的相关医学知识,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
但从实际效果看,行政调解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医疗纠纷数量总体上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医患双方自行和解的方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诉讼方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行政调解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广东为例。2009-2013年这五年间,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平均占比为86.4%。行政调解方式处理的医疗案件处于低量徘徊状况。7以北京为例,医疗纠纷投诉案件数量从2010年的1484件减至2015年的1273件。而从平潭综合实验区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来看,其受理的医疗纠纷投诉案件的数量逐年减少, 从 2010年的20余件减至2015年的不足10件。8 这表明行政调解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在制度设计上难以获得医患双方的认可和信任。
(二)调解主体的中立性遭受质疑
卫生行政机关具有管理医疗活动和规范医疗秩序的职责,医疗卫生行政与医疗机构虽然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但医疗卫生机构与医疗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因此,医疗卫生行政机关出面主持行政调解,患者往往对调解组织能否保持中立性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患者认为调解方案对医疗机构更为有利时,更是会认为行政机关有意偏袒。导致调解失败。有关的调查数据显示,67.7%的患者认为以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是公平的, 而仅有23.7% 的患者认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是公平的。9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由于医疗卫生行政机关具有对医疗事故的调查权和行政处理权,一旦医疗纠纷可能涉及医疗事故时,医疗机构也不愿行政机关的介入,以免遭受行政处罚。从而更愿意采取与患方自行和解的私了方式。
(三)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模糊
在三大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方面,司法调解协议的效力最强,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调解协议之,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而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最为尴尬。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其法律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调处后所形成的明确载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这一文件从法律性质上看,不属于法律或司法解释,仅是具有司法指导意义的政策文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效力。
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行政协议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法院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规定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或确认其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并起诉到法院,法院应当受理并应依原纠纷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和判决。10有的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不需要对行政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进行直接确认,可以直接出具与民事司法裁判具有同等强制执行效力的的司法调解书。11这种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认识上的不一致和分歧,严重制约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效能的发挥。
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完善对策
(一)行政调解立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十分零散,散见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而且内容规定的比较原则和简略,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就医疗纠纷调解而言,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由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可以行政调解。但也仅此而已。由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在实践中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因此出现取消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主张,这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的起草过程中即可显示出端倪。在该条例草案的“一审稿”第5条规定的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为:(1)医患协商;(2)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人民调解;(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途径。该条直接删除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至“二审稿”才在“一审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向卫生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调解”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并最终在正式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中得以维持。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实际运行效果不彰,究其原因,法律规范的严重缺失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在系统化的《行政调解法》出台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调解的基本原则、调解机构的组成和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使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工作在法治化的轨道有序进行。
从行政调解范围看,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仅规定了确定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才可以适用行政调解,除此之外的医疗纠纷没有调解权,2018年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将行政调解的范围扩大到医疗纠纷,扩大了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是立法上的重要进步。但行政调解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对医疗事故和事故等级的确定应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对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态度、医疗收费等方面的投诉,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法处理,亦不应适用调解。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台湾地区“卫生署”起草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中将调解作为诉前强制程序,目的在于“通过调解鼓励医患之间的沟通,已达到限制诉讼的价值取向。”尽管有观点认为调解强制有悖于调解的自愿原则。但实际上强制调解只是在行政权的引导下为当事人创造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倡导当事人通过非对抗以及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并非强制其达成协议,医患当事人双方是否愿意达成调解协议完全由其自主决定,这与调解的自愿原则并无实质的冲突。这种调解前置的做法有利于行政调解作用的发挥,可资参考和借鉴。
(二)行政調解组织的中立化和专业化
目前,各地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的医政科处(科、股)负责对医疗纠纷投诉的接待和处理工作,虽然有相对固定的人员,但并非专职人员,未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这容易产生以下问题:一是患方容易对卫生行政部门在调解中的中立性产生质疑。担心卫生行政部门出于各种利益关系在调解中偏袒医疗机构。二是卫生行政部门工作本身工作任务繁杂,人手不足和精力有限导致无法对每一起医疗纠纷进行深入细致的调解,调解质量大打折扣。三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少并非医学专业出身,大多没有医疗从业经历,医学知识和经验严重缺乏,加之缺乏调解经验和技巧,难以胜任对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要求的调解工作。
对此,有学者主张将医疗纠纷调解行政调解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调解人员包括司法行政官员和卫生行政官员。12也有学者提出在政府法制部门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13另有学者提出在医学会下设置调解机构。14还有学者提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15本文认为,鉴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应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定位为行政服务。在卫生行政部门内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该中心负责医疗纠纷的投诉、咨询和调解的受理,具体的调解工作由中心聘任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员不再由卫生行政部门人员担任,而是聘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担任调解员,建立调解员名册供当事人选择。以此实现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中立性,从而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和认可。另外,调解员的沟通技能对于调解的成败有重要的影响,调解员上岗前应当进行开展适当的调解技巧和技能的培训,以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
(三)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对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效力模糊的状况,有观点认为,我国应立法赋予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以弥补当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最大的软肋。16这种做法似乎过于激进,偏离目前对调解协议的主流理论和实践认知。按照本文将行政调解视为行政服务的观点,由于行政机关只是对纠纷解决提供服务,没有对纠纷解决的决定权,行政调解协议能够充分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存在行政强制,当事人所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应当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为了赋予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出具确认决定书,产生强制执行的效力。第二,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予以公证。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公证,由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
注释:
[1] 林文学:《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 页。
[2]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
[3] 《侵权责任法》第54条。
[4] 湛中乐:《行政调解、和解制度研究—和谐化解法律争议》,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96-897页。
[5] 胡建淼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46页。
[6] 赵银翠:《行政过程中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173-174页。
[7] 广东医疗法治法治状况研究课题组:《广东医疗纠纷处理调研报告》,http://www.gddx.gov.cn/fzgdyjzx/146285/149060/index.html
[8] 薛舒予:《论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中国卫生产业》2016年第4期,第8页。
[9] 方鹏骞,王桂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制度构建》,《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年第3期,第178页。
[10] 王偲:《法院有审查行政调解协议的权利吗》,《广西政法报》2003年11月5日第1版。
[11] 2012年4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州海关、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福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福州市知识产权局共同签订《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大调解”联动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政部门组织诉前调解可以引导当事人自行约定,请求人民法院在行政调解协议的基础上依法出具与民事裁判文书同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司法调解书,
[12] 陈美雅:《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比较研究》,《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3期,第190页。
[13] 舒广伟:《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中国卫生法制》2011年第6期,第51页。
[14] 唐春燕:《论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构建》,《现代医院管理》2006年第4期,第12—17页。
[15] 张虹:《论医疗纠纷的调解制度》,《医学与社会》2006年第1期,第35—37页。
[16] 龚文君:《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意义、问题及完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58頁。
(作者单位: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