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副面孔”:城市美学与澳门电影的影像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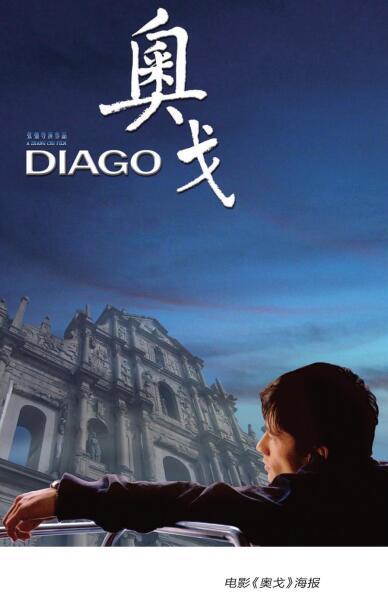
电影艺术需在故事虚构性与生活真实性之间寻求平衡点,虚构建基于真实之上,如此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才容易忘我地进入亦真亦幻的影像时空。
对于城市电影而言,独特城市时空的美学营造,是观众获得真实感最直接的方式,因此,城市电影应尊重城市空间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指向,透过美学化的电影艺术手法将之呈现;更进一步看,优秀的城市电影中倡导的城市伦理与生活方式,契合了城市观众的价值认同与身份归属等多层心理需求,因而城市电影需尊重城市特有的风土人情、社会阶层、职业特色及生活方式,以影音符号建构适合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气质。
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要求,城市电影应以城市美学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城市美学的对象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即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交通工具、灯光店招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城市景观要素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工景观要素,常常提及的如城市纹理、建筑模式、建筑高度、天际线、城市轴线、软硬界面、节点等[1],同时包括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如穿着打扮、节日庆典等;另一方面是以城市中人的生存处境为主要对象,观照处于不同社会阶层、职业、文化群落中的人对于城市的情感、情绪、感受和体验以及城市公平与正义、人文关怀等城市伦理与文明秩序的问题。[2]
从城市美学的视角观察电影,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城市电影的边界,探寻城市电影的美学特质,思考城市对于电影类型与风格创造的影响及可能性,尤其是探索城市符号在电影中如何具备审美功能这一美学问题;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城市空间并非现实地理空间的简单再现,而是指涉多种因素的文化建构。从澳门电影建构的澳门城市想象与地理城市空间的对比中,可以揭示澳门城市文化中存在的多种矛盾张力,为城市家园的积极建设提供一些美学的思路。
澳门是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纵览近百年澳门电影(本文仅讨论故事片类型),来自国外、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本土四大文化背景下的导演以影像建构着澳门城市的想象,呈现出六种主要的澳门城市形象及美学特征——跨文化爱情圣地之澳门、情义江湖之澳门、休闲娱乐之澳门、亲情疗养之澳门、“童年不变、怀旧小城”之澳门、坚强女性之澳门,揭示出四组深刻的矛盾张力——文化张力、空间张力、时间张力与性别张力,其内在规约着澳门电影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向。
一、和而不同:跨文化语境下的澳门景观
1952年,美国上映了第一部以真实澳门城市为拍摄背景的黑白片Macao,与其说这是一部跨国警匪片,不如说是一部展现澳门这座城市东方神秘文化的历奇片。影片重点选择澳门的港口、商业街、娱乐场(赌场)、陆地船仓、近海等城市空间,将城市中不同群族(如美国人、葡国人、日本人、华人等)、阶层与多样化职业类型(如警察、歌女、摄影师、理发师、盲人算命师、人力车夫、商人、赌场老板、黑社会)一一呈现。
导演尤其注重透过多样化交通工具(如邮轮、汽车、人力车、自行车及小渔船)以动态镜头捕捉都市生活的繁华与多元,如影片中最为精彩的都市浪漫爱情场景,均选择在动态化的交通工具中拍摄完成。从城市美学的角度看,此部影片最为独特的美学贡献,是美国导演将好莱坞电影中繁华都市的动感植入到了澳门“城市”的想象之中。更为可贵的是,作为开启澳门电影跨国叙述的首部影片,它并没有特意表现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感,而是秉持一种历奇态度,借西方镜头下的东方人(如摄影师的神秘面孔、盲人算命师的未卜先知、黑社会手中完胜手枪的飞镖)发现澳门这座城市的东方神秘美感。
澳门是一座最适宜表现东西方跨文化之美的样本城市。如果说1952年的历奇影片Macao只是相当表面地呈现澳门城市中东西方文化的有序并存,进而初探东方文明的神秘美感,那么,1995年由导演蔡安安、蔡元元根据澳门葡萄牙籍土生作家飞历奇小说改编的本土爱情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在澳门这座城市中由对抗走向“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并存的美感历程。影片中明确择取了大量隐喻东西方文化特质的澳门城市景观——葡萄牙人的狂欢节舞会/中国元宵节的舞狮表演、明亮宽敞自由的葡萄牙贵族住宅别墅/灰暗窄小封闭的华人居住区雀仔园、象征西方开放激情型爱情观念的海边栈桥、电影院/象征东方保守安定型爱情观念的亚婆井、西方绅士的白西装/中国女性的黑色大辫子、西方教堂神圣的婚礼/中国院落热闹且带宗教色彩的满月酒、西方医院的不出診/中国家庭式婴儿接生、西式住宅里情趣的红酒之夜/中国少女神秘的洞房花烛夜、西餐的贵族礼仪/中餐的平民亲和等等——诸种城市景观成为中西方文化表征的符号而被导演以文化平等的态度运用于影片的构建中,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澳门华人与葡萄牙人在生活方式、文化理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与对抗,肯定男女青年勇于追求真爱,冲破种族、文化与等级隔阂、愿为对方付出所有的爱情观念。
客观展现文化差异与对抗却又能走向文化和解与美满融合,例如澳门土生葡萄牙人便是中葡爱情友谊的结晶,这种跨文化之美的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极其少见,惟有澳门这座独特的城市才诞生了《大辫子的诱惑》带有世界意义的跨文化爱情经典影片。
二、“澳门街”:空间张力与城市想象
在澳门的城市空间中,除去海洋亟待被发掘外,占陆地空间的主体建筑是娱乐场、教堂与中西方商用、民用建筑,这种城市格局自然限定着澳门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格局。然而,我们发现澳门电影中的城市想象又远比这丰富,而这种想象空间的最初拓展与香港文化力量的参与密不可分。
香港在1956年不仅为澳门输送了强劲的黑社会人力资源[3],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为澳门电影输入了表现“江湖情义”黑社会题材电影。1987年香港导演张同吾在澳门拍摄《江湖龙虎斗》,选择了表征“江湖”空间的夜总会、码头、赛马场与表征救赎力量的“宗教”空间如修道院、教堂、黑沙海滩,探讨江湖人士在兄弟情义与爱情之间两难选择的问题,建构了澳门黑社会的“江湖”价值观——恩怨分明、有仇必报、胆识即英雄、富贵险中求、感恩图报与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兄弟情义观。香港导演充分利用了澳门城市中的宗教元素,将“宗教”世界设置为“江湖”世界的救赎力量之一,同时将澳门与香港并置,赋予澳门一种“童年”“怀旧”色彩与“几十年不变的味道”的澳门形象,反衬出“江湖”爱情短暂却炙热的悲剧色彩,这可以说是澳门城市赋予黑社会电影的独特元素,而澳门作为香港城市形象对立面的美学特征——“童年”“怀旧”“恒久不变”——也初步确立起来。香港导演杜琪峰的《暗花》(1998)、《放逐》(2006)、《复仇》(2009)和林超贤的《激战》(2013)可以说是澳门作为“江湖”想象的延续与发展。
澳门城市形象长期被定位于“赌城”这一单一旅游形象,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原因,当然也与赌场占据城市视觉景观主体有着直接關系。因此,2002年以来,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试图重塑澳门城市旅游形象为“博彩娱乐”“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的结合。截至2004年,除了澳门居民认同澳门“文化之都形象”“休闲度假形象”“博彩娱乐形象”外,外地游客更加认同澳门作为“博彩娱乐形象”高于“休闲度假形象”,而对“文化之都形象”认同度最低[4]。有鉴于此,为逐步改变澳门城市形象,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邀请部分香港导演拍摄了带有旅游宣传性质的城市电影。
在1989年香港导演王晶开创的《赌神》系列“赌片”中,澳门只是作为与蒙地卡罗、拉斯维加斯一并出现的文字符号,并未以澳门城市为主要拍摄地。1992年王晶以澳门葡京大酒店为主要拍摄背景的传记片《赌城大亨》(—、二)仍将澳门作为“江湖”赌城形象来塑造。2007年后随着澳门威尼斯人、新濠影汇等路凼区旅游度假建筑综合体的陆续建成与运营,澳门城市形象获得了重塑的机遇。2014、2015年王晶受邀拍摄以澳门路凼旅游度假区为背景的贺岁喜剧影片《澳门风云》(一、二),由于澳门已经回归,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重点又要打造“休闲度假”城市形象,因此澳门作为“江湖”空间已不是表现的重点,澳门重点展现富丽堂皇、时尚休闲的酒店及户外泳池、高科技感舒适十足的澳门居住别墅以及充满“澳门街”底层温情的龙华茶楼。
比《澳门风云》更进一步,2015年香港导演叶念琛拍摄了表现“澳门街”情怀的亲情电影《十月初五的月光》。这部电影虽是为香港2000年TVB热播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又称《澳门街》)结局,延续着电视剧一以贯之的“澳门街”情怀,但是对于澳门城市形象的塑造角度却十分耐人寻味。为帮助精神创伤病人疗伤,澳门的街道漫游、赌场娱乐、旅游塔蹦极、教堂祈祷等城市活动将澳门营造成为精神疗养胜地,而贯穿所有城市活动的情感内核则是澳门“横街窄巷”温暖的亲情味。影片中以金胜为代表的江湖世界,获得成功的关键仍然来自于“澳门街”给予他的友情支持。在“澳门街”的亲情社群中,大家都像一家人,面对困难时可以同心协力,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倡导为了别人的幸福愿意牺牲自我的《祝君好》式的美德。
“澳门街”作为社会底层亲情之美的空间想象,在澳门电影中并不少见。但能将澳门街道景观在电影中充分展现其美学功能的电影却并不多见。其中,香港导演彭浩翔于2006年拍摄的父女亲情影片《伊莎贝拉》,可以说有意识地开掘了澳门街道的自由美学。在“父女”二人尽释前嫌、感情步入新阶段时,父亲深夜在街头畅快淋漓地教女儿爆酒瓶,而后在漫长的街道上自由奔跑的场景,将澳门街道的斑驳陈旧、自由畅快的美感特征抒情地表现出来,此刻街道成为溢满情感的容器。在艺术手法上,澳门城市景观参与电影艺术空间营造需要更为重要的隐喻蒙太奇手法。《伊莎贝拉》中澳门司警马振成在游戏人生一系列镜头过后,紧接着导演插入了一组旋转着的被凌乱电线分割与高楼压迫的狭窄天空镜头,隐喻着澳门回归前夕小人物们看不清未来的迷茫状态。
同样,澳门本土导演徐欣羡2017年拍摄的姐妹情谊影片《骨妹》,也运用了隐喻蒙太奇手法,当诗诗离开澳门10年后重返澳门,从银河酒店走上街,她用陌生而犹疑的眼光打量澳门发生的巨变,紧接着是一组代表着进入澳门路凼新娱乐区的路凼连贯公路圆形地的镜头,隐喻着人们对于澳门城市发展方向的困惑,通过隐喻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引发观众深思。
三、何以为家:澳门回归主题与怀旧之美
2000年以后拍摄的澳门电影,基本绕不过去澳门“回归”这一历史性话题。“回归”到底带给澳门人何种情感体验?澳门导演最擅长讲述澳门的“城市记忆”。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澳门回归前社会混乱无序,回归后安定光明,澳门居民理应对未来充满希望,表达积极情绪(如影片《伊莎贝拉》中澳门司警马振成自首的最终选择),然而澳门电影却在不经意间总是流露着某种历史怀旧和惋惜之情,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加强对于澳门历史建筑景观的保护,澳门以历史变迁为背景电影自然选择表征澳门历史的城市景观,如大三巴、岗顶剧院、教堂等,同时澳门的饮食文化也保持了传统特色,因此,建筑怀旧与美食怀旧成为澳门电影怀旧之美的城市美学因素;其二,澳门“回归”后,面对着澳门博彩业的迅猛发展,外资力量的进入,以“拜金”为价值标准的职业导向使得澳门人体味到人情味的淡薄,寻找“初心”、重拾“澳门街”情怀成为澳门人应对社会巨变、安定内心的情感需求,如《骨妹》以中国台湾的人情味对照澳门人情味的流逝;其三,澳门电影往往借助跨国(跨地区)叙述的策略为澳门寻找一个对立镜面,特别是澳门“回归”对土生葡萄牙人而言,引发了“何以为家”的身份焦虑感。
2006年导演陈逸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澳门拍摄的爱情片《濠情岁月》,以岗顶剧院与大三巴为重点拍摄地,表现内地人与澳门人跨越60年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爱情。由于导演对于传统静态美学的偏爱,影片中1945年的澳门城市被塑造成宁静纯美的传统小镇,虽然不乏社会黑暗势力,但这里有爱国正义的澳门记者、有为爱献身的青楼歌女、有坚守爱情诺言的戏班少女。2017年,澳门本土导演徐欣羡执导的《骨妹》无疑在经典情节设置上受到了《濠情岁月》的启发,选择在大炮台座椅背部刻下姐妹二人惺惺相惜的誓言。两部影片都流露出人去楼空的时间伤逝之感,但在历史空间讲述方式上与《濠情岁月》不同。《濠情岁月》影片重点叙述1945年的历史时空,当下时空只是为怀旧而设;《骨妹》则将1999年历史时空与当下时空穿插起来同时叙述,将澳门变迁后人情淡漠的当下现实与历史上曾经的“姐妹情深”对比,从而表达保持“初心”对于当代澳门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
“变”与“不变”是时间在电影美学中制造了的一组张力,而在反映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回归”前后抉择的电影《奥戈》(2009,导演张弛)中,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为澳门另一个家的镜面。表现在城市景观的选择上,导演选择麻将这一最日常家庭娱乐活动、澳门关闸海关、唱着葡国哀伤命运民谣——“法朵”(Fado)的酒吧、八角亭图书馆、亚婆井、大榕树、小街巷、大利来猪扒包、凉茶等表征令人怀旧的“不变”,以李念未能寻到男友马赛、奥戈为寻找生父而错失生母、彼得死后未能带露露去葡萄牙,营造出失根、漂泊、忧郁的澳门城市氛围。尽管电影结尾,奥戈重新认可澳门作为“家”的身份归属,但面对“回归”这群城市漂泊者希望澳门不要改变。因此,美学上“回归”这一历史话题赋于澳门电影以时间的张力与怀旧的美感。
四、父性缺失:女性主导的澳门电影叙事
澳门的城市景觀对于澳门电影风格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柔和秀丽之美。澳门建筑之秀美、色彩之斑斓、线条之柔和、大桥之轻盈、人情之亲和、软性介质如雨水、榕树、海洋等,使得导演在表现澳门的影片中不得不以女性之美为重点表现对象,而作为男性力量最典型代表的澳门父亲形象在澳门电影中是缺失的。
澳门“有母无父”的影视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回归”之前拍摄的澳门电影中,澳门父亲的形象名正言顺地由葡萄牙人担任,如影片《大辫子的诱惑》女主角阿玲的华人父亲不被叙述。“回归”之后,大量葡萄牙父亲离开澳门。如《十月初五的月光》《濠情岁月》《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妈阁是座城》《伊莎贝拉》等电影中都有所体现。男性叙述力量的薄弱,使得澳门电影更偏爱采用女性叙述的视角与口吻,更倾向表现女性坚定的内心与为爱付出所有的情感世界,这在两位内地女导演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与李少红《妈阁是座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尽管《濠情岁月》《十月初五的月光》亦有男性叙述的参与,但影片整体仍以表现女性内心活动最为精彩。
然而,内地导演对于澳门城市美学的认知还相当陌生,优秀的城市电影中一方面应尊重城市空间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指向,透过美学化的电影艺术手法将之呈现,另一方面应尊重城市特有的风土人情、社会阶层、职业特色、价值认同及生活方式,以影音符号建构适合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气质。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姣爷梦中的澳门城市想象或许更符合纽约大都会模式而非澳门的未来,作为赌场公关的姣爷在工作赌场里公开参加博彩娱乐活动同样不合澳门法规,如果说这些只是事实上的失真,那么影片中的价值失真在某种程度上则会伤害城市伦理与人情,塑造并不符合澳门城市的他者形象。为表现姣爷落魄的生存境遇,导演设置了一场房东将住客所有物品从楼上抛弃到街上的炫丽场面。这种绚烂的场景虽然有视觉冲击力,但对于倡导“澳门街”亲情之美的城市既不会存在亦不会认同,相比而言《伊莎贝拉》中对于拖欠房租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在城市情感可接受程度之内。
结语
从城市美学的视角纵观百年澳门电影,一方面我们发现澳门这座城市自身存在的文化张力、空间张力、时间张力与性别张力深刻地规约着澳门的电影类型与风格创造,城市景观在电影中既因为景观自身的柔美特质而具备审美功能,又可以作为中西方文化表征的空间符号,还可以隐喻人物主体的情绪;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城市空间并非现实地理空间的简单再现,而是指涉多种因素的文化建构,来自西方、香港、大陆及澳门本土四大文化背景下的导演将其各自的文化力量植入澳门城市的文化想象中,建构起六种主要的澳门城市形象——跨文化爱情圣地之澳门、情义江湖之澳门、休闲娱乐之澳门、亲情疗养之澳门、“童年不变、怀旧小城”之澳门、坚强女性之澳门,他们的努力也使得澳门城市电影处于不断生长变化之中,而“他者”力量的介入与澳门本土城市美学的规约性之间势必处于长期的角力中。
参考文献:
[1]曹晖. 城市美学论纲[ J ].城市问题,2007(7):21.
[2]涂珍兰. 论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的变迁[ 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4(2):43.
[3]雷冬文. 澳门黑社会问题探析[ 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77.
[4]郑向敏,林美珍,陈传钱. 澳门“赌城”形象分析与旅游形象塑造[ J ].东南学术,2004(5):98.
【作者简介】 张志国,男,山东青岛人,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UCSD)文学系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