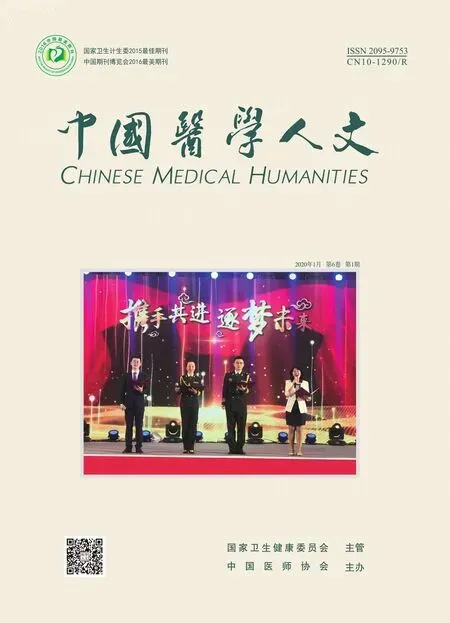2016 赴塞拉利昂光明行日记
文/李 芸
2016 年11 月17 日 长沙 晴
因为明天就要出发赴塞拉利昂,今天终于自己送曦曦上了一回幼儿园。她上中班了,我送的次数屈指可数。开心得不得了的曦曦神气地说:“妈妈你不记得我的教室没关系,跟着我走就好了。”晚餐桌上,曦曦说:妈妈这个咸蛋黄好好吃,给你一半;洗漱完,曦曦说:妈妈你今天陪我睡,不要再等我睡着以后偷偷地溜走啦;(我经常等她睡着后离开去做自己的事)
迷迷糊糊中,曦曦说:妈妈,你明天一路顺风……
妈妈最亏欠的就是你们姐妹俩和外公外婆,这次一去这么多天,外婆又要辛苦啦。


2016 年11 月18 日 长沙
晴破阵子·赴塞
李芸
剪我长发及腰,
别我倚门阿娇,
接得光明旗猎猎,
何辞征战路迢迢,
并肩有同袍;
狮子山中贫弱,
兼困视界昏渺。
惟愿竭力驱翳障,
柳叶刀作我戈矛,
善举架心桥。
注:塞拉利昂又名狮子山共和国


2016 年11 月19 日 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 晴
我们在凌晨五点多抵达巴黎。队员们都面有疲色,又兴奋不已。宽敞明亮的候机厅、琳琅满目的名品店,都不如一个小细节让队员们感到兴奋——戴高乐机场所有的标识牌都由法、英、中文标注组成,广播里不时传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家纷纷感叹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提升可见一斑。
是啊,越出国才越知爱国。2008 年8 月8 日,我 在澳大利亚,当北京奥运会上的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难忘正在收拾、泡脚的室友们丢下手里的事情,站在脚盆里齐声跟着高唱国歌,直到个个泪盈于睫的场景;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在纽约,尤记相约potluckparty 守着收看赛事,得到金牌后爆发的掌声与欢呼;更不必说上次赴塞拉利昂,亲眼见到塞国首都弗里敦最高的政府大楼、最平坦的主要道路、技术最好的医院、条件最好的宾馆,都是“中国制造”的自豪感,还有当地黑人民众对“中国医疗队”标志所自然流露出的尊敬、感恩之情,都会让人深深地觉得,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做一个中国人,真好!
2016 年11 月20 日 弗里敦 晴
长沙-广州-巴黎-弗里敦,三十八小时征路漫漫,三万一千里尘满衣裳。终于在夜色沉沉中我们抵达弗里敦,见到了等候已久的驻塞医疗队员。光明行和驻塞医疗队队员们握手、拥抱,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从机场坐车—坐海轮颠簸40 多分钟,再坐车我们才算到了驻地。抵达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互喷防蚊水,然后是集体吃蓝色小药丸——防疟疾药。在餐桌上,大家本已累得没有任何食欲,但在异国与故友重逢的喜悦却又让我们兴奋不已,谈工作、聊生活,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由于时差,第二天不到七点,几乎所有的组员都醒来了。大家简单的吃了点早餐,在弗里敦的灿烂晨光里开始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昨天晚上了解的一些情况,开始调整原先的手术预案、应急预案和职责分工,我“惊喜的”发现,战友们都是一群工作起来较真程度不亚于我这个处女座的完美主义者。尽管累,但我想说,我爱你们所有人!



2016 年11 月23 日 弗里敦 晴
罗马原来是可以一天建成的!药械被塞国海关耽搁了三天,为了不耽误手术,除显微镜和超乳仪外的所有设备仪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所有的药械都是我们自己拆箱清点,每一个人都既当搬运工又当工程师,既当医生护士又当库房工人,大家在塞拉30 多度高温下挥汗如雨,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忘记了无处不在的传染病的威胁,配合默契,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物资清点、仪器装配完成,新开了一个22张床位的眼科病房和同时开展2 台内眼手术的规范手术室,还完成了对首批病人的术前检查工作。这个效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比自豪!为我们自己点赞!

2016 年11 月24 日 弗里敦Jui 镇 晴
手术第一天,我们完成了预期的五台局麻一台全麻。六台白内障在国内是多么小儿科的数字,可在这里,每一步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在我们进行第一个全麻手术病人的时候,手术室就突然停电了。我的心一沉,既担心烧掉手术显微镜的灯泡,又怕手术出现意外。我们不得不动用所有人的智能手机光源来勉强继续手术,直到来电。万幸的是所有病人都非常顺利的完成,跟着我们学习的塞国眼科医生看过我们的手术后,也激动不已地为我们点赞!
医疗队的兄弟姐妹们也给予了光明行最大的支持。大家都是忙完自己的事情后又过来帮我们张罗,正如此次光明行的口号“We fight for sight together”,为了塞国人民的光明,我们携手并肩,砥砺前行!
2016 年11 月29 日 弗里敦 晴
昨天,16台手术的空隙中我换了衣服准备去吃饭,协助我安排手术病人的黑人护士Favor拦住我,小声地告诉我,有一个77 岁的艾滋病人白内障已经相当重,行走困难,但是去了好几个当地医院,别人都不愿意给他做,他摸索着生活了几年,前段时间听说中国来了白内障手术医生,就满怀希望地赶过来了,Favor问我们还给他做不做?我不加思索的说:“当然做!放最后一台。”这是出于器械消毒要求的考虑,以免威胁其他病人的健康。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了老人,向老人说明了他的手术可能要晚一些。当天下午,老人由护士搀扶着走进了手术室,他一直念念有词:“God bless you,God bless China”
除了艾滋病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外,他的手术本身难度也很大,四级以上的硬核,眼部解剖条件也并不太好。我想了想,对所有队友说:“这一台手术我一个人慢慢做,你们都不要上台。”带上两层手套,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向躺在无菌巾单下的老人。老人也很紧张,整个手术床都随着他的颤抖而晃动。加上老人既不懂英语,也听不懂克里奥语,我只能用左手掌根部固定他的额头,每一步都很小心,当人工晶体完美的植入清澈透亮的囊袋内的时候,我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发现手术衣下的洗手衣再一次全湿透了。在换下衣服的时候,队友忍不住关心地责备我说:“又是艾滋病年纪又那么大了,手术还这么难,何必冒这个险呢!”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在一次暴风雨过后的海滩,许多小水洼里都有小鱼被困住搁浅了。一个小男孩努力的将一条一条小鱼从水洼里捞出来用力扔回大海。旁观的人忍不住劝他:“孩子,这些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小男孩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扔呢?有谁在乎呢?”小男孩说:“这条小鱼在乎!”他捡起一条扔回大海,“这条也在乎,还有这条!这条!”我想,我做这件事的理由,就跟这个小男孩一样吧。医生不是救世主,但我可以竭尽我之所能,让每一条小鱼,都游回光明的大海。

2016 年11 月30 日 弗里敦 雷阵雨
也许是因为思念我的孩子们,也许是因为自己就是从事小儿视网膜病的缘故,我一直对这里所有孩子有种自然而然的喜爱。非洲的宝宝们眼睛特别大特别黑,头发卷卷的像洋娃娃,可爱极了!不过你要试着抱抱,那叫一个沉!我第一次差点把那个孩子没抱住。
塞拉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可爱,可他们面对的,是比我们的孩子严酷得多的、充满未知的命运。在使馆的一次宴请中,我遇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塞的总干事,交谈中得知,塞拉的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连续多年居世界前5,尽管在全世界的援助下这个数字逐年下降,但2015 年仍然高于中国10 倍多。我们也听到好几次,黑人护士或工人告诉我们谁家的孩子死了,当我们很震惊的问原因时,他们会以让我们更为震惊的平静语气说:“饿死的”。塞拉全国平均22% 左右的儿童为低体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即使是给高官开车的司机、卫队,家里也很难保证一天三餐,那里的大人孩子们对食物都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渴望。所以后来,我们的队员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早餐时偷偷藏起一个鸡蛋或一点点心,带去给护士或工人、司机、病人,此时他们眼睛里闪烁的光芒,令我终生难忘。我想,回国后我会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告诉我的孩子们,让她们知道,在远隔万里的世界那一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多少同龄孩子想象不到的幸福天堂。

2016 年12 月2 日 弗里敦 晴
今天又停了两次电,但依然完成了26 台手术。脱下手术衣,里面的洗手衣早已经完全湿透。在这里,一天下来出汗都会减掉一两斤体重,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地忙碌着。一身臭汗回到驻地想洗个澡,常会碰到龙头水作前列腺肥大状滴淋,我脸上、脖子上都长出了汗疹,魏欣姐更惨,长了一身的痱子。
时近旱季,停水几乎难以避免。按手术应急预案每天我们要备一桶水以免无法洗手,可是看看那过滤三遍后仍如泥浆的龙头水,碰到停水我们也只有不脱手套、连续免洗消毒液上台一个办法,手都被自己的汗水沤得皱巴巴了。
快回去了,自己的衣服全懒得洗,但只要有水,每天无比勤勉的洗自己的洗手衣(整个医院只有一个洗衣工,会把病人布单和医生的衣服一起洗),西非阳光虽美,也不能室外晒衣服,因为怕芒果蝇蛆病,好在空调够劲,一般洗手衣过夜就能干。
疯狂的想吃米粉,想吃剁辣椒。

2016年12月6日
昨天的总结会非常成功,晚上的飞机,累散架了的队员们终于可以睡上来这里后的第一个懒觉。我也想多睡一会,却仍然在早上4 点半准时醒来。看着窗外沉睡的大西洋,心中感慨万千却无从说起。在塞拉的日子,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和悲悯感。这里的人,太需要帮助了!而我们能做的,又太少太少。两次赴塞,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不愉快,有的朋友因此义愤、失望,可是,我常常不由自主的从他们的身上,恍惚看到百余年前外国人眼中,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的影子。一场十一年的内战,让西非小巴黎变成了今天仍满目疮痍的塞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今天我们所处的太平盛世呢?
塞拉,再见!也许很快再见,也许再也不见,但当我老了,回首人生,这段回忆一定静静躺在我的心底。下面这几张是此次光明行我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不是和部长、大使、高官们的合影,虽然那里面我显得很神气;不是在手术台上的特写,虽然那时的我也许最有魅力。最后,借朋友的赠诗,以自勉:
送给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光明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把那些陷入黑暗的、饱经风霜的人们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手术室门口,高举光明的灯火。
——赠 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