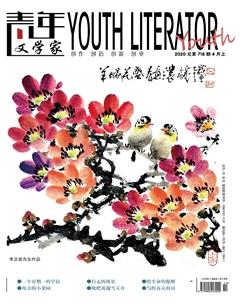草心、木心及农具
张裕亮
转眼又到四季扎口处。砸出去的锤子停下来,一年中哈出的热气,就要在大寒节气里,全部变成雪花落下来。
年初放飞的各种祈愿、祝福,大多成为司空见惯的各种安分守己的小动物,老老实实趴在被人遗忘的暗处,蛰伏;少部分的已彻底走远,即使把我们累虚脱了,也不再可能唤回来。
怀念我们的热血青春,那些淹没在深处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光的锤子。那光溜溜的锤把,每一寸河山都是粗粝的茧子和汗珠子硬杠出来的。
有的锤子等到了它的贵人,在某一天被幸运拎出,等来出人头地的一击和千万次中流击水、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奋击;有的锤子终身埋没于荒野,破败、衰落,就此沉沦下去,像大多数乡间野草,从没遇到被征召的机遇,永生不能成为“应梦贤臣”或“朕的王妃”,只好麻雀一样在村子里一代代“蜗居”。
农业高度机械化的当代村庄,“留守农民”几乎成为一种装饰节日喜庆用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而平时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多少活可做,闲下来的乡亲们干脆把自己挂成东、西厢房或某个偏房里的农具。如果不是偶尔遇到他们赶赶小闲集的身影、听闻搓搓小麻将时山呼海啸的巨大喧哗和哗啦哗啦的撞击声,你都感觉他们好像多年就不在世上存在似的。
这是乡村最闲适、惬意的应有味道,没什么不好。桃花灼灼,浣纱浣溪,坊间精彩,请将继续。
劳累一生的老人们得享余生,像被割下来的草,平静面对锈迹斑斑的时光镰刀,彼此忘掉仇恨、仇视,忘掉所有的悲苦,超然于尘世之外,笑看死死生生,像隐士,这是岁月老人送给村庄最和美的格局和大写意。再没有比生活富足、时光静美更畅快的日子了。何不就这样延续下去?
我们都蜗居到高天里去,把更多的草木留给新空置出来的原野圣域。我们亏欠皇天厚土地的,就都还回去。
感谢时间的化解与融合,感谢时光分解了那么多被卑微者深恶痛绝的。像沤过的土杂肥撒进岁月的田野,村庄里飘荡着些微腐殖质发酵后,草木泥土混合的气息,它们飘散又聚拢,又在飘散中一点点把味道淡下去,这就是我的故乡了。
或许厚厚积雪的草屋子上,还会漂浮起一些水雾之气,袅袅婷婷的,如安谧之诗,这是我更具细腻质感的故乡了。每一处都有值得我深深感恩的亲情浇筑于这片莽苍大地。
枯草里的故乡、粗犷的风,有着让我丢魂失魄的狂野。我并不讨厌它们曾经一次次揪扯过我穷困少年的耳朵,不怕冷鲜鲜的风牦牛一样,一年年把我吹彻。
冻凉了的肚皮,蹦跳一会就滚烫烫,这有什么好怕的呢?蹦着跳着,甚至我们都未来得及记清父母那些年身强体壮的样子,乡村的孩子就已长大了!
树杈上的故乡,弹奏着木风琴。木琴声在乡村各处呜呜、幽幽响起,整个村庄都在琴声里微微颤动。
每当这些个意境星空一般呈现,那木的心就月光下的流水般,亮了,亮了,亮在我伊甸园呓语的梦乡。
一些瓦片,趁着月光的细柔雨丝,把月华的水缓缓流淌下来,哪怕你不是一个正常人,也会看到月光里的村庄有着迷人的清亮光泽。
每一棵草木都是一首诗,露珠是它们更瘦小的孩子。你锦帽貂裘打这儿路过,它们泪眼湿湿,却不一定为你。
草的心,木的心,在时光细细碎碎中荣荣枯枯,谁在草木间低头抚琴,谁的歌声被河流搬运走,哺遥远大地上嗷嗷待哺的草木婴儿。
月亮回到西厢房,晃一晃,就缩回屋里去了。这馋嘴的老家伙,又凑着红泥小火炉,取暖、温酒了。酒醇氤氲,像古风,灌满整个屋子,呼噜声在暖烘烘的炉火影子里布幔一样缭绕、摇曳。离愁别恨都没有。都被岁月给洗去。“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内心的空明让安静的村庄都感觉澄澈无比。
云也不来。热闹过后的天空逐渐散场。猪啊猫爪啊,鸡鸣狗吠都潜伏在暗处,仿佛被土层深埋。静,保持了村间万物应有的尊严和尊严里的温婉平衡。微山湖畔的这些个冬日村庄,像听进了神的话语,被招安,被慰抚,这群神的小宠物。
芦花在暗夜收敛起它惯有的忧虑和光芒,成为村庄的雅士。
草木的本性,回归到质朴无华的息壤内部去。那“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是鄉村最妩媚部分,是带着唱腔吟哦的《青玉案》那让人脸红心跳的挠心曲儿。
所有的光阴、光影,都在凡夫俗子的身体内沉浸;仿佛筑巢,我们在古老的土坯房墙体内,熬尽汗珠泪水,最后再耗干我们自己。
大地无声,在冬夜,成为我怀念故乡中的最美物语。乡间的素胎,在怀揣美好希望中,安然而睡。
大寒过后就是春天了。一些种子举着芽,举着生命的空灵,呼之欲出。
一些叶子,不系的古老舟子,并不曾真正远离,而是换了一身贴身的道衣在冬眠,像虫卵或蛹蝉,牛羊扭一扭腰身,又枕着麦苗青葱之气呼呼睡去。当年放牧的孩子都去了哪里?那留在原地的,也越来越不再能聚齐。余下的空缺,都是晚风的——不是一缕一缕,而是一滴又一滴……
夜色阑珊的味,更见浓郁,唐诗的银勺子也研磨不开;换宋词的竹筷子上来,更不行,长句短调、参差不齐,容易崴脚、闪腰,弄得失眠者,扶着柴门也不敢站起来。
在这一刻,百丈的冰入河,带着辽阔的刃。而铁马,为带刀护卫。河流被填进骨头,村庄重新恢复它久违的硬度和韧性。
经常在旷野独行,我坦承,是河流惯坏了风;是谁,用汹涌澎湃的真情,宠坏了你。
那么多被生活宠爱成了诗的祖先们,在幸福中被熬成了汤,成为美好传说和过往,他们是幸福的,现在未尝不是,何必在意时间是寸短,还是恒远。
站在大地上,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美成神话。进不了神话的,拐弯就进民谚、民谣的洞窟吧。草的心、木的心,星星般一闪一闪,我这个老农具的莽苍,又扩大一寸。
但愿荒芜不再占据无知思想的空地,我想让你对我的每一次凝望,都化作浩瀚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