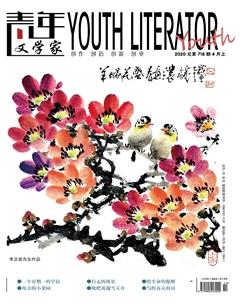从黄桷垭出发的人
吴景娅

从前,山下到黄桷垭,只能去爬黄葛古道,一爬小半天。那古道真古,始于唐,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那古道旁植有黄葛树,大大小小,各荫一方天地,一棵隐匿在另一棵的身后,随古道婉约、长高,绿意通天,伸入无限的迷离;那石板路上的石板也都是几百岁高龄的老家伙了。人们把它们重重叠叠彼此镶嵌,一块垫着另一块的背脊骨,它们也毫无怨怼,老老实实地顺了自己的命,任千万脚千万次地踩在它们的身体上,踩出泛着青色的光溜溜的肌肤。
有些石板上也留有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以想见擅长爬山的川地马登这样陡峭的坡地也是不易,要使出拼命的劲来。于是一路烙下的这些马蹄印,个个皆辛苦,犹如一枚枚的勋章,在一路颁发。
三毛说,她沒想到的是父亲会采用骑马这种交通方式,去山里的律所上班……会不会也包括了去山下美丰银行大楼上班的时候?当律师的父亲是那样文弱。
这个在我听来也像是个神话。骑马上山还容易。下山,那些几百岁的青石板多少长了些苔癣。如果再遇上雨霖霖,泥泞处,会不会马失前蹄?还有,当年接近海棠渡那一帶是马尾松林遮天蔽日。大暑天走着,也有森森阴冷气偷袭背脊。如果是雾气沉沉的冬季呢,重庆冬季总比夏季长啊!
父亲即使顺畅地下了山,他的马会栓在海棠渡的哪里?坐船过江爬上陡峭的石梯坎后,从望龙门到打铜街,他是徒步还是坐车?在美丰大楼这座当时重庆最高最时髦的标志性大楼里,父亲又是在怎么个废寝忘食地仔细做事?
三毛好想知道这一切。她总觉得父亲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像一堆刚刚燃尽的炭火,尚有余温。但,能清楚告诉她的人好像已沒有了。短促的几十年却是朝花夕拾,变了人间。
她说,儿时,睡在黄桷垭的老院子里,总听得到那匹马嗒嗒走路时的声响,它们的轻与重,让她一下便能判断出父亲离得有多远;是已在九宫庙的老黄葛树下歇脚,还是迈入了他们缪家院子的后门。踢嗒声近了,便是她的节日;远了,她的小胸膛里便装满忧伤。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以马代步在山上山下奔波求生的还不只有三毛的父亲,大画家傅抱石也算一个。傅氏当时住在歌乐山,要下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来讲课,坐不起轿子时,也会选择骑马而行。那个年代像三毛父亲陈嗣庆这样的中国精英男士,哪怕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也活得很不容易。左肩总想以一己之长来报忠国家,右肩还得担负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危和柴米油盐……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累的那一拨男人。
差不多快三十年前,我和三毛坐在重庆饭店,频频隔窗去眺望对街的那幢当年的美丰银行大楼,以此来向一位辛苦又伟大的父亲致敬!
这是我和三毛的第一次见面,在重庆寒色渐现的深秋。我坐在三毛身边,就像坐在自己的梦里面,见着一个穿花布裙的女子影影绰绰从撒哈拉沙漠、西班牙的橄榄树林、秘鲁的马丘比马古城走过来,叹着气,千山万水的。
怎么可能呢,这个照亮过我生命的女子,竟与我咫尺之隔?!
她人很疲惫了,不停地咳嗽。身体的衰弱仿佛在拖累她的灵魂。好在,她的声音实在年轻,让人不敢相信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清亮,温暖,迷人。那是第一时间里会激发你去接近并呵护它主人的声音。
我们的话题从一对耳环谈起。
那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很“三毛”, 浑身叮叮当当,戴了红红绿绿夸张的藏式耳环和首饰。其实,这已是我多年的着装风格了,带着对都市精致规范的不屑,仿佛随时都会叮叮当当踏上陌生之旅去流浪。
而“流浪的教母”正与我面对面,她比我想象的瘦小、虚弱……哪里寻得到她狂放不羁的焰火?她喜欢低头,长发顺耳流泄而下,脸颊更显清癯,皱纹在那里不动声色。她问:你的耳环在哪里买了?夸张得好……
女人通向女人原来就这么简单!
我们汪洋恣肆地聊她那些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半毛钱的“宝贝”——从美浓乡下淘到的一把油纸伞,到雕刻着福字的老铜戒指……她说,有些东西跟着你的年代一久,便成了家人。家人哪里能去论贵贱,也不能随便就丢下吧。
我小心翼翼地与她绕到了男人这个话题——
我们绕过了荷西……我不忍心,她实在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强悍潇洒、百毒不惧的三毛。
我们谈那些无关痛痒的男人们,过一把指点江山的瘾。
三毛对内地男人有种文化和地域的陌生感,他们让她好奇、新鲜又困惑。
她语调婉转地说,觉不觉得中国现代的男人好像缺少点旧式男人的儒雅气和谦和?我极其赞同:“还是该让他们穿长衫子。让他们粗野的时候多少沒这么利索。”她被我的话弄笑了,眼里突然炯炯有神。“台湾偶尔也会见到穿长衫子的男子。只是在一种场合,带着礼服性的色彩。但好像都不对呀。好像穿长衫子的男子就只能呆在那样的时空里。走过了,就不是那回事了……”她真是明察秋毫。但,似乎再尖锐的问题经她柔声细语地说出来,就不那么锋芒毕露了,她的声音自带了一种敦厚和宽容。
谈王洛宾时也是风轻云淡。她很坦率地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王洛宾是能够撬动她隐秘激情的人——这不仅是因他曾为了理想圣徒般地在荒凉的西部流浪,也不仅是因他创作出那么多堪称不朽的经典歌曲,更是因他的苦难!对,他的苦难像万箭齐发的光束,逼得她背过身去。只是她沒想到那个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的人竟还活着。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更想代表命运对这个度尽劫难的人加以补偿……
川端康成曾说,青年人有爱情,老年人有死亡。恰好站在中年门坎上的三毛,真想攥住自己与王洛宾的头发,升腾,摆脱时间的万丈深渊……
三毛把王洛宾当作了自己的精神伴侣,世俗中的在不在一起已不重要。
爱情一直是三毛很重要的人生课程。在这个课程中,她既是学生,又是老师;她既会看见树,更会看见森林。她理解的爱情也与常人不同,有种宗教意义上的广阔,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小女人,计较着一亩一地的得失。
三毛说自己其实是不擅交际的人,所以有时会造成一些读者对她的误会。
我知道,三毛有她的另一个世界,那是她为自己独留的桃花源。我们这些“武陵人”自以为早已闯入过了,其实,即便作了多少记号,也不会再找到入口了……谁又能真正懂三毛?尤其是夜深人静时的三毛,谁会深味她的辗转反侧?
我问她这次去不去黄桷垭看看,那个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呆到四五岁,才随父母去南京,而后又去的台湾,算起来已四十三、四年了。
三毛沒有回答我,感觉得到她的踟蹰。她在纠结什么呢?少小离家,就怕老大还?她害怕了那沉甸甸的四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黄桷垭在她记忆中丝毫沒有衰老过,她总是把它和那个野里野气的自己一起记录在案了。她还记得自己只管瞎胡闹,“嗵”地一声却掉进了地下埋着的大水缸里,大人把她捞起来,脸都吓白了,她還嘴里边往外吐水边幽默地说:感谢上帝。黄桷垭背街的山上坟堆林立。大人在吓唬:别去哦,别让里边躺着的人逮住哦!她却不信邪,偏爱在那些坟堆与坟堆之间爬来爬去。天黑了,大人喊了又喊,她仍在那里晃荡。
她问我,重庆现在还有那种小黄花吗?一到四五月份,野外到处都是的那种小黄花?我说还有还有,仲春便漫山遍野都是,一直开到夏天的尾巴。我们也叫它小黄花。还查过,说不清学名该叫“抱茎苦荬草”还是“串叶松香草”……“小时候我很喜欢和姐姐一道用妈妈的空药瓶子盛满井水,养一大篷小黄花在房子里。它也有香气,带着药苦味的那种。”
该告别了。
我把那对色彩扎眼的藏式耳环送给了三毛。她摊在一支手的掌心间,用另一支手去拨弄,欢喜雀跃地说:给我了吗?我要带着它回台湾,还有好多地方……
那一刻我相信了三毛的喜悦。我以为那样喜悦着的三毛就是她该有的样子和永远的样子。所以我起身告别的姿势无比轻盈,仿若我们第二天又会再见面——
我边向门边退去,边摇动手:三毛再见!
她如梦初醒:啊,这就走了……
一直记得她仿佛被什么蜇了一下的眼神,倏忽便黯然。她是个怕告别的人。
我步履轻快地下楼,以为后会有期。却沒想到一面永恒……
两个多月后,传来三毛走了的消息——这么多年了,我都是用这个中国字来表述一个事实。曾为三毛留下若干经典瞬间的人像摄影大师肖全也同样,在我们谈及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刻时,他双手向天开启,说,三毛是飞了……我们都不愿接受她的自我了断,那成了我们人悬崖下沧海中的旋涡……
1992年深秋,我在敦煌的鸣沙山到处找三毛的衣冠冢。沙海浩渺,人如蝼蚁,哪里找得到?!
风才不管。它仿佛是从月牙泉那些长势喜人的芦苇丛之间一路吹拂过来,让人神清气爽,恍惚作了春风。想起三毛为电影《滚滚红尘》写的那句歌词: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独怆然而涕下。
去年十月,我见到了三毛的大姐陈田心、弟弟陈杰以及弟媳、侄女,还有其闺蜜——画家薛幼春……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像家人一样地聊天。他们为我构建了另一个立体可触的三毛世界,让我得以更深邃地继续阅读三毛。至少,她不再是我幻觉中那个孤孤单单漂泊在尘世间的女子,只是靠喝着浪漫和不羁的西北风而存在。她也是人家的妹妹、姐姐、小姑子、姨和叽叽喳喳说悄悄话的闺蜜。
这一家子个个温文尔雅、谈吐不凡,配得上做三毛的家人。尤其是近八旬的大姐陈田心,穿一身玉白色的蕾丝旗袍,斜戴一顶浅驼色的薄呢贝雷帽,两耳缀着红珊瑚的耳环,与红珊瑚的花朵胸饰遥相呼应……她说话,柔声细气;微笑,抹着珊瑚红的嘴唇便成优美的弧型……感谢她,让我能揣想三毛老去的模样……
薛幼春女士穿着当年三毛送给她的布长袍,白底蓝花,扎染的那种,头上系着同色系的发布。我小心翼翼和她谈及心里的结——三毛为什么要放弃?她握住我的手,语气坚定:三毛从沒放弃!她身体的痛苦非一般人能去想象和承受。她不愿它再拖垮自己的灵魂……
我沉入自己的海洋,四周游动着海参——女诗人辛波斯卡说:它舍弃一半自我,留给饥饿的世界,带着另一半逃逸。它暴烈地将自己分成死亡与拯救,惩罚与奖赏,曾经与未来……女诗人这样写着海参面临危险时的“自断”。它把自己分成了肉体和诗歌,“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