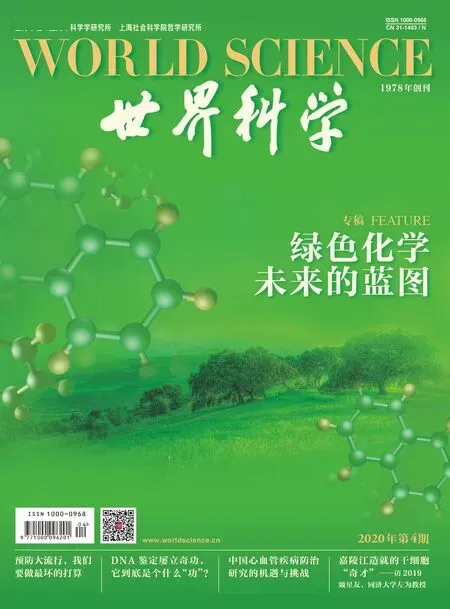这不是他面对的第一种传染病
——安东尼•福奇医生坚持以事实为本
编译 高斯寒
政客在笨拙地摸索,卫生部门的其他官员避之不及,福奇医生却勇敢地站出来解释疾病。

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面对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发言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医生是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顶尖专家,广受尊重,那是因为他能向受众清楚地解释科学,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资讯——而在近期,他受人尊敬是因为他设法纠正总统特朗普的声明,又没有明说他是错误的。
特朗普总统说,制药公司“不久后”会准备好冠状病毒疫苗。在总统发布声明之后,福奇医生多次在电视简报会时走上讲台,或者在白宫圆桌旁发言,修正疫苗出现的时间表,给出更准确的估计值(至少1年到1年半)。
特朗普说,“解药”有可能出现。福奇医生解释说,目前在研究多个抗病毒药物,看它们是否减轻病情。总统还说,疫病会在春季消失。福奇医生说,也许是那样,但因为这种疫病是由一种新病毒引起的,现在还无从判断。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唐娜·沙拉拉(Donna E. Shalala)说,在传染病大流行时,面向社会大众讲话的人应该是福奇医生这样的专家。沙拉拉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美国卫生部长,曾是安东尼·福奇的顶头上司。
“我认为安东尼扮演着与过去一模一样的角色——确保科学的准确无误、清晰明了。”沙拉拉女士说,“在卫生紧急事件中,对美国公众来说,可靠的人是科学家与医生,而非政客。”
“我过去让安东尼在面向公众发言时穿白大褂,”她补充说,“我让他们全都穿白大褂,那样民众会放心,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医生。”
周日时,福奇医生上了至少两档电视新闻节目,警告大家,随着病毒的传播——当时在至少33个国家内有450多个病例——也许要考虑采取一些更严格的措施来隔离感染者。他也向长者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士提出建议,他们面临的风险最大,应当避免邮轮旅行、乘坐飞机和人群聚集。
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一位众议员询问福奇医生是否有个双胞胎兄弟,因为近来似乎在哪儿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另一位众议员提供了医学建议:将柠檬、蜂蜜和波旁酒调成饮料,对他的嗓子有好处。因为面对立法者、科学家、卫生官员和记者的各种讲话无休无止,福奇医生的嗓子已经嘶哑了数周。
假如说福奇医生已经变成冠状病毒传染病的首席解释人,部分是因为政府内的其他科学家留下了真空地带、回避新闻媒体的聚光灯,或是被特朗普政府控制得死死的,被指控说夸大了病毒的威胁。而当记者打电话给福奇医生时,他会给记者们回电。
美国疾控中心(CDC)目前正面临尖锐的批评,因为它迟迟拖延,未能给美国各州提供病毒检验试剂盒,也因为它对于在亚特兰大CDC总部进行的检验设下严格的限制,导致一些病例的诊断遭到拖延或忽视,有可能让被感染的人传播病毒给其他人。79岁的安东尼·福奇医生看起来不是抨击的焦点。尽管他最近被告知必须要通过白宫获得授权,再去接受众多的电视、广播及报刊采访,但他说自己并未被封口。
“你不会想与总统开战。”福奇医生告诉《政治家》杂志。但他认为,公众需要确切可靠、易于理解的医学资讯,尤其是在危机之时。他更为重视不要试图用知识去向受众“进行夸张的宣传”,他在2015年时的一次采访中这么说道,并补充说他在耶稣会高中与大学接受的教育使他懂得缜密思维和公共服务的价值。福奇医生从1984年起就担任了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历经六任总统,多次回绝了请他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邀约。他领导美国联邦政府抗击新兴病毒引发的疾病,包括对抗艾滋病、SARS、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和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他是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缔造者,该计划由乔治·布什总统于2003年启动,旨在引领全球对抗艾滋病毒。
2001年,在恐怖分子将炭疽杆菌邮寄给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后,小布什政府最初试图对炭疽的威胁轻描淡写,然而福奇医生的人格特质就是直言不讳。“这是一种相当难对付的东西,吸入炭疽会感染人,不用直接接触就能感染。”他说,“就它的等级和规模而言,无论是武器化还是非武器化,你想怎么称呼它都行。事实是,它的行为就像一种高效的生物恐怖战剂。”
过去的传染病暴发已经让他一直警惕新兴病原体。在1月时,中国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案例报告在他的头脑中拉响了警报。
“甚至早在我们知道那是冠状病毒之前,我就说了,这听上去像是冠状病毒-SARS类型的传染病。”他说,“一等病毒类型得到确认,我就召开了高层会议,说‘咱们立刻开始研究疫苗吧’。”
福奇医生能归入最高薪水的联邦雇员之列,一年所得大约为40万美元,超过美国副总统或者首席大法官。在2020财年,他监管总计58.9亿美元的预算。特朗普政府提出削减7.69亿美元预算,但遭到国会拒绝。
也许福奇医生看起来镇定从容,但新型冠状病毒让他担忧不已,尤其是病毒在西雅图地区的传播以及它在当地一家疗养院造成的死亡人数。他说,他认为仍然有可能阻止这种疾病,但卫生部门得要知道该在哪儿采取遏制措施,而检验能力的不足是个巨大障碍。
由CDC发给各州的检验盒有缺陷,替换那些检验盒已经耗费数星期的时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出的严格规章阻碍了外部实验室独立进行检验的努力。
但福奇医生拒绝加入谴责CDC的批评者队伍。“放马后炮很容易,”他说,“联邦政府的每一分子都在全速工作,努力摆脱困局,好好做事。”
“我真正想要集中精力做的工作是进行充分的检验,打好循证医学的基础,那样才能知道我们国家的疫情处在什么水平。”他说,“西雅图的情况让人担心。我们需要了解社区传播的程度。”
弗里登医生说,福奇医生过去对他经手的、有待开花结果的项目满怀热情,间或也许有过度承诺的现象——譬如对于艾滋病疫苗和通用型流感疫苗的许诺。通用型流感疫苗会针对多种流感病毒株提供长期免疫,那么民众就不需要每年注射一次流感疫苗。
“你得要扮演这种永远乐观的科研者角色,认为解药即将出现,唾手可得,这样才能从国会山弄到钱。”弗里登医生说,“在向国会要钱方面,他非常有本事。”
弗里登医生补充说,福奇医生也是一位持平公正的同事。在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时,两名护士照料一名赴美旅行的病患而感染埃博拉后,CDC遭到严厉的批评,被指责未能帮助医院更好地应对埃博拉。但福奇医生那时没有推波助澜。
“并非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完美无缺,”弗里登说道,他那时是CDC的领导者,“许多处在和安东尼相似职位的人也许就利用那个机会,为他们所在的机构谋取利益,而安东尼总是高风亮节的。”
“假如我们做错事,他会坦率地说出来。”他继续说,“当我们受到不公正的抨击时,他为我们辩护。在华盛顿有时能看见各种官僚主义的状况,而他的行为常不同寻常。我认为那就是安东尼如此受人尊敬的原因。”
在艾滋病流行的初期,美国政府以及卫生机构常常受到批评和抗议,被指责在寻找潜在疗法方面不作为,给予科研及医疗的拨款不足。
1988年时,当艾滋病患者维权人士在研究所外示威,要求获得试用试验性药物的机会时,福奇医生的做法让活动带头人大吃一惊——他邀请他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他最终与维权人士合作,制定新的方法来扩大药物获取,又不会危害临床试验(当时急需临床试验来确定药物是否奏效)——这个方法后来被应用于其他疾病的药物研究。
“世上有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但安东尼有着一套特别的技艺,”沙拉拉女士说,“沟通的能力、正直诚实的人格,以及对政治世界的理解——他懂得为了保护科学家要待在政治圈之外。”
福奇医生承认,他的年龄使他处于最高风险的群体中,极易因为冠状病毒感染而病重。这并未让他放慢步子。他一晚上仅仅睡5个小时左右,醒着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他乘坐地铁到华盛顿都会区的各个地方,包括他的办公室、国会大厦和白宫。大多数日子里,他会跑步或快步行走3.5英里。
“我不为自己担心,”他说,“我担心的是我不得不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