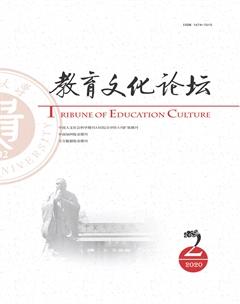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及其对当下教师的启发
李宜江 张李
摘 要:“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是孔子哲学方法的核心,自孔子提出之后,曾子受孔子耳濡目染影响以“忠恕”为“一”诠释“一以贯之”,孟子身处动荡不安社会以“仁义和仁政”为“一”发展“一以贯之”,荀子在百家争鸣、天下归于一统中用“以一持万”丰富“一以贯之”。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启发当下教师:应牢固树立教书育人为“一”的使命,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精神贯之,应掌握“以一持万”的方法育人。
关键词:先秦儒家;一以贯之;忠恕;仁义和仁政;以一持万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2-0010-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2.002
Abstract:Th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of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is the core of Confucius philosophical method, since Confucius put forward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Zengzi, influenced by Confucius constantly, put forward “loyalty and forbearance”as “one”to interpret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Mencius, who lived in the turbulent society, with his thought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t governance”as “one”, further developed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Xunzi, in the era of contention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with his application of “grasp the key point”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The methodology thought of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in Confucianism in Pre-qin Era enlightens teachers at present in the perspectives of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miss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s “one”; teaching should be run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tireless learning and teaching;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should abide by the method of “grasp the key point”.
Key words:Pre-Qin Confucianism; 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loyalty and forbearance; 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t governance; grasp the key point
“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是孔子哲学方法之核心,贯穿于儒家哲学体系之中。“所谓一以贯之是指在学说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理念”[1]54,指的是在思维上注重整体、联系与连续。“一以贯之”主要从“一”和“贯”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指的是事物的主要原理和中心思想,随着时代与人物的变迁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贯”存在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横向,即在整个思维体系中贯穿的理念;二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去理解,即理念存在时间的长短。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在曾子的继承中得以明晰,随着思孟学派以及荀子的传承与发展得以完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是儒家思想中的灵魂,只有掌握这动态因素,思想本身方能够寓开来以既往。”[2]11
本文仅就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及其对当下教师的启发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提出“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
春秋时期,“一以貫之”的方法论思想在儒家阐释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在《论语》中,孔子先后两次对他的弟子提及“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孔子问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认为是。孔子回答:“非也。予一以贯之。”[1]296孔子认为他的学问不是广博的知识简单堆积而形成的,而是由他学问中贯穿着一切的“一”联系着所有知识。孔子告诉曾参“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强调自己的思想贯穿着一个基本理念,不希望别人理解他的学说只限于博学之见,希望他人在理解其学说时主要把握“一”的思想内涵。难怪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1]106在孔子看来,知识都是一脉相承的,有着系统的理念贯穿于其中,不会出现不懂学问而造作,故意显得博学的情况,他重视的是“一以贯之”的理念而造就的智慧。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进行反思:“一以贯之是首要的;多学而识,乃是知之次。孔子并非不注重多学而识,不过认为如仅多学而识,所得的只是零杂的知识而已,尚不足以为真学问,必须发现一个大原则以通贯所有知识方可。”[3]通过孔子的言论可见,孔子极其看重“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只是对其具体的内涵孔子没有明确的表达,“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孔子这里还是一个尚待明晰与发展的概念。
2.曾子以“忠恕”为“一”诠释“一以贯之”
孔子的弟子曾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对曾子影响极为深刻,可以说曾子学说体系的建立与之密切相关。曾子将“一以贯之”理解为“忠恕”。何为“忠”,则分为两方面去理解。通常大多数人会狭隘地理解为忠于君主或者是忠于国家,其实“忠”更强调人内心的真诚,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何为“恕”,“则为将心比心,己之所欲,推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68曾子将“忠恕”具体体现在他的人生观、修养观、宇宙观三个方面之中。在人生观中,曾子主要将“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他曾经说过“民之本教曰孝”[5]86,认为孝是“仁”的出发点与归属点,是最基本的道德。曾子在《孝经》中强调所谓仁,就是以奉行孝道为仁;所谓礼,就是以奉行孝道为礼;所谓义,就是以奉行孝道为义;所谓信,就是以奉行孝道为信;所谓强,就是以奉行孝道为强。安乐从顺行孝道中产生,刑罚也由于违背孝道而兴起,因此,若不“孝”,则无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也无法真正做到“忠”。在修养观中同样也表现出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笃实,《论语》中曾子常言“吾日三省吾身”[1]4,认为人应该经常自我反省,去思考自己的不足。而这些思考来源于“仁”,《曾子》中说道:“君子以仁德为尊,天子富甲天下,不如仁义。”“君子思仁义。”[6]曾子以仁义内化于心,显而易见,这是将君子的修身归纳于修心,最终达成“著心于此,济其志也”[2]13的理想境界。曾子所论的修养过程是将“修心”视为“一以贯之”中的“一”来看待,贯穿于整个人生,最后达到以“仁”成“礼”的状态,同时也达到“恕”的境界。不仅如此,曾子的宇宙观中仍然贯穿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中记载,曾子将阴阳之气看作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源,从阴阳之气去寻找繁杂世间的真理所在,认为伦理五常等道德都是由阴阳之气产生,将此形容为“阳施而阴化也”[7],足见曾子“宇宙观”中“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如此,传言曾子所作的经典《大学》中同样也贯穿着以“忠恕”为基本理念的“一以贯之”思想,《大学·经一章》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8]至善就是“元者善长也”[9]的“善之长”,元者就是生机最初最始的第一个善,是生生之端。止于至善就是止于一。《大学》接着提出“知止而后有定”[10]。定于何?则定于一。只有达到一定的境界,才会志向坚定明确,而这里坚定的便是内心的“一”。“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大学》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将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体现到了极致。此时,在曾子的诠释下,“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已从孔子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开始具体化,成为一套系统的实施方法。
3.孟子以“仁义和仁政”为“一”发展“一以贯之”
作为亚圣的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样将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灵活地体现在他的理论中,并在此之上有所发展。具体体现在孟子的修身观和治国观上。在修身观上,孟子认为,想要成为圣人就必须“保持本心”、善养“浩然之气”。《孟子》云:“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矣。”[11]这种“浩然之气”强大无比,实则乃以保持本性和加强仁义与道德修养的方法罢了。这是与孔子不相同的地方之一:孔子强调“仁”,也强调“义”,但未将“仁义”并举[12]。據考证,“仁义”为墨子首次提出,到孟子时成为其理想人格和主线。孟子将孔子的“仁”作为行为上的准则,或者将行为用另一个概念“义”来表述,认为所谓“仁”注重的是内心的情感,意识上应有的状态,这是将孔子内外兼顾的“仁”具体化的体现。这其中孟子的“仁义”观中的“义”也便是作为“一以贯之”中的“一”,贯穿于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成为其修身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在治国理念上,孟子在与梁襄王讨论治国时明确提出“定于一”[13]理论,认为治理天下,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施行仁政王道,只有施行仁政才能统一一个国家,百姓因为仁政才会蜂拥至此拥护君王的统治。如何具体实施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将百姓放在帝王之上的位置,将得民心视为“天下统一”或者“天下一统”的前提,只有这样才会有长久的安定。可见至孟子时,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一以贯之”的具体内涵得以明晰化,使得“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可操作性更强。
4.荀子以“以一持万”丰富“一以贯之”
上接儒孟的荀子同样也坚持“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并从深层次去理解“一以贯之”。《荀子·非相》云:“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15]74“以一知万”是指认识了一个事物,掌握了该事物的本质,就可知道与此类似的千万个事物。后来荀子认为,了解这个“一”之后,不仅可以“以一知万”,还可以进一步地“以一持万”。《荀子·儒效》云:“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15]134在荀子看来,只有能根据一件事物把握上千万件事物的人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儒者,即使在鸟兽之中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合乎礼仪的事情。荀子将“一以贯之”的思想丰富为“以一识万”“以一持万”,在理论层面上更加注重实践的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先秦儒家“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的内涵。
5.其他学者的理解
“一以贯之”的原话虽然只在《论语》中被提及两次,但却一直贯穿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然而,“一以贯之”的内涵孔子尚未明确表达,故自汉以来成为经生争辩之端。何晏注谓:“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16]何晏认为,“善有元”是众善之本,也是“一”的内涵,善不是来源于经验,所以不需要多学,知一足以知多,知本足以知末。所以,何晏强调,我们追寻的是万生万物所归于的“一”的理念,才可“众善举”。朱子在注释这一句话时采用了曾子的观点:“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万事,忠恕是一贯的注脚。”[5]87将“一以贯之”中的“一”理解为“忠恕”,简言之就是反身尽己、推己达人,以理学为万事万物之根本,又以“心”来贯通万物。王夫之谓:“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者。”[17]如果将一粒稻子种下,则可以生长出来无数稻子,天下都是这样,圣人也是如此,若懂了世间万物之“根”,那便理解了天下之道。与何晏的“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何晏强调的是万物归于“一”;而王夫之则强调的是万物从“一”出发,一个为聚集所有,一个是呈发散的状态。近代章太炎说:“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约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5]86章太炎从“一以知十”“举一反三”的发散角度去理解“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将之与方法论中的“演绎”“归纳”相比较,在荀子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层地阐释,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其之见。胡适在章太炎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道:“我的意思,以为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是孔门的方法论,不单是推己及人的哲学。”[18]在胡适的论述中,“一以贯之”已经明确地成为儒家学说的方法论思想。虽然上述诸家对于“一以贯之”抱有不同的看法,但存在着共同之处:都强调“一”的理念,在“一”的基础上博古通今,不拘泥于“一”的狭隘而广博地吸纳知识,但又强调在广博的同时又归于“一”。总之,孔子所描述的“一以贯之”,是贯穿于其思想始终的方法论,这也是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随着代表人物、形式、内容的不断变化,仍然能够保持“我还是我”的原因之一。
二、“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内涵发展的归因
“一以贯之”自从孔子将其提出,到曾子以“忠恕”诠释,至孟子的“仁义仁政”发展,最后是荀子的“以一持万”丰富,这不仅与曾、孟、荀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传承有关,更与他们身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客观历史环境与主观认识经验有关。
1.曾子受孔子耳濡目染影响,用“忠恕”阐释“一”
孔子在提出“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时并未诠释“一以贯之”的具体含义,他只是在与曾子谈及“一以贯之”时寥寥地说了一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1]54曾子明白了老师的话,在解释给别人的时候,和老师所讲应该是一致的。孔子在《里仁篇》中所谈到的“道”归结为“仁”,这个“道”是形而上的道,是“本体”上的道。然而,曾子并未回答夫子之道是仁,而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54。“忠”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解释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9]。如果自己想要立身,就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恕”孔子则定义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68。然而,为什么曾子不回答孔子的道在于“仁”,而在于“忠恕”,主要是在于“忠恕”与“仁”的关系。孔子在与曾子说“道”时,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道”,而是可以“一”可以“贯”的道,是动态的可以执行的道。曾子将它概括为“忠恕”,“忠恕之道”是自己不愿意别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不要把它施加到別人身上去,离孔子的“道”已经不远了。所以,“忠恕”中“忠”可以解释为尽心竭力,“恕”也就是“仁”,即是尽心竭力推行仁[20],这是对于孔子“道”可操作层面的解释。
2.孟子身处动荡不安社会,以“仁政”发展“一”
孟子是“仁”学说体系的巨大贡献者,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孟子的“仁政”思想跟孔子的“仁”是分不开的,孔子的“仁”是孟子“仁政”的基础。孟子之所以提出“仁政”,主要与其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价值观念冲突日益加剧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四分五裂,但孟子积极入世,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治国理念,但都未被接纳。孟子在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归纳之后,潜心研究儒家思想,但他希望的是将思想投向现实斗争更本质的东西上去,寻求更完美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将“仁”的思想结合现实到达“仁义”,最后结合政治形成“仁政”。孟子认为,一个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完全取决于民心之所向背,这是其“仁政”的出发点和归宿[21]。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则是对“仁”的最好阐释,但他认为保持“仁”只是“修心”之所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与现实结合:“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致天下可运于掌上。”[22]圣王只有用怜恤别人的心去体恤别人的政治,那么治理天下才会像在手中玩弄东西那么容易。从“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这一过程便是从“修心”到“仁政”的转化。孟子与梁襄王会面时更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23],即不嗜好杀人的人才可能统一一个国家。天下君子若“不嗜杀人”,天下的百姓便纷纷前来归顺。从“仁”出发,人要“仁义”,君王要“仁政”,这是孟子的理想,也是“仁”思想贯穿在孟子生命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3.荀子在百家争鸣、天下归于一统中,以“以一持万”丰富“一”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各个国家由分裂逐渐走向统一,百家争鸣的生活环境让荀子的思想在其中受到不少影响。荀子立于儒学,博采众家之所长,对于孔子的“吾道”论述曰:“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24]28君子若精通“道”,专心于道,心志不偏,则万物都可归于“一”,用它来帮助考察万物,就能明察,用纯正的思想、明察的行为去对待万物,那么万物都可以得到治理了。这亦是在孔、孟“仁道”上的拓展。荀子又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24]28掌握道、做事的原理,那就可以以一生得万千,道不可拘泥在小范围内,而是要举一反三。换言之,掌握了“一以贯之”的“一”,那就要将“一”来贯之以千万。荀子继承了孔孟“一以贯之”的“仁”,并将其与诸家学说进行结合考量,在实践的层面上提出:掌握“一”,那就要“以一持万”,将“一”的道展现得彻底,这相较于孔、曾、孟的学说来说,更加具有实践上的意义。
通过对曾子、孟子、荀子“一以贯之”含义变化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以贯之”的实质“一”就是“仁”,在孔、曾、孟、荀的诠释下不断地发展变化。孔子提出“仁”,在教学、自身修养等方面都贯彻着这个基本理念;曾子在老师“仁”的理念上做进一步阐释,将“仁”从理念上的概念落实到实践上,将“仁”归纳为“忠恕”,即“尽心竭力地推广仁”。曾子的“忠恕”针对的主旨侧重于自身修养;孟子在此基础上将“仁”与政治和日常处事结合,将“仁”的概念扩大化为“仁义与仁政”;荀子则认为,“一以贯之”则可以以一持万,在通透了“一”的实质上,与“一”相关的事物也会自然地掌握牢固,将孔子“一以贯之”中演绎的成分进行了拓展。先秦儒家的“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在孔子、曾子、孟子、荀子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表述,但自始至终他们的核心出发点都是在“仁”的基础上,围绕着一个坚定的信仰,一直坚持下去。
三、“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对当下教师的启发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经过孔、曾、孟、荀以及近代儒家学者的传承与发展,展现了其独有的魅力与价值。“一以贯之”是孔子的首要哲学方法论思想,从曾子的“忠恕”观至荀子的“举一反三”理念,都是儒家极其关注“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的体现。对“一以贯之”方法论思想进行分析梳理发现,当今教师应牢固树立教书育人为“一”的使命,才能更好完成立德树人的目标;教师只有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精神贯穿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活,才能获得自身的持续发展;教师要掌握“以一持万”的教学方法来育人,学生方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1.教师应牢固树立教书育人为“一”的使命
教师是一个令全社会都尊敬的职业,自古以来,教师的地位基本上都处于一个较高位置。然而,价值多元化、信息化、市场经济的多方面原因造成了教育变革中教师角色的错位,进而导致教师使命感的缺失,出现了不想当教师,乡村学校教师资源缺乏,乡村教师流动量大,师范学院招生难,教师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等情况,教师的使命感逐渐下降,在教育改革的时代洪流中也是“随波逐流”,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与目标。从根本上说,使命乃是根植于主体自觉意识的主体自身所应担当的重大责任和义务,其中内涵着的是主体对待自身、他人、民族、国家与社会利益的一种积极态度和责任感”[25]。这也告诉我们,提升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感有多重要。孔子、曾子、孟子和荀子他们身为教师一生都坚定着自己“仁”的理念,虽然每个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但他们的一生都将自己定位明确,明白自己的职责,正如钱宁先生在《圣人》中感悟的那样:“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在我看来,是他能终生坚持一种信念。”[26]孔子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用他“一以贯之”的理念坚定着他的理想,忍受着其他职业所没有的孤独。然而,当下部分教师受一些世俗影响,动摇了身为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迷失了心性,更不用说像孔、曾、孟、荀那样,有着一以贯之的信仰,在诱惑面前坚定不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一”。周勇在《跟孔子学当老师》中反思当今的教师:“上路不容易,但是上路之后不迷路,更不容易,因为太容易被周围纷繁妖娆的事情以及信息干扰,变得心浮气躁。我就曾因为陷入后现代主义的迷雾而失去了心灵方向,‘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也不知道去寻找‘坚固的东西。”[27]39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若教師没有办法做到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根本上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从而教会学生如何成长,那教师这个职业便也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反思当今教师,说过一句话:“我们并非医生,而是疾病。”这句忠告,非常适合现在正在尝试走进柏拉图和孔子来治愈自己的教师[28]。孔子值得我们学的,是他精神可以不断地影响着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根”,以孔子的思想为根,在教学的同时坚定自己的教学使命,给学生带去文化和精神上的熏陶,真正地教书育人,而不是因为世俗的好与坏而忘记成为教育者真正的意义所在,也不是仅仅让学生通过所谓的考试,而不知自己究竟该往哪里去。教育者必须从“迷雾”中钻出,提升自身修养,与时俱进,找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一”并且“贯之”下去,将教书育人的使命感融入自己的血液,教育方可继往开来。
2.教师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精神贯之
每一种职业都具有其内在的职业精神,教师作为一门以教书育人为使命的职业,挑着培养人的重担。教师的职业精神对于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的职业精神是构建教师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9]。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标准:“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30]。但现在,有一些教师不太认同教师的价值及其特殊的意义,只是把教师当成谋生的手段及工具,在教学上不愿意跟随教育改革的脚步,固守着陈旧的教育观念,导致教师的职业精神发展停滞不前,没有办法适应现在学生的发展要求,跟不上现在的教学节奏,并且因为思想陈旧、对自己职业不满,导致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对自己失去信心,同样对自己教学工作进行反思的教师越来越少,教师的终身学习理念也显得越发空想。对比孔子、曾子、孟子和荀子他们作为教师,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作为自己的职业操守,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他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停止自己的梦想——孔子周游列国,不断地向大家宣传自己的思想,尽管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但孔子并没有放弃,还在与自己的弟子和他人交流时不断地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一直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学而不厌”;曾子也曾以“吾日三省吾身”来提高自身修养;孟子与荀子更是在坚定从教的决心后不断地提高着自己,反省着自己。他们面对不理解的问题时,虚心求教,哪怕对方的知识涵养并不如自己,但不认为是羞耻的。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31],并不是说三个人一定有自己的老师在,而是指三个人当中必然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人,若是善人,那则学善,若是恶人,那便用以反省自己。孔、曾、孟、荀一直以“仁”作为自己的教育底线,用仁、义、礼、智、信严格要求自己,用修身养性来不断提高自己,用以更好地教授学生,这样的教学之恋,是现在教师所需追求的,也是应当一以贯之的。孔、曾、孟、荀不仅对待教学一如既往地爱,对于学生也是充满师生之爱:在先秦的儒家,只要学生愿意学,主动地去学习,不会因为其出身以及学习的好坏而有所区别对待。孔子更是对待学生宛若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知识的教授不会因为亲疏而有所不同,真正达到了“诲人不倦”的状态。反观当下的一些教师,在班级里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产生出“优生”及“差生”的群体代名词,在对待其不同“团体”的态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区别,用“毁人不倦”和“因财施教”完全扭曲了“诲人不倦”和“因材施教”的意义。当下教师应站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角度进行自我反思,真正将“爱教育”“爱学生”贯穿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精神强化于内心,终身学习,发展完善自己,对学生一视同仁、因材施教,引领学生向善向上。
3.教师应掌握“以一持万”的方法育人
“以一持万”即“举一反三”的拓展,它对教师的要求不仅仅是教学中简简单单地教授完知识点就可以结束教学,而是要求学生学习之后可以从一个知识点出发而理解相似所有知识点。即要求教师在教授知识时教的是学习的方法,而不仅是知识的本身。这也是现在经常讲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即传授给人以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道理其实很简单,鱼是目的,钓鱼是手段,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解长久之饥,如果想永远有鱼吃,那就要学会钓鱼的方法。现在新课程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根本上取决于在校期间自主发展的空间和维度,取决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虽然每个教师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平时的课堂上,真正肯放手让学生去想、让学生去讲的并不多。勤奋的教师们往往是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到头来还是一节满堂灌的课,有时甚至还要利用课间10分钟,但结果是教师在上面讲得唇干舌燥,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32]。这也表明,传道授业解惑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基本职责所在,学生学习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教师这里获得,教师教授给学生文化知识以及如何做人是责无旁贷的,但如果想成为一个好老师,让学生掌握学会知识的能力远比学生学会知识重要得多,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重视学生参与,引导学生自我评价与反省,养成优良的自我习惯才是教师所需要做的。周勇在《跟孔子学当老师》中说:“从孔子以及朱熹等人的教学实践来看,爱仅仅是池子里美好的存在之一,还得教学生怎么样游泳,游什么样的泳,什么又是最好的游姿。”[27]128儒家最推崇的教学方式为启发式教学,反对将死气沉沉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如果将死气沉沉的知识直接硬塞给学生,那并不是对学生的爱,反而是将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给掩埋的错误方法。若教师在学生似懂非懂时给予学生一定的启发,学生恍然大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式与方法,那么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学生必然可以举一反三,以一持万。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 罗新慧.曾子研究:附《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注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67.
[4] 芳园.论语·中庸·大学[M].耀世典藏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5] 姜涛.曾子注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6] 刘光胜.与《曾子》十篇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41.
[7]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M].长沙:岳麓书社,2013:343.
[8] 曾参,刘强.重读经典·大学:平民的修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21.
[9] 伍华.周易大辞典[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1237.
[10]张葆全.大学中庸选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11]秦榆.孟子学院[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7.
[1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617.
[13]南怀瑾.孟子旁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16
[1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4.
[16]何晏.論语注疏[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224.
[17]陈梦雷.周易浅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49.
[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5:92.
[19]孙立权,姜海平.论语注译[M].最新修订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73.
[20]《论语》“一以贯之”与“忠恕”原来是这个意思![EB/OL].(2016-12-25)[2019-09-2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25/00/37268633_617420163.shtml.
[21]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34.
[22]黄文娟,许海杰.孟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44.
[23]李修生,朱安群.四书五经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66.
[24]李存山.关于荀子的“以类度类”思想[J].人文杂志,1998(1):27-31.
[25]李飞.试论当代教师的社会使命感[J].现代教育论丛,2009(4):59-62.
[26]钱宁.圣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
[27]周勇.跟孔子学当老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8]汪辉.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0.
[29]储朝晖.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1949—2009):下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725.
[30]辛伟豪,王晶莹.“四有”好老师视角下我国中学科学教师师德现状的实证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9(4):41-46.
[31]李世化.孔子大讲堂——孔子的忠恕之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59.
[32]张亚星.自主·合作·探究: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22-28+160.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