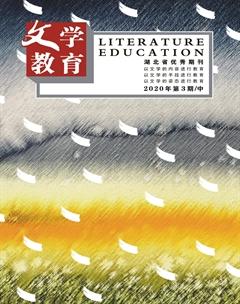新世纪乡下人进城题材电影主题解读
内容摘要:乡城迁徙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动之一,与这种现实对应,电影市场上也出现了一大批乡下人进城题材作品。人们常常认为这类影片属于社会问题电影,除了“介入现实”的精神值得看重外,在艺术性方面难以差强人意。事实上,很多优秀的进城题材影片虽然与社会现实保持了共振,但并没有放弃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特别是它们在叙述出进城者的生存状态时,由于着重于对人的精神的探索,取得了令人刮目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乡城迁徙 电影叙事 存在主义
昆德拉有个著名观点:“小说是人的存在的探测器”。通过描述“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人可能做的一切”,追问“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些什么?”这一亘古难题。[1]其实,一切优秀的艺术都可作如是观。具体到当前的乡下人进城题材电影,人们往往简单地将其视为介入现实的社会问题电影,这无形之中窄化、弱化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很多此类影片虽然关注社会现实,却又指向了更永恒、更根本、更具魅力的“人的存在”。而在它们叙述出的“人的存在”的诸种状态中,“虚悬”,就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种。
一.“双重的异乡人”
作为描述“人的存在”状态的“虚悬”概念,来自萨义德。根据萨义德的观察,从一种文化空间移入另一文化空间的移民,常常既无法融入“寄体”,也难以返回“母体”,以至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处于“两不着边”的“虚悬状态”。[2]在这里,“虚悬”既是一种现实生存情境,更是一种心理情境或情感情境。在当前乡下人进城题材电影中,那些怀揣梦想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移民,就经常陷入萨义德所描述的这种困境:既进不得城,又返不得乡,永远“在路上”,永远无“家”可归。——“家”在这里通常并不主要指实体意义上的家园,而主要是一种心理慰藉、精神归宿和情感寄托。
先看进不得城的困境。以《欢迎你到城里来》(2009年)为例,影片大致内容是乡村男孩牛顿被做装修工的父亲接到了城里读书,却因穿了一双假耐克鞋处处受到城市同学的嘲笑和排挤。但由于生意不好,父亲无力为牛顿购置真耐克。后来,牛顿在校运会长跑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学校奖励了他一双耐克鞋。可惜还没舍得穿,就被父亲为承接一项工程拿去送礼了。耐克鞋在影片中是一种象征,既承载着牛顿对城市的认同,也承载着城市对牛顿的认同。无论是牛顿还是城里同学,都认为只有拥有了真耐克,才与城市人身份相匹配。而这双鞋子始终未能得到,说明牛顿依旧是“高岭乡牛庄村的牛顿”,而未能实现成为城市人的愿望。《欢迎你到城里来》的开场,是即将进城的牛顿站在村口等车,这时有一个关于他所穿的鞋子的特写:鞋子已经开胶。而影片的结尾,是学校奖励的耐克鞋已被父亲拿去送礼的牛顿坐在出租屋里闷闷不乐,这时又是一个关于那双开胶的鞋子的特写。一首一尾两个相同的镜头,让整部电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隐喻了牛顿未曾发生丝毫改变的命运。
再看返不得乡的困境。以《回家结婚》(2010年)为例,电影讲的是城市发生了经济危机,马老亮结束打工生活回乡结婚,最后却不得不再次进城打工的故事。回家以及结婚,都代表了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为此,影片专门设置了一个“融入土地”的镜头:求婚前,马老亮躺在刚刚收获过的田野上,用散落在地的甘蔗叶掩埋住自己,然后在那里睡了一觉。不过,没等真正结婚,未婚妻就怀孕了。这时才发现马老亮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领取结婚证。适逢当地政府正在严查“非法结婚”,为躲避风头,马老亮只好带着身怀六甲的未婚妻去城市打工,其时距离新年已不到十天。全片结尾,是马老亮和未婚妻坐在卡车上离开家乡。电影采用马老亮的主观视点并以手持摄影机的拍摄方式,拍摄了一个“告别”的长镜头:亲人和家乡渐渐远去渐渐模糊,无限的伤感、留恋和无奈充斥主人公心头。在这部影片中,不仅“回家结婚”的愿望成为泡影,整个乡村也都是一副“沉沦”图景。例如马老亮的外公重病缠身,“全身疼痛,怕冷怕寒”。年幼的表弟是一个只能在梦中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而且其所在的学校也拆掉了,村里的儿童多半都不再读书了。行将就木的老人象征着乡土家园的衰竭,教育和儿童的危机则又象征着这个家园已经失去了未来。在村庄,人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根据梦境的预示,买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小彩票;而马老亮回乡在村头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醉汉。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就是乡村生态的真实写照。再加上贯穿全片的场景,有干涸的土地,有破败的院落,有灰蒙蒙的天空,有尘土飞扬的道路,所有这些,都如鲁迅《故乡》对于故乡的经典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幾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既然进城还乡两不能,那么无论在城还是在乡,人都处于“虚悬”状态,也就是无可选择的命运了。在《盲井》(2003年)中,姓元的无名矿工被害死后,骨灰被凶手倒入马桶冲进了下水道,骨灰盒被扔进了垃圾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成了孤魂野鬼,这是“虚悬”状态。在《一诺千金》(2006年)中,小宝随父亲进了城,父亲却不幸病亡,父亲的工友带他回乡寻母,却始终没有找到。乡下儿童失父又失母,这也是“虚悬”状态。在《落叶归根》(2007年)中,民工刘全有死后,工友老赵背着他的尸体送他回家,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老家,却发现因三峡移民,刘家已迁到了另一个省份。即便能够找到新家,刘全有也没有真的“落叶归根”,这同样是“虚悬”状态。在《百鸟朝凤》(2016年)中,一帮唢呐匠在乡下无法维持生存,到城里打工不到半年,有的失去了手指有的染上了肺尘病,同样生活艰难,这依旧是“虚悬”状态。包括那唢呐本身,在乡村失去了市场,在城市又沦为卖唱者的乞讨工具,何尝不也是一种“虚悬”的象征?总之,这些乡下人在城乡之间成了“双重的异乡人”:“他们是突入城市的‘异质,城市将是他们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异乡,而乡村也将不能再安妥他们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他们遭遇到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3]
二.“抓住一点真实的基本的东西”
面对“虚悬”状态,人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或采取某种行动。精英知识者常常认为,接受、坚守甚至选择“虚悬”状态,像波西米亚人那样做“永远的流浪汉”,像鲁迅《影的告别》中的“影”那样“彷徨于无地”,像萨义德所称赞的流散知识分子那样“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能够获得异乎寻常的积极意义。或者说,在当今这样一个被称为“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作为一种真实处境和隐喻处境兼而有之的“虚悬”状态,为获得革命性、先锋性的“流浪者的思维”提供了保障。毕竟,这一思维本就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性、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4]为根本特征和主要追求的。但问题是乡下人终究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在“虚悬”之中体会到的只是悲苦和不适,他们的应对之道总是像张爱玲小说中“软弱的凡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从而希望以“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摆脱“虚悬”状态。[5]
于是,进城电影中就普遍出现了一种“寻找”主题:“《过年回家》中陶兰寻找回家的路;《盲井》中少年寻找父亲;《盲山》中女人寻找逃跑的路;《小武》中小武在大街上寻找猎物,同时也寻找友情、爱情和亲情;《十七岁的单车》中打工少年寻找丢失的自行车;《卡拉是条狗》中老二寻找解救卡拉的办法;《图雅的婚事》中图雅寻找能接受前夫的丈夫等等。有希望、有所期待才执著地‘寻找,‘寻找成了底层人物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支柱和理由。”[6]在这里,路、父亲、情感、自行车、丈夫等,就是“真实的基本的东西”,而“寻找”它们,就是不甘于“虚悬”,要“证实自己的存在”。
特别是在《落叶归根》中,几乎将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老赵背着刘全有的尸体回乡诚然是寻找归宿,而他一路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其实也都在为摆脱“虚悬”状态而寻找心灵家园。像那位货车司机,本来设想跑完30万公里路程就与相爱的女子结婚,孰料完成任务后女子却弃他而去,为此痛不欲生。经过老赵的鼓励,准备再跑30万公里将女子找回来;像那对养蜂的夫妇,妻子因打工时被工厂的大火烧毁了面容而处处遭人嫌弃,夫妇二人为此选择了养蜂,因为这样可以远离人群;像那位依靠捡破烂和卖血支撑儿子读大学的单身农妇,虽然儿子并不以她为荣,她却依旧以儿子的成才为最大安慰,而且也并不排斥对自己爱情的寻找;像那位孤寡老人,预料到死后一定无比凄凉,于是就在生前为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熱热闹闹了一把,由此得到了慰藉;而那位发廊妹,为排解独在异乡的落寞,甚至将自己的发廊都命名为“梦乡发廊”。这些人物都是边缘人,而且在电影中都没有姓名,因此,他们与刘全有和老赵的相遇,就与二者分享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命运,也分享了二者“在路上”的生存状态所承载的寻找归宿和寄托的追求。至于他们的努力能否真正结束“虚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抓住一点真实的基本的东西”,展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对这一点,影片是高度赞赏的。举个例子,重新踏上寻找爱情之路的货车司机与老赵分别时,电影设置了一副非常唯美的画面:空中一朵靓丽的云霞,金色的夕阳下,两条小路伸向远方,路旁皆绿树繁花。在舒缓悠扬的配乐中,依依惜别的两人互相鼓励:“你一定把她(女子)找到”,“你一定把他(刘全有)送到地方”。这是经典的导演诠释镜头。
但当前电影并未因对这些底层人为摆脱“虚悬”状态所做的努力的赞赏而陷入廉价的煽情和乐观,相反,它们直面现实,如实叙述出了弱势者的努力同样是弱势的,乃至是虚幻或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十七岁的单车》中体现得再也明显不过。乡村少年小贵进城当快递员,公司有偿提供了一辆高级山地车,他从此要做“新时代的骆驼祥子”了。而这辆车就是小贵为融入城市所能依靠的唯一资本,所以视如生命,影片多次出现小贵骑车时轻松愉悦的欢快场景。但是如同祥子的黄包车经历了三起三落一样,小贵的自行车在城市也并非无坚不催的利器,它也同样经历了三次“被侮辱与被损坏”:第一次是刚要挣够公司代付的购车款,也就是刚要真正拥有这辆车,车子就被人偷去了;第二次是依靠不懈努力找到了车子,但由于已经被城市青年小坚从二手车市场购置了,虽然竭力争取,却也只能无奈地与小坚“一人骑一天”,即是说并未取得对车子的完整权利;第三次是小坚终于答应将车还给小贵了,但没等骑走,就遇到小坚的仇敌前来寻仇,他们认为小贵是小坚的同伙,不仅对他围殴,还毁坏了这辆车。电影将毁车者的行为刻画得让人胆战心惊,几乎是以疯狂、病态的方式摔打、踢踏自行车。或许在这位城市痞子心里,一个快递员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么高级的山地车,否则就是对身份的僭越,而要阻止这种僭越,就必须通过将车辆彻底毁坏来完成。影片结尾,是小贵肩扛已经变形的自行车走在城市街头,电影采用了慢动作镜头:尽管主人公坚定地奋力前行,但看起来却走得非常缓慢。再加上“慢动作配乐”,都象征了人物的疲惫、受挫、艰难、无助和苦痛。最后一个镜头,则是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观众已看不到小坚的身影,预示着在茫茫人海,他又陷入了“虚悬”状态。换言之,看不到他有切实的归宿。
但无论如何,小贵为了融入城市所依靠的自行车,毕竟还是一种能够抓得住摸得着的实在物。而在《不许抢劫》(2009年)中,农民工杨树根所依靠的,却是虚无缥缈的“良心”:老板答应只要干够一年半就一定发工资,本着“我只知道,这世上,人不能欺负人,更不能骗人,人说出来的话要算话”的淳朴道德和信念,杨树根还真的带着一帮兄弟干了一年半。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最后铤而走险以违法的手段才讨到工钱,但也因此被判刑一年。城市显然不是杨树根的家园,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杨树”离开了乡“土”,如何扎“根”?但问题是乡村也不再是家园了,杨树根之所以去打工,是因为妻子嫌他窝囊,跟情人跑到城里来了,他是为寻妻才进城的。——在文学艺术中,女性往往是家园的象征,失妻也就意味着失家园。如此,从乡村“拔根”又无法在城市“扎根”的乡下人,除了“虚悬”无依,又能怎样呢?
三.“脱胎换骨”的代价
在根本上,进城者意愿中的家园并不在乡村,而在城市,否则他们当初也就不会选择进城了。“城市文明作为现代化的象征符号,是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的乡村追随者;而乡村追随者为使自己能融入城市,必须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蜕变历程”[7]。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艺术中,乡下人并非绝对不能实现由乡入城的身份变迁,但他们为此却必须“必须付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代价”[8]。这无疑是一种悲剧。而如果乡下人对这种悲剧不自知,甚至将悲剧视为喜剧,那才是更沉痛的悲剧。一些优秀的进城电影就对此进行了精妙叙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狗小的自行车》(2007年)。
《狗小的自行车》的大致内容是:农民工的儿子狗小的自行车丢了,在寻车的过程中遇到了城市人海天。海天的儿子小天六年前走丢了,由于狗小与小天长相相似,海天就笃信狗小就是自己儿子。直到狗小娘拿出狗小的出生证明,海天才彻底死心。但后来,狗小爹在干活的时候摔断了腿,实在拿不出医药费。无奈之下,狗小娘主动找到海天,欺骗他说原来的出生证明是假的,狗小确实就是小天,愿意将儿子归还,以此从海天那里获得了一笔酬金,拯救了狗小爹的命。而狗小也终于“脱胎换骨”,过上了城市人的幸福生活。从生活逻辑看,电影当然存在一些漏洞,例如只要一个DNA鉴定,就可以证明狗小的身份。但抛开这一点不论,影片对于人性的解剖才真正耐人寻味。
首先耐人寻味的是狗小爹娘的反应。最初,海天主张狗小是自己儿子时,他们无比气愤。后来无奈地将狗小送给海天,也无比悲痛,电影还为此专门设置了两个镜头:一是答应将狗小归还后,狗小娘满含泪水迈着僵硬的步伐在街上缓缓行走。这时,有园艺工人正在修剪大树。随着刺耳的电锯声,一根根被锯下的树枝沉重地坠到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二是狗小被海天夫妇接走了,狗小娘哭泣的画面淡出后,在沉重的配乐中,淡入了一台挖土机挖土的场景。这两个场景的象征都很直白:树枝被从树上锯下,泥土被从大地挖出,都象征着母子分离,至于声音,则象征了狗小娘内心莫大的哀痛。然而即便如此,看到狗小终于成为了城市人,狗小父母依旧无比幸福地感慨:“多少人做梦都想成了城里人,狗小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为了让儿子获得城市身份,必须以放弃儿子为代价,而且又为这种放弃而欣喜,这真是对现实和人性莫大的反讽。
更耐人寻味的是狗小的反应。狗小对自己的名字是这样解释的:“一条狗的狗,大小的小。”由于狗小又来自一个最底层的家庭,因此电影其实是希望借助这个名字让人们联想到一种传统道德伦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实际上,狗小并没有遵从这一道德伦理,自海天误认他为儿子之始,他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示了认同。原因倒也简单:城市家庭為他提供的优越条件,能让他在同学面前“抬起头”“有面子”。这种虚荣心,是他的原生家庭绝对无法满足的,那个家庭甚至不能保障他写出一篇体面的作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是xx》,其他同学的爸爸都是工程师、经理、会计等,狗小的爸爸却只是一个修鞋匠。所以,在成为海天的儿子后,狗小立即就适应并喜欢上了这种光鲜体面的生活。不仅如此,影片还多次叙述了成为城市人后的狗小对原生家庭的嫌弃、鄙视和排斥。直到最后,当父母再喊他狗小时,他明确告诉父母:“以后叫我小天!”这意味着狗小已经彻底否定、割裂自己的出身了。即便父母邀请他回家吃一次饭,他也不屑理会了。对此,父母只能黯然神伤:“小呀,真把家给忘了!”可以说,为了认同城市并被城市认同,狗小的灵魂已经发生了异化。不仅狗小如此,狗小的弟弟也是这样。看到哥哥做了城市人后生活优越,弟弟甚至以绝食向父母抗议:“为啥哥穿那么好的衣服,住那么好的房子!我也要!我也要做海天叔的儿子!”任何形式的身份认同都是由“我来自哪里”“我到哪里去”“我是谁”等种种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如果遗忘了“我来自哪里”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错误回答,那就不可能真正完成身份认同,或者说就是丧失了自我,至少是一部分自我。狗小和弟弟不正是如此吗?一边是父母在底层为儿子含辛茹苦讨生活的情节,一边是儿子因父母身份低贱而嫌弃父母的情节,电影就这样表达了在“城市文明病”中,“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的人性异变。
此外,海天夫妇俩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丢失儿子后,相互之间的埋怨以及亲人的不理解,让二人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而狗小的到来则让夫妻俩重新恢复了恩爱。不过,二人后来先后知道了狗小的真实身份,但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完整,他们却不约而同选择了隐瞒。这无疑是另一层面的讽刺:城市人伦关系的修复和维护,要以牺牲和占有乡下人的儿子为依凭,这就是城乡之间伤害与被伤害的不平等霸权。在这一霸权关系中,乡下人诚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城市人似乎也并不是真正的赢家。电影结尾的镜头,是狗小站在天桥上拿大顶,在他眼里,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倒立起来了,这意味虽然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行走/寻求,但倒立的双脚无法以坚实的大地为支撑,人就会面临失去根基的危险,也就是说依旧会处于“虚悬”状态。
在当前电影市场中,乡下人进城题材影片基本都是小众电影,绝大多数都无法进入院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反倒可以不用过多考虑票房收益,从而能够投入更多精力专注于艺术探索,并奉献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作品。即便这类影片所关注的因城乡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但因为了有了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探索,它们也可以拥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这就是社会问题类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法]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3.
[2][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61-69.
[3]黄轶.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J].小说评论,2008(3).
[4]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5]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93.
[6]何英.在边缘与漂泊状态下寻找[J].文艺争鸣,2013(4).
[7]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J].文艺争鸣,2005(3).
[8]丁帆.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J].江海学刊,2005(6).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5-QN-531)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李玉杰,南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浅析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