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笔下的女人
范家进
“重评文学史”曾是风行一时的口号,只因生逢其时,且有尼采之“价值重估”之义,惹得众多学者纷纷加入“重评”大军。如今却日渐式微,原因很简单——学界热点很多,说是日新月异当不为过,此其一也;而且那“重读”话语权早已被他人占据,后来者又何必跟在后面,咀嚼他人余味?此其二也。
但是,文学史上确实值得重读或重评者依然很多,依然“还在那里”,等待后人为其剥去岁月披上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那么,倘若能够多少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历史真相,更好地走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则“重评”亦无不可,“再探”尤为必要。
这里论及的几位都是文学史上的大家,其作品价值早有定论,只是他们的某些作品,即便只是从纯粹学术角度看,也有深入探讨必要——何况今天所约四位作者,毫無阐释什么“话语权”的想法,只是就事论事、就人说人,也惟其如此,反倒写出了历史的底色和作家的本心。此外,这一组文章所谈作者都是语言大师,故各篇文章在行文方面也力求和论述对象保持一致,至于是否做到了言简义丰、意在言外,则不敢擅自结论,且待读者评判才是。
——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刘克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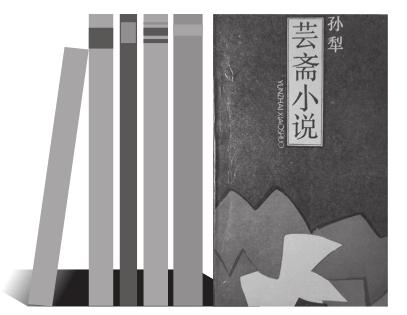
从1981年到1991年,孙犁断断续续写了总题为“芸斋小说”的30余篇小说作品,篇幅一般都只有一两千字,长的也不过三千来字。仅从字数角度看,简直是大山前面的小土丘,但精神产品的分量又岂是可以用数量和体积来加以判断呢。孙犁自己对薄薄的一册《芸斋小说》看得就很重,他曾这么写道:
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文虑——文事琐谈之二》)
作品出版后,评论界、学术界也给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吴泰昌认为《芸斋小说》是“孙犁对小说文体创新的一次有意尝试”;郜元宝则认为,这些系列小说“并非告别革命或忏悔革命, 而是痛惜当下现实与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严重不合,重点是抚今追昔, 是由于目睹今天的败坏而追念往昔的单纯与美好”,还有人说它“绘制了一幅幅‘乱世聊斋图”。
其实,具有“离休干部”身份的孙犁,晚年并不快乐。贯穿整个《芸斋小说》中的情感与文笔几乎都少有明丽清亮色或是开朗轻松。最后那篇《无题》所附的文言体的“芸斋悼之曰”如此道及其中原委:
当今,处开放之时,国家强盛,人民富足。重驿来游,商贾满路。万民欢腾,而君似又有所戚戚。小我之悲,无乃有失大公之初衷乎?无以名之,谓君为后天下之乐而忧,可矣!
壹
统观孙犁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小说,活跃在他作品中的勤劳、朴实、纯洁、美丽的乡村女性形象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水生嫂(《荷花淀》)、吴召儿(《吴召儿》)、双眉(《村歌》)、春儿(《风云初记》)、大绢(《秋千》),还有美艳动人、性格颇受争议的满儿(《铁木前传》)等,无不如此。文学史家也习惯于把擅长表现“女性美”“人情美”当作孙犁小说的风格标记,如王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就这么表述:
他的作品大都以抗日时期的冀中农村为背景,尤其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和她们的伟大 贡献。……在他这些作品中,关于农村女性活动的描绘往往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勇敢矫健的革命行为,但也有一些委婉细腻的男女爱情。
8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也延续了这种评价,认为孙犁小说“着意刻画、赞美的都是妇女”,“所表现的是解放了的新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美”。
《芸斋小说》中所写的女性,总体上与孙犁四五十年代作品中那种婉约、贤淑、朴实、美好,且充满青春气息的女性已经迥然不同,尤其是总不免带上一种阅尽人世的沧桑感。这些女性形象多数来自于他不同人生历史阶段的遭遇,少数则是作家写作这些作品时期的偶然邂逅。按照这些人物在“芸斋小说”中的出场顺序,第一位就是在战乱岁月里曾大红大紫、“文革”当中也跟作家“我”一同落难关牛棚的女相士。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女相士自报罪名和阶级成分时竟然回答的是:“我是反动文人。跟孙芸夫一样!”这位相士“身材修整,脸面秀气”,落难前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但解放前因相术有名,“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文革”中也落得与革命作家(此时自然已成“反动文人”)一样被集中学习和改造的命运。但或许是出于两者均属“天涯沦落人”的境遇吧,这位姓杨的女相士对落难的老作家也还说得上友好,不像另一位也沦为改造对象的女同事那样时时对作家绷紧阶级斗争之弦,所以赢得了作家一定程度的好感与信任。作家还如此辩解道:
我认为此人也不坏,她的职业,说起来是骗人的,但来找的人,究系自愿。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
人民日报出版社最初出版的单行本《芸斋小说》中收有作家纪念其亡妻的《亡人逸事》,内中记载了作者通过媒婆与这位邻村姑娘的结婚经过以及婚后“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篇末的几句议论带有总结性,既坦率赤诚,又充满哀痛与自责。他说: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
而在以单篇形式放在“芸斋小说”专题下发表的作品中未见此篇。“芸斋小说”最后一篇《无题》中倒也出现了写及亡妻的段落,那是以主人公想象自己即将进入骨灰盒的形式出现的:
他对小木盒,并没有什么美好的感情。他尤其害怕,在那种更密集的住宅区,遇到在20年前,先他赴冥的老伴。在那里,她已经获得彻底解放,观念已经完全更新,她可以没有任何顾忌,摆脱一切束缚,向他提出生前忍耐多年的责难,他将无言以答,无地自容。
因此,“芸斋小说”中几篇描写他第二次婚姻及几次婚外情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妨看成孙犁情感世界里的“忏悔录”,其坦率和真诚程度在当代作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按照在“芸斋小说”中出现的顺序(也是作者创作时间上的顺序),这些篇目依次是《幻觉》《还乡》《无花果》《宴会》《续弦》《石榴》《忆梅读〈易〉》。考虑到全部“芸斋小说”只有31篇,这方面的文字比重其实已相当不小。倘若从女性形象是否美好的角度着眼,这些作品与同一作家四五十年代小说之间的距离确实不能以道里计。《幻觉》描写“文革”中老伴去世后“我”遭遇的第二次婚姻,伴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和老干部、老作家命运的沉浮,这位“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的“仙人”兼“侠女”健步踏入“我”的日常生活,随即又飘然离去。作品篇幅并不长,但所显示的短暂共同生活期间,两人在金钱观、邻里观、政治观等方面的隔膜与分歧简直别如霄壤。芸斋主人篇末也只能感慨:“今仙人一女身耳,值不测之机,而求自全之路,余不得责怪之也。”仙人或女侠们自有在复杂年代里的生存法术,一个乱世中的落拓文人又如何能够加以责怪?只能回过头来嘲笑自己“新病并未痊愈,旧病又复发了”。
贰
《无花果》《石榴》《忆梅读〈易〉》均以植物为题,描写的是“我”所遭遇的三段婚外感情,三篇作品写作的时间与事件依次发生的时间正相反,即《无花果》所述事件离写作时间最近,而《忆梅读〈易〉》最远。与其说这些作品侧重表现的是其中的女性主人公,还不如说作家所着重表现的是“我”当年与这些女性产生感情时的感受以及晚年回顾时所生发的一些反思与感慨。三位女主人公分别是青岛疗养时的女护理员、解放前在某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时所寄住的房东家的女儿、抗战时期集体步行奔赴延安的一个女学生。
《无花果》所写女护理员也因为出生农村,刚“离家不久,还带有乡村姑娘的朴实羞怯味道”,因此颇得疗养中的“我”的好感,“平日有了水果,都是请她吃”;有一次,这位护理员反过来请我吃她采摘来的无花果,还别出心裁地要跟我分吃一颗,于是“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看来即使是病中的 “我”,对于女性的美也還是欣赏如故,这也很正常。只是毕竟处在因神经衰弱而引发的长期病休疗养中,加上此事还引起老伴的怀疑,所以不能不让他感到“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情感上的纠缠”。
美固然可以随处欣赏,男女之情却不能不加许多限制。写作时间最晚的《忆梅读〈易〉》(写于1991年4月)篇末破例没有文言体的“芸斋主人曰”,却又破例加了一行附注:“时大病初愈,此作,颇不利于养生。”因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我”对这位女学生是动了真心的。直至事过近50年后的小说中,作者还如此沉痛地写道:
事实是,梅对我是有缘的,是我负了心。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很快就回信,一口答应了。我很快又反悔,这对她的伤害太大了。我一生也不能原谅自己。
并且加以如下的说明性补充叙述:
梅,是我的学生。就在她答应和我缔结同心之时,也只是在延河边上,共同散步十分钟。临别时,我还保持老师的严肃习惯,连她的手也没有握一下。
一段在延河边刚刚萌生的感情,很快又被30岁出头的“我”亲手加以掐灭。对于女性,倘若像作家在他四五十年代小说中那样,仅仅将她们想象成碧水荷花、白雪红梅的风景一般加以欣赏,固然十分浪漫而温馨,可一旦将自己置身在与她们的关系之中,这对敏感多情而又性格优柔退守,且谨守传统人伦道德的作家来说,就很不容易驾驭了,笔下也就多了许多感伤、沉重和自责、忏悔。
叁
《芸斋小说》中写及日常生活中邂逅的女性时也有显得较为超脱,甚至不失“幽默轻松”的文字。其一是《心脏病》。事情发生在“文革”后期,再婚后的新夫人张女士督促“我”去一家医院做刚刚传到中国不久的心电图检查,然而却莫名其妙地遇到一位“二十来岁,穿着那时还很时髦的绿色军装”的年轻女护士——
女护士一看单据,就生了气,大声说:“你应该到门诊部去做!”
张女士低声陪笑说:“我们在楼下交的费,他叫我们到楼上来!”
我躺在病床上,女护士一边拉扯电线,一边摔打着往我四肢上套,像杀宰一样。她一直怒气不息,胡乱潦草地完事,把心电图摔给了张女士,撵我们出屋,就碰上门走了。
在“文革”中与国营医院或别的国营服务部门打过交道的人对这样的场景或许见怪不怪近于麻木了,作品中老干部身份的“我”似乎也采取这种态度。所以当张女士询问要不要将那张刚做的心电图交给大夫去看看时,“我”十分果断地加以拒绝,并肯定自己心脏很好,还如此解劝张女士道:
你还没有看清楚,即使我的心脏一点毛病也没有,也被这位女护士气死在床上,起不来了。既然我完好如初,这就证明:我的心脏非常健全,不同一般。
一番话说得张女士也几乎破涕为笑。以擅长表现纯洁质朴的女性美作为风格标记的作家实际生活中却遭遇如此时髦女郎,不能不说极具幽默讽刺意味。
另一篇是《我留下了声音》,所记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北京一家团体委派两个姑娘来老作家这里让他“留下声音”,又是录音,又是拍照,又是找书,又是题词,忙得老作家不亦乐乎,可老作家积极配合、毫无怨言,因为这两个姑娘的美貌简直让老作家的寒室里蓬荜生辉:
宽去了头巾外衣之后,我发现这两位姑娘,虽然态度腼腆,实在秀美异常,容光照人,立刻使我那空荡、破旧、清冷的房间增加了不少温暖和光彩。
并且解释自己这几年的习惯:
这就是青春的魅力。这些年来,凡是姑娘们叫我做的事,我总是乐意去做,不叫她们失望。即使她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能很快原谅她们,同时容易引咎自责,先检讨自己。
然而两个姑娘回去以后,老作家吩咐的寄几张照片回来以供留念却一直杳无音讯。隔了几年,其中的一位(此时已经结婚)又带来一班人马来给作家录像,一向不喜欢录像的作家也给以积极配合。作家也要求回去以后把这次的合影寄一张回来,但照样还是毫无下文。作家只能自我宽解道,她们仅仅是把这当成一件别人让她们完成的工作,“回去一交差,就算完事了”。作家在篇末“芸斋主人曰”里对此表达得相当含蓄:
风雨交加,坎坷满路。余至晚年,极不愿回首往事,亦不愿再见悲催、丑恶,自伤心神。然每遇人间美好、善良,虽属邂逅之情谊,无心之施与,亦追求留恋,念念不忘,以自慰藉。彩云现于雨后,皎月露于云端。赏心悦目,在一瞬间。
抗日战争时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之后又伴随共和国坎坷经历一同成长的孙犁,晚年写作则一再提及让自己铭心刻骨的“残破”印象,个人家庭的残破、家园的残破,以至民族国家的残破。体现在对笔下女性的感受和描写方面,作家早年那种倾情想象、醉心讴歌的女性美好风景和情思,到了“芸斋小说”里,已然转化成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简直是一片萧索肃杀了。愤激之中,作家甚至对于早年热心讴歌的爱情本身也要给它泼上怀疑的冷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物质实为第一义,……固知巫山一片云,阆苑一团雪,皆文士梦幻之词也!”至于在形式创造方面,有学者认为整部《芸斋小说》“确实算得上是当代新型小说。但它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作者吸取了多种文学营养,其中包括古代文学特别是笔记小说、古代散文以至唐宋散赋营养之后的一种创造”(见张稔穰《〈芸斋小说〉与古代文学》),亦颇有见地。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