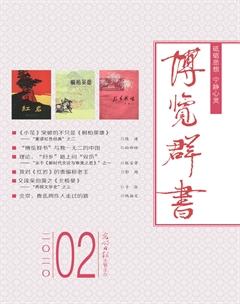此书名尚未道出其理论创造
谭旭东

十多年前,我就在一些重要期刊上读过范玉刚的系列论文和文论,他敏锐的目光、宽阔的视野和全新的姿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过往的研究成果看,显然,范玉刚是一位跨界研究的高手,学术视线自由地游弋在文学、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以及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解读多个理论和学术热点,阐述自己对文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的观点和看法。
若要梳理范玉刚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学和文艺学及文化研究,不可否认,他当归于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人文社科前沿研究学人之列。范玉刚的新著《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厚重的著述,是他主持的中央党校创新工程的《文化思潮与国家文化战略研究》的成果,也是他作为首席专家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部新著,有呈现了他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清晰脉络,有他立于新时代,站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现场所作的现实性思考和当下研究,也有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心得和发现,这是一部既能体现学术创造力的论著,也是一部展示范玉刚敏锐洞察力和现实情怀的论著。这部著作,有三点值得欣赏。
第一,入世和出世的人生态度和学问精神。这是范玉刚的理论和批评最具有感染力的特质,他做研究,写纯学术论文,写理论文章,都饱含感情,有着丰沛的人生感悟,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经验。他的观点既来自前人的理论,他善于借鉴和学习他人的理论和观点;但更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所以读他的文章,能够充分感受到他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入世的学问精神,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位清醒的理论洞察者。如代序《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锻造文艺精品》一文,就可以反映出范玉刚这一特点。序言中说道:
当今天的中国再次汇聚起世界目光、重新复兴为人类文明主体的时候,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国道路的参与者、实践者、记录者、反映者和思想者,当代文艺家不仅有责任让文艺在中国的前行和秩序中成就民族文學经典,更有责任让中国在文化的怀抱和瞩目中迈向世界,助力文明型中国崛起。
生活和工作中的范玉刚,激情满满,有文艺家的豪气,理论和学术研究中的范玉刚也沉潜深邃,胸怀抱负,肩负责任,有人文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三个维度》一文,也可以印证他深具的现实情怀这一特点。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第一要以问题意识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第二要以理论自觉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第三要以国家需求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这三个维度紧紧扣住“当代性”,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指南,聚焦于如何彰显当代性,在充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进行了现实解读,把准了当代文艺研究脉搏,命中了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还有《在紧紧抓住时代中引领当代文艺发展方向》《人性的复归与精神的涅槃》和《众声喧哗中的繁荣与现代性的焦虑》等文,也体现出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风姿。
第二,严谨理论与中肯批评的共奏和鸣。这是范玉刚的理论研究给我的第二个重要感受,他文字很稳,很实,对政策和理论都把握得很到位,表达很严谨,对中外文艺理论、美学观点和当代的最新话语,都信手拈来,看得出来,他的学养很深,但也密切跟踪当下,追踪最新信息,因此,他笔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是有来头的,都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稳中有序,既有理论逻辑,又讲事实逻辑,还讲审美逻辑和情感逻辑。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各种名词术语都纷纷泊来,张政文先生说过的“理论转场”就是一个贴切的名词,正好准确描述了这一现象,但在转场的过程中,是否融合并消化了,是否与中国当代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了,这是个问题。范玉刚在论著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强制阐释”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和《“强制阐释”的歧途与“公共阐释”的正道》两文中,以严谨的态度和中肯的语言,评述了“强制阐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局限,回应了张江先生对文艺理论中国话语建构的雄心和造诣,在评述张江先生的《强制阐述论》和《公共阐述论纲》时,对此有了清晰的判断,他非常认可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阐释”这一命题,这不只是一个名词的换新,也是一个元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当代文艺话语体系的关键词,也是一把文艺理论的新钥匙。这一理论的提出,也解决了文艺理论界和文化界所纠缠不清的西方理论不及物和文艺理论批评失范的问题。在评述张江先生的理论观点时,范玉刚也多有中的的新见,如“阐释学就是一种从语言视角进入的现代本体论,它虽有认知的价值,但不是一种认识论,而是意义的阐发和价值的守护”,如“阐释是文艺批评及其理论建构的一种思维方式”等,这些严谨、直观又切中要害的观点,都体现出范玉刚对“公共阐释”的深度理解。在《“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和《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美学担当》等文章里,也能清晰地体悟他对“十七年”时期的美学思想和消费时代美学研究的梳理和省思,这些论述里,问题意识和批评精神凸显,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情怀跃然纸上。
第三,理解时代与现实基础上的创造创新。这是范玉刚理论研究最值得嘉许的一点,创造、创新才是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本意,没有创造创新,纯粹是整和和复制,显然不是学术,不是研究,也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有的品格。范玉刚的理论研究,有几方面的创造和创新:其一,他的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他出身于文艺学和文艺美学,按照传统的学术研究路径,他应该要么是古典式的学者,言必《文心雕龙》和《人间词话》,在传统的文论里打转转;要么是先锋式的学者,在西方文论里纠缠、盘旋,言必称希腊,并享受已有话语的消费。但他二者不兼,走出了第三条道路,他既没有做古代文论的强制阐释者,也没成为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者,他有效地整合和消化了文艺学、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新的话语等,打通了古代和现代、西方与中国,站在时代和现实的土壤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阐释”者。因此,他的理论话语,既有古典的气韵,又有现代的新颖,还有先锋的前瞻性,既有历史维度,也有现实立场,所以《新时代文论和审美之思》读起来,酣畅淋漓,气贯长虹,有新一代中坚实力派的豪气和热气。其二,他的思维和话语创新。无论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观点的提取和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思考,抑或是对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参与,他都试图形成自己的见解,体现自己的思维,成就自己的话语,尤其是成就自己的理论逻辑和独特发现。在《新时代文论和审美之思》这部著作里的上篇、中篇和下篇之间,看似三个方面的研究,但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都贯穿着范玉刚的理论自觉下的创造思维和理论发现。
当然,前面三点不足以总结范玉刚的学术成就和学问特点,在文艺学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当代文艺批评方面,尤其是对其新时期美学思想研究的研究,以及其文艺理论话语创新与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之间关联的研究,范玉刚的判断和发现还需要专文梳理和论述。品读《新时代文论和审美之思》,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尚未很好地概括范玉刚的理论创造,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等课题的深度研究。不过,对有耐心的读者来说,书名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文本”的该书的内涵与价值。借用书中范玉刚对“公共阐释学”的解读,读者对这个文本里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有深度有创见的文本,既需要共识性的理解和阐释,也需要个性化的理解和阐释,但无论怎么阐释,作为理论“文本”的《新时代文论和审美之思》,其学术的、思想的和实践性的价值和意义是显在的,因此,我的理解也只能是对范玉刚新著的部分阐释,或有限的阐释。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