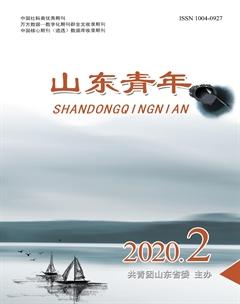科研单位对基因编辑行为的管理规制
潘雨
摘 要:南方科技大学“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过去近一年,在此期间,国务院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其余相应的立法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但却没有提及科研单位应扮好的角色。基因编辑的管理规制专业性强,尺度难以把控,管理存在交叉,规定的法律层级较低,社会重视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科研单位作为科研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平台,有足够的信息来源和专业知识支撑。虽然科研单位在法规范层面上,不具有对科研工作者管理的直接权限,但通过目的解释,科研单位应当是基因编辑行为的管理规制的第一责任主体。
关键词:科研单位;基因编辑;管理规制;责任主体
引言
案例一: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邓宏魁把基因编辑变成了可以治疗艾滋病的工具,通过在成体造血干细胞上敲除CCR5基因,结合已经在临床上成熟应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将编辑后的细胞移植给患者。该种策略编辑成体细胞,不会遗传给后代,不存在伦理上的问题。
案例二: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通过修改一个基因(CCR5),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该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毒。该事件遭到了多方的声讨和谴责,认为贺建奎将修改了的基因融入了人类的基因池,突破了科学的伦理。事件发生后,上至国家部委,下至南方科技大学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南方科技大学更是官方声明,贺建奎副教授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学校并不清楚贺建奎的所作所为。最终南方科技大学决定解除与贺建奎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其在校内的一切教学科研活动。
同样都涉及艾滋病,同样都关系到CCR5基因的编辑,北大的邓宏魁教授和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副教授两人的境遇是完全相反的,這其中牵扯到很多基因遗传、基因伦理等很多专业知识。笔者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基因编辑这一项生物技术上,而是站在法律的角度看,对于基因编辑道理该如何管理规制,尤其是科研单位,例如高等院校在其中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问题提出
201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正式开始施行。条文重点强调了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中承担着监督管理的重要职责,而整个条文中没有见到关于高等院校应当承担的责任。实际上,从两个案例中看,北京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虽然不是基因编辑实验完成的最直接的主体,但却是间接的管理主体,对基因编辑活动的开展、进度以及成果,最有可能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就案例二引发的后果来看,南方科技大学如果在早起就能探知贺建奎团队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及时上报或者采取措施,两名基因编辑婴儿也不可能直到出生,经由贺建奎主动公布才被发现。事件发生后,南方科技大学首先做的是,将贺建奎与学校的关系彻底分割,这一做法显然有逃避责任的嫌疑。但基于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南方科技大学都无法开展相关的管理活动。
科研领域的层级结构分为,科研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科研单位和科研者,行政部门是科研领域的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则是科研交流的平台,但科研单位相比较而言,存在感却较低,它实际上仅起到一个科研平台提供者的作用,对科研工作者约定的限制条件较少。以高等院校为例,根据《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高等院校与科研工作者之间签订的一般是《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因此,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较为简单,且以民事赔偿为基本范畴。在人才争夺的大背景下,严格的管理机制不仅为人才引入加上了门槛,也在无形中限制了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
除去民事上的权利义务,科研单位对科研者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责,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目前已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专门针对基因编辑进行规制的少之又少,主要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几部文件。[1]而进一步明确科研单位对科研工作者责任的,可以说是模糊的。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为例,其在第五章规定了医疗机构对自身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又在第六章规定了项目研究者的法律责任。从表面看,医疗机构是伦理审查的责任主体,但机构的责任对象却没有明确,细究至最后,医疗机构对项目研究者却没有直接的管理责任,完全由伦理委员会承担;而医疗机构仅针对伦理委员会承担日常的管理职责。最新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又提出行政审批,要求临床研究和应用必须经过行政部门审批。为何最终的责任不能完全落在医疗机构身上呢?
再以高等院校为例,高等院校对科研工作者的行政管理职责,只能从《教师法》内寻找蛛相关依据。根据《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师三种行为,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2]而这三种行为很难说是针对科研行为本身。因此,南方科技大学在面对贺建奎事件的时候才显得“游刃有余”,毕竟最终的临床实验与学校无关,学校对其也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所谓的“解聘”是从民事责任考虑出发,还是从行政责任考虑出发都已无关紧要。
基因编辑管理规制,在贺建奎事件爆发前后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不变的是,从责任主体被忽视,到由行政部门直接审批,科研单位在两次变化中依旧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其次,如果由行政部门直接审批,会不会又矫枉过正,诸如北大邓宏魁教授的成果又难以出现呢?问题最终的核心在于,科研单位在基因编辑管理规制过程中该如何正确定位。
二、基因编辑管理规制的难点所在
基因编辑是不是“潘多拉魔盒”,现在还不得而知,它和“人工智能”一起,已然成为当下引起最广泛社会关注的科技议题。正如郑戈教授所言,两者都具有改变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秩序的潜质,而两者也都源于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即生命和智能的去神圣化和可操纵性。
[3]这种自我探求的渴望程度源自于进化的本能,对于科研者个人而言,如果能将这种进化本能落到实处,哪怕是一点细微的进步,他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担忧一样,过度发展而不加以管理规制,贺建奎事件就可能不是个案的存在。那么基因变管理规制,尤其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其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突破的尝试容易触及伦理的底线。“技术先行,伦理在后”的现象和“急功近利”的科学文化氛围在基因编辑中同样存在。[4]名利与科学研究并不是完全绝缘的,但如果为了名利,跨越伦理的底线,名利与科研注定无缘。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基因编辑的研究如同一匹匹跃跃欲试的骏马,伦理是这些骏马的缰绳。张弛有度,这些骏马就能取得让人惊喜的成果,但如果突破伦理底线,就会成为脱缰野马。
既想让骏马奔驰,又要控制缰绳,确实很难把握,不仅在中国,国外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民间对于人胚基因编辑的研究与应用是持谨慎而积极态度的。[5]又如在欧洲,基因编辑的研究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英国总体上是比较开放的,但德国受历史文化影响,一直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立场。[6]
第二,涉及领域前端,专业性强。毋庸置疑,基因编辑技术是世界上的尖端科学之一。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如果没有详细的介绍,恐怕是不能理解,同样是基因编辑,同样是CCR5基因,为什么贺建奎和邓宏魁两人的境遇完全不一样,甚至有的权威媒体也难以辨别其中的不同,例如人民网就提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正面评价,这也成为贺建奎事件的导火索。难度和专业性决定了对基因编辑的管理规制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仅靠科技行政部门的行政审批或者一个单位内的伦理委员会恐怕是难以完成的。
第三,管理存在交叉,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三个部门难以配合。虽然2019年7月1日生效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明确科技行政部门作为主管部门,但是基因编辑的管理规制并不是科技部门专属管辖,如同时具有教师身份,又可能涉及教育部门管理,而临床实验,必然又涉及医疗卫生部门。除此之外,甚至还可能存在“三不管”区域,如中科院,由国务院直管。尽管从事项上来看,基因编輯属于科技类事项,但基于科研者身份的多重属性,以及科研平台的多样性,科技行政部门能否完全胜任,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四,法律规制层级过低,社会重视不够。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国家对基因编辑管理的规制,但我国相关的法律一直没有跟得上国内科学研究的步伐,即使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提出了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也已经到了2016年底。换言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基因遗传技术的法律,散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经有11部之多,但专门针对基因编辑事项的,却是少之又少。另一面,相比较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受众范围较小,贺建奎事件发生前,中国社会对于基因编辑管理规制的关注度可以说达到了最低点,中国知网文章数量的变迁一定层面上证明了这一点。在2018年11月26日之前,仅有7篇文章关注了基因编辑法律规制问题,而贺建奎事件爆发后,共有20篇文章重点关注。除了热点影响外,数据对比也充分说明了社会对相关问题的不重视。
第五,宪法中保障人权的原则没有真正落到基因编辑研究中。众多学者认为,基因编辑管理规制的核心在宪法中保障人权原则的落实。例如郑戈教授就认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并带动以“人的尊严”为核心价值的“生命宪制”国际共识的缔造。[7]有学者提出,权利保障原则应当是基因编制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之一。[8]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保障人权的引入,例如基因编辑的法律底线是人性尊严。[9]韩大元教授则直接从宪法的角度考虑,认为应将基因科技对人类共同体利益的潜在促进意义纳入以宪法基本原则为中心的法伦理判断之中,形成宪法性共识。[10]还有国外相关的文献也认为,遗传基因编辑应该遵守的伦理原则,包括未来人们的福利。宪法与基因编辑研究完全属于两个学科体系,以宪法中的基本原则规制基因编辑研究表面看,确实有些浮于表面,但实际上它才是基因编辑真正的底线。基因编辑的出发点是人,它最终回归的地方也应当是人。从面伦理委员会的设置,以及未来行政审批的趋向上来看,我们的基因编辑经历过贺建奎事件后,努力尝试把重点控制在终点上,实现终端的“人权保护”。但却可能导致人权的反向侵害,即没有积极的保障人权的实现。当基因编辑实现行政审批制后,基因编辑能够开展的程度、范围可能都要大打折扣。
三、法规范角度探析科研单位的定位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科研单位主要分为两大类。从大的类别来看,分为事业单位和企业法人,而从小的分类来看,事业单位又可以分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医疗机构,即目前可能从事基因编辑的科研单位,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企业法人组织。
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授权,仅能作为民事主体,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笔者利用北大法宝进行相关检索,并没有发现科研院所具有法律上的授权成为行政主体。但科研单位作为事业单位,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可以给予其工作人员相应的处分,无独有偶,公立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同样也可以针对自己的科研人员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但高等院校相对特殊,兼具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双重身份。一方面,高等院校是民事主体中的法人组织,另一方面,也是法律授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政主体,这里的法律授权仅指《学位条例》授权其授予学位的相关内容。
企业法人,包括私立医院在内,则因为没有法律特别的限制在内,既自由又封闭。此次贺建奎事件暴露出来的就是,尽管涉事医院极力强调与基因编辑事件没有关联性,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私立医院几乎处于监管中的空白。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从法规范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现有的科研单位对其所属的科研人员并没有法律上直接的监管内容,尤其涉及基因编辑这一内容,除非临床实验,否则科研单位并没有法定的义务介入或主动核查,更没有主动汇报之义务,而科研人员相应的,也没有向自己所在单位进行汇报,或报请批准的义务。
即使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具有事业单位的身份,但这似乎不足以成为事业单位监管规制科研人员进行基因编辑的理由,更何况,并不是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具有开展基因编辑的能力。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社会服务组织”。那是否私法人就无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追逐个人利益呢。《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