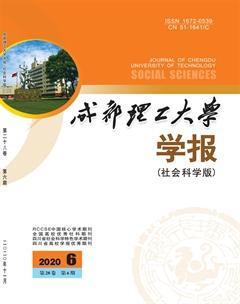论康拉德在《吉姆爷》中的空间建构
邵莹莹
摘要:《吉姆爷》以其对人性、道德的批判和独特的叙述手法受到广大评论家的关注,被认为是康拉德的杰作之一。运用空间理论探讨《吉姆爷》中空间建构的方式及其意义发现,康拉德借助多线索并置叙事、多声部叙事与印象主义手法在文本中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形式,又通过对地理空间、个体的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层的调用,在小说中创造了大量的空间隐喻,既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提升了作品的社会内涵和主题深度。
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空间
中图分类号:1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6-0075-06
一、引言
康拉德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的一流作家,单凭《吉姆爷》就可流芳百世,理查德·柯尔称:“毋庸置疑,康拉德作为小说家的名声主要是靠《吉姆爷》这部小说建立起来的。”故事中“帕特纳号”即将要沉没时,主人公吉姆看到一些官员不顾乘客的性命拼命地抢夺有限的救生艇,十分鄙夷,但是关键时刻他自己也本能地跳了船,为了躲避舆论他在马洛的帮助下去了东方的原始森林,最终害死了酋长的儿子,也酿成了自己的悲剧。自从一位评论家把小说里的故事描绘成真实事件,说“帕特纳号”邮船真的沉了,只有几个人死里逃生,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这本书的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主要从道德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叙事学、精神分析等角度去阐释,但较少人从空问的角度深入地剖析《吉姆爷》,因此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探析康拉德在小说中的空间建构,一是从叙事手段角度分析文本形式空间的构造,另外从地理空问、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方面探讨了小说的空间隐喻。
18世纪,莱辛在《拉奥孔》中指出,小说因语言媒介的因素具有时间性特征。到了20世纪初,一些作家开始打破以时间为顺序的线性叙事,作品中呈现出空间化趋势,对小说这一文类的叙事形式进行了革新。1945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首次提出“空问形式”的概念。他认为:“在我们所指的小说空问化的形式中,就场景的持续时问来说,至少叙事文的时间流被中止了:在有限的时间域内,注意力被固定在各种关联的相互作用中。这些关联在叙事文的进展中被独立地并置着;该场景的全部意义仅仅由各意义单位自身的联系所赋予”。现代小说通常采用特殊的叙事手法来摒弃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读者需发挥主观想象才可以把握故事脉络。弗兰克的论述对之后的空问理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在他的著作《空间的生产》提出“社会空问”的概念,他认为空问与社会生产密不可分,“(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一概念表明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在弗兰克、列斐伏尔等学者的空间理论的关照下来探析康拉德在《吉姆爷》中的空间建构,以期为解读该文本新启发。
二、外在形式:叙事的艺术
作为“‘形式和方法的创新者”,康拉德在继承英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打破了小说的时间叙事传统,通过多线索并置、多声部叙事和印象主义手法淡化时间流和促进读者心理感知效应,因此小说中产生了空间化的现象。《吉姆爷》作为康拉德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追求。
(一)多线索并置
自“空间形式”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不断对这个概念进行补充和延伸。埃里克·s.雷比肯将文本实现空间形式的方法从并置手段转移到情节和叙事上,他认为“一个叙述不但使它所反映的事物陌生化了,而且引导读者意识到了阅读时问和实际时间之前的对应的韵律。……这些韵律就能调整我们的意识活动,结果,依靠特殊的技巧,至少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或多或少地接近共时性”,这种共时性体现的就是一种空间性。作为最突出展示康拉德多样化叙事手段的作品《吉姆爷》中,多线索并置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产生了丰富的空间形式,因为面对多条并置的故事线索,“迫使读者应对同时发生的各种行动,因而它们侵蚀了时间的发展,并以一个比较静止的统一体取代了这种发展”。首先,吉姆与马洛的关系是贯穿康拉德复杂性叙事中的主线。马洛从一开始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密切关注着马洛,对于其跳船的动机发出持续的追问。尽管马洛作为叙事者和小说主角的双重身份使他讲的故事显得错综复杂,但是在小说主题部分仍然不可忽略较单纯的成分,即马洛与吉姆之间的友谊。同时,康拉德还运用了并置艺术中划分的异类并置(人物、事件彼此对立),在故事主线之内夹杂了不易察觉的双重线索,那就是吉姆和马洛作为两个成长人物的故事,“即年轻主人公的探求和他经验丰富的指导者都经历了变化”。一个是开始十分有信心、最后对吉姆的逝去或者说对集体共同信仰的逝去都发出了哀叹的马洛,而另一个是在不切实际的虚幻理想与现实社会冲突中走向灭亡的吉姆。更重要的是,几条故事线索彼此对立、交织,在不同人物、事件、主题的相互对照中呈现出空间化的效果。此外,文中各种复杂的叙事手法打破了线性叙事进程,如倒叙、转述、多角度叙述,使几条线索同时发展,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就需要读者细读、重读小说去把握理清故事脉络,虽然这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对细节审慎的注意过程中读者已经失去了和时间的联系,沉浸到空间意识中。
(二)多声部叙事
讨论康拉德的叙述技巧免不了对其作品中叙述声音的关注。在《吉姆爷》中,不断切换、此起彼伏的叙述声音构成了康拉德不确定叙事的要素之一,同时这个要素本身又直接导致了文本空间形式的产生。小说中主要有三种叙事视角,包括全知全能叙述者、马洛叙事以及其他角色叙事。首先,全知叙事者描述了吉姆受流行文学的影响而渴望成为英雄,但他从未真正“经受过海上那些大风大浪的考验……那些考验能说明他的抵御能力并揭示他伪装背后的真实面目”,可以说第三人称叙述者客观而富有洞察力的描述给读者留下强烈的第一印象,读者可能因此想象吉姆的缺陷而带来的毁灭性事件。然而,从第五章开始,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权威性很快因马洛的叙事而受到质疑,读者的第一印象也随之被推翻,从他们对吉姆外貌描写的不同便可分辨。全知叙述者眼中的吉姆是个普通的在水上兜生意的人,“他差个一两英寸不到六英尺”,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自负”样子;马洛却认为吉姆“简直是阳光沐浴过的最有希望的小青年了”,“他在外表上是那种典型的给人良好印象的傻瓜”。两种不同的声音让吉姆的形象变得模糊、不确定,读者陷入迷惑不解中。尽管有评论家声称马洛角色的安排让吉姆的故事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区分开来,使其更具真实性,但是另一方面马洛的叙事声音使康拉德不确定叙事特色达到顶峰,“全知叙事曾带给读者的清楚、确定感被完全摧毁”。马洛常常提问一些他自己也无法解答的问题,看不明白“雾”中的吉姆,对吉姆的評判也只是他的主观想法或者复述其他人的看法,不具备传统全知叙述者叙事的确定性。因此全知叙事者的可靠性遭到质疑,马洛叙事的可信度尚未确定,而夹杂的其他声音更加使读者疑团满腹,比如当吉姆的审判成定局,吊销其航海证书时,就有数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切斯特认为吉姆的人生完了;斯坦利同情吉姆的处境;朱厄尔十分赞赏吉姆的为人处事;马洛则声称吉姆只是我们当中普通的一员;而吉姆本人则自认倒霉,碰上不幸的事。可见,众多叙述者声音相互博弈,众说纷纭,貌似一场“国际论坛”,读者在不同的叙述声音之间驰骋,再加上读者的联想和猜测,这些因素共同汇成一股自由穿梭、游动不止的意识流,空间性在读者脑海中呈现。
(三)印象主义手法
康拉德致力于追求革新的艺术表达形式,而强调瞬间印象的印象派画风给予了康拉德创作灵感,他认为小说也“应该是一个通过感官的印象”,不再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而是注重感官印象去再现人及其经验。在康拉德看来,“对印象的生动表现要比对平凡事物的客观再现更富于动力感,它的效果更像是未加工过的感觉,像是原始状态的心理体验材料”,因此在阅读具有印象主義元素的作品时,读者体验的是叙述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要获得客观事物的真相则必须拼凑各种零碎的、主观的印象,直至事物的真实面貌浮出水面。伊安·瓦特曾用一个词来描述印象派手法的特点,即“延迟解码”,它指的是作者通过延迟解码,以此“展现一种感觉印象但不给予命名或待后来再做解释,这样把我们先直接带人观察者正在感知这一时刻的意识,然后才揭示这种意识的原因”。对于暂时难以理解的事件和印象,延迟解码这个概念会起到帮助作用。小说中关于吉姆的直接描述并不多,但全知叙述者在第一章介绍吉姆的家庭背景和接受训练的信息很关键。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在道德修养方面应该深受熏陶,而且他在“远洋商船队指挥员训练舰”上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精英教育的环境下,吉姆“头脑清醒,体魄健壮,精明出众”,这些简单的背景信息通常暂时不能被理解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被忽略,但是当读者把前后文各种碎片化的印象进行分析、比较和整合后,就会发现这些背景信息和后文吉姆跳船事件产生鲜明对比,慢慢地可以明白在全知叙述者的描述中吉姆给人的第一印象事实上使吉姆后来的跳船行为显得始料不及和令人唏嘘,强调了吉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且使读者对吉姆为自己辩解更加地怀疑。因此,对于感官印象化的事物,人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心理反应,理解其中的含义存在延迟,但是人的意识是阐释意义的重要因素,在意识的空间网络中拼凑、粘贴印象化的描写才可以掌握事物隐藏的意义。
总之,康拉德的叙事比传统的叙事模式更复杂、多变,弱化了时问标志语,淡化了故事情节,展示不同叙述者对同一人物的不同叙说和阐释。毫无疑问,这样的叙事凸显了叙事的空间效果,叙事结构实现空间化,这对于康拉德来说更有利于塑造他笔下那些性格矛盾、褒贬不一的人物,也更有利于揭示现代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心理。另外,康拉德还运用类似于印象主义绘画的创作方法去描绘人物,小说的立体空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更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空间形式。
三、内在隐喻:帝国空问与反帝国空问
康拉德不仅重视空间形式的生成,而且也在作品中调用了许多的空间隐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外殖民掠夺,殖民地遍布各个大陆,欧洲版图得到充实,同时也将数百万的非洲人和亚洲人置于死地。令人惊讶的是,除了那些歌颂帝国主义的作家之外,大多数作家对帝国暴行沉默不语,而康拉德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这或许和他的波兰身份有关,同样遭遇祖国被帝国瓜分的经历让他能较客观地审视欧洲帝国主义,从作品中反思和反抗现存的帝国统治秩序。
(一)地理空间
二十多年的水手生活让康拉德对大海有特殊的眷念之情,在作品中广涉这一题材使他素来有“海洋作家”的称号,而他本人则非常排斥这个标签,或许海洋对于康拉德来说并非停留于经验层面上的认识,而是包含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大海对于康拉德来说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空间,即想象空间和意识形态的空问,它既是“堕落的浪漫语言和白日梦、叙事商品和‘轻文学的纯粹干扰空间……它本身也是一个工作场所,也是帝国资本主义把分散的滩头阵地和前哨阵地聚集在一起的要素,通过这个要素,帝国资本主义慢慢实现了对全球前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渗透。”海洋既是吉姆实现堂吉诃德式理想的舞台,也是大不列颠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场所。船舶空间作为海洋空间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大英帝国话语建构的过程。吉姆最初就是在东方各港口靠给轮船货商拉生意为生,“他的工作是,只要有船要进港停锚,就跟其他同行比着从船帆、蒸汽、木浆底下跑过去,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同船长打招呼……”海洋已经不再是静态的空间,而是由人和社群组织形成的社会空间。事实上,通过船舶运输实现跨国别资源流通,从而扩大了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实现对殖民地的管辖。因此,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从事或冒险或征服的海洋空问参与了大不列颠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人类空问实践的场所。
《吉姆爷》不仅体现了康拉德潜意识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同时也反映了康拉德在亲身经历殖民行径后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在故事的第二部分中,小说的地理空间转移到了原始森林。在西方人眼中,远在帝国中心边缘的东方世界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而在康拉德笔下,这些景观都被赋予了不可知的神秘色彩,充满了冷漠与敌意。当吉姆沿着一条河初入帕图森时,一群猴“在他路过时侮辱般地喧嚣着”;那晚的月光“像一个精灵从坟墓中升腾出来”;屋子周围的河边“成了一排拥挤、模糊、灰色、银色的形状,混杂在团团黑影当中,就像一群幽灵似的形状飘忽不定的生物”。这些独特的修辞策略正是康拉德刻意为之,通过借助热带丛林的空问表征,被西方话语贬低的东方世界部分地恢复了它神秘的魅力,正如张德明教授所说,“反帝国的空间表征采用的第一种手段是将叙事语境神秘化和再魅化”,再魅化突显了东方世界本身蕴藏的反殖民和反剥夺的原始力量。由此看来,在这帝国反帝国的空间的表征中已经预示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走向,同时也反映了康拉德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怀疑和否定。
(二)心理空间
康拉德所使用的空问隐喻也体现于人物的心理空间这一维度。列斐伏尔认为,“心理空间是人的思想的空间,它是能够被文学和文本、话语和语言等解码的‘加密现实”,而康拉德非常擅长于深刻而细腻地刻画人物心理,《吉姆爷》也被称为“是一部心理分析学说尚未出现前的心理分析小说”。虽然康拉德对吉姆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但是仍然可以从文中构建吉姆多维、立体的心理世界。海上生活和流行文学的阅读滋生了他浪漫主义的英雄梦,不断幻想着自己与大海搏斗、与原始部落斗争、英雄般地激励和拯救处于绝望中的人们……然而吉姆虚幻的浪漫主义梦想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理想化身,建立在不具可行性西方理想上的观念不仅导致吉姆失去了自我,也因不可能的至高理想使自身的存在变得虚幻。而且每次当他没有做出符合理想标准的行为时,便把责任推给外界并重新坚定地声明自己具备英雄般的道德与气魄,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便能向全世界证明他能够达到西方理想的标准,这样吉姆牢固地建构起虚假空间,孤独感加深,并且伴随吉姆进入帕图森直至死亡。
刚进入帕图森,当地人对吉姆十分谨慎和害怕,但是当吉姆帮助多拉明战胜另一派势力,解决当地长期的纷争和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吉姆爷,从那之后吉姆的每句话都被奉为金科玉律,可以说,远在西方世界另一端人们的认可和信赖契合了吉姆原本的幻想空间,同时也使其更加封闭。与此同时,吉姆作为外来白人,其自身神秘的特性难以被当地人解读,并且来自西方国家的优越感也不可能使吉姆真正和帕图森融合。即使是吉姆的妻子珠儿也难以走进吉姆的心中,总是被巨大的恐惧感包围,吉姆对于他们来说始终像个“谜”一样,而吉姆本身也从未真正接纳他的妻子包括当地的一切,原始森林对他来说只是实现其权力统治的场所,最终因无视和误读现实的帕图森造成悲剧。这点从戒指也可以看出,把象征着当地图腾力量的戒指误以为是他开启统治帕图森的钥匙,沉浸于自己幻想世界的吉姆对环境氛围的模糊不清和空间的不断切换,使其不能阅读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从而陷入隔离、痛苦的幻想世界,最终走向死亡。
(三)社会空间
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离不开社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将《吉姆爷》放置在历史长流中会发现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比欧洲帝国主义更颠覆性地重塑了这个世界。从头顶悬挂的煤气灯,到不断扩建的铁路网和结束风帆时代的蒸汽船等,这些代表社会转型的符号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城市空间的剧烈重组。然而正是殖民扩张的力量加速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开拓了广阔的地理空间,推动全球资本流通,从而形成帝国势力以欧洲为中心向其他大陆发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F.R.詹姆逊说:“除了爱尔兰文学和乔伊斯作品的特殊情况外,我们都可以在空间上窥见帝国主义的踪迹,它们作为形式症候存在于第一世界现代主义文本自身的结构内部。”《吉姆爷》中康拉德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昭然若揭,吉姆试图开发帕图森,开垦土地,开辟咖啡园,将其完全打造为另一个西方附属的殖民地,他以主人翁的眼光看待那里的一切,满怀自信地决定在那里待下去,以为能躲避之前的丑闻,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当在法庭上接受帕特纳号事件的审判之后,吉姆就想法设法离开舆论的是非之地,他“转到另一个码头,一般是越走越往东……有人相继在孟买、加尔各答、仰光、槟榔屿、巴达维亚见过他”,但是吉姆逃跑的速度仍然赶不上消息传播的速度。这归因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其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压缩了空间上的距离,改变了人们的感知和生活方式,于是人们感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吉姆找不到藏身之处,被赶人了原始森林。带着全球市场的空问逻辑,吉姆进入帕图森,试图将其纳入全球市场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殖民化、市场化、全球化已然将个人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全球性空间中,中世纪的英雄罗曼司显然难以成立。可以说,康拉德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诉说了新型社会空间对个体的压抑,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帝国统治秩序的质疑和挑战。
四、结语
作为康拉德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說,《吉姆爷》通过丰富的空间形式和空间隐喻实现了小说的空间建构。在空间形式方面,康拉德通过复杂多样的叙事手法创造了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表现了文本内涵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其次通过康拉德擅长的印象主义手法赋予小说如绘画般的想象空间;在空间隐喻方面,康拉德通过帝国反帝国的空问表征斥责了虚伪的帝国主义行径,而在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问角度,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扩张生产出来的新型社会空间中个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和英雄梦的虚幻,地理、心理和社会三维立体的空间隐喻在小说中铺陈开来。总之,康拉德在《吉姆爷》中对空间层面的关注不仅拓展了文学表现形式,而且提升了主题深度和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