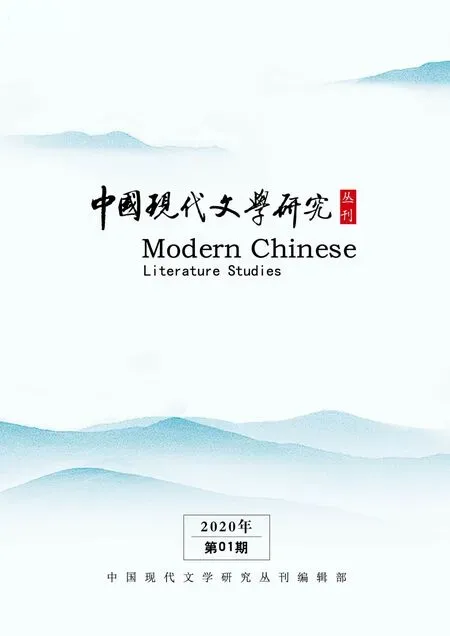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台湾自然书写
内容提要:台湾自然书写自1970年代末发端至今,涌现出一批女性书写者,她们不以感性的私语抒悲遣怀,而是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公民姿态,表现出清晰可辨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显示女性书写由“私人领地”向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拓。本文梳理几位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者的创作流变,认为1980年代后期,是台湾生态女性主义创作的转型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创作文体由“社会批评”式报导文学,转向审美意味的“女性智性书写”;二是书写对象由“荒野写作”走向“生活的自然”;三是由“二元对立”社会批判转变为鲜明女性特色的“还魅式书写”。
“现代自然书写”(modern nature writing)是社会现代化的直接产物,它在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大背景下,经由生物学、生态学、土地伦理学等多门交叉学科融合互渗,从传统博物学出发,糅合丰富自然科学知识、伦理自省、文学抒情,呈现出丰富的创作面向。台湾自然书写发端于1970年代末,台湾学者认为其有几个主要特质:强调人与自然互动的非虚构、自然知识符码的运用、以个人叙述为主(personal narrative)。1990年代后,台湾自然书写臻趋成熟,为“解严”后台湾文学注入新活力,反映台湾作家对土地和生存现状的集体焦虑,以及对“人地关系”的深沉思考。台湾自然书写发展历程中,女性作家是持续在场的主力军,她们从闺秀文学中走出,以性别介入自然,凭借女性与自然的天然亲密,书写台湾的山川河流,与台湾经济社会的变化互文,也呼应了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一 从“社会批评”派报导文学到“女性智性书写”
“生态女性主义”概念,最早源于法国女性主义学者佛朗索瓦·德奥博娜(Francoise d’Eaubonne)在1974年发表的《女性主义或死亡》(Feminism or Death)。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思想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破坏力,时刻压抑女性,也时刻与自然为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来自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也正是这样的世界观确立了统治妇女的合法地位。”①统治自然与统治女性是孪生政治。女性是大自然最义不容辞的代言者,反对男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既是对现代性的反拨与批判,也内含“重返自然”的“反启蒙”色彩。
台湾自然书写发端于1970年代末,彼时台湾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计划”,从1974到1979年先后开展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工业化飞速运转,现代化弊病却越发显露,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介入环境问题。当时尚处“戒严”,政治环境严苛,焦心社会现状的作家无法直接触碰敏感的政治、社会话题,于是绕道“绿色小径”,呼唤大众对生存空间的关注。与此同时,伴随妇女社会解放运动,台湾女性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极大提高,“新女性主义”出现,女性作家创作维度日趋多元。徐如林、韩韩、马以工、心岱等女性自然书写先驱者崭露头角。
1978年徐如林出版的《孤鹰行》,被视为台湾女性自然书写先驱作品之一,书中呈现作者大学四年的历程,表现对山林的醇厚感情与赤子热忱。作者与自然进行灵与肉的接触,充满对自然的尊重和理解,以女性的细腻,丝丝入扣地描绘女性与自然亲密无间的互动。
1981年韩韩、马以工在《联合报·副刊》“自然环境的关怀与参与”专栏发表系列文章,就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勇敢发声。1983年,这些“报导文学”集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出版,得到学者的广泛肯定,“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韩韩、马以工合著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以降,以作者的人文体验书写关乎于自然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自然写作’”②;“开启了‘自然书写’在台湾文化与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序幕”③,“此书的问世,被认为是台湾‘环保文学’的滥觞”④。该书揭露台湾当时触目惊心的自然状况,如淡水红树林被大规模铲平、东北角天然海蚀平台被开挖成九孔螺养殖池;垦丁红尾伯劳鸟惨遭大量捕杀等。
1978年开始创作报导文学的女作家心岱,是两届“时报文学奖”得主,她用耐心和胆识一次次挑战严肃的环境议题,足迹踏遍宝岛,用锐利视角如实记录恶化的环境。1983年,她的《大地反扑》出版,以报导文学形式,揭露台湾千疮百孔的生态状况,抨击人类对大自然不知餍足,其中涉及发电厂肥料随意排放对海岸的污染、台湾南部恒春半岛的环境变迁、宜兰哈盆地区的植物等,具有突出的现场感。
面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论,“女性与自然”是共同受到剥削的一体两面。对天然宰制力量的批判,既是台湾自然书写初期女性作家对周遭现实的敏锐洞察,也源自女性潜意识中对弱者的关注。以上几位女作家以细腻的观察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充分发挥报导文学的及时性,加之报刊媒体的宣传造势,成为当时启蒙民众的环保读物。她们创作的一系列自然书写文本,如《在我们的土地上,观鸟》《玉山国家公园》《寻找老台湾》《自然之美》等,不仅收获了大量读者,更充分发挥了文学对社会的作用。由此台湾环保运动开始持续发热,出现一些反公害组织和环保团体。但是,由于报导式书写对自然知识的欠缺及对环境问题成因的认识不深,笔调往往热情有余,文学性不足。就作家自身而言,她们当时尚未产生鲜明的性别意识,创作出将性别特征与生态伦理恰切结合的文本。
1980年代中期,台湾女作家的自然书写转向深沉反思,建立起较专业的自然知识体系,创作形态也由性别模糊的即时性报导文学,转向富有女性审美的智性书写。吸收欧美系统化的生态理论后,她们用行脚丈量岛屿,写出具有鲜明在地性(localization)的文本。洪素丽、凌拂、杜虹是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走向成熟后较具代表的几位。她们的观察对象和文风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与男性自然书写迥异的新面貌。女性轻盈绵密的情感,冲淡了男性书写者理性过浓的弊端。更值得称道的是,她们虽以情感穿透景物,却不用以“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审视自然,她们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态度,引自然为知己的生活方式,一览无余地展现了“自然”与“女性”的密切关系。
洪素丽兼具专业作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她的国际视野和本土观点,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社会文化内涵。洪素丽虽然长期旅居美国,但始终将关切目光投注在故乡台湾,称自己为“大地永远的行旅者,远方永远的愁乡人”⑤。在各国游走时,她始终体会“他者”身份的隔膜,但也带来清醒反思,使她善于通过观察域外生态环境,反身观照台湾本土,察人所未见,唤起台湾百姓的共鸣。她的文字摆脱了女性作家闺秀气浓重的弊病,行文颇具清丽智性的色彩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文章结构严谨且逻辑严密。
与男性自然书写者相比,女性作家将细致情感融入自然,造成“一切景语皆情语”审美体验,尤其擅长用古典文学的词句和意象,阐发对自然的体悟。杜虹的《山海满洲》《定风波》《登高送别》等,将人生况味、四季景物、古文用典融于一体,具有独特文体美感。2019年,新作家伊丝塔的《飞羽集》是第18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得奖作品。全书以鸟羽为线,以女性口吻的第二人称叙述,从拾羽、集羽到走访鸟径、书写鸟羽,带出女性个人成长生活史。散文与鸟羽、女性自我、大地母亲的对话,层次丰富,体现出清醒的女性文体意识。
二 从“荒野写作”走向“生活的自然”
从“荒野写作”走向“生活的自然”,是台湾女性生态主义书写转型在内容上的拓展。比如,洪素丽的创作转型,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洪素丽的创作,贯穿台湾自然书写发展各个时期,也反映了自然书写由“荒野”向“生活”过渡的趋势。她积极投身环保运动,参加美国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奥杜邦学会”,详细学习鸟类知识,研修海岸生物课程,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1986年出版的《守望的鱼》,她以“一个河口海湾忠实的守护者”自居,野外观鸟时,毫无畏惧深入野地,与男性无异地经受严酷环境考验。洪素丽不仅以女性细腻视角记录观鸟点滴,也开始有意识探讨人地关系,寻求人类在自然界立足的支点。
进入21世纪,洪素丽的自然书写呈现新变,情感由急促尖锐转为和缓隽永,此前“请大家救救海岸线!”式大声疾呼已不见,焦灼与急迫的使命感转为耐人回味的文字。她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日常生活的鉴赏者”,观察点由遥远的野地,转为城市周遭“小环境”,通过描摹日常生活习见的自然场景,打开自然书写生活化新局面,一改以往拒斥都市、归园田居的文学态度,《金合欢》《银合欢》等作品,将台湾城市习见的动植物与环环相扣的家族故事相连。洪素丽从全然否定现代化城市文明到“大隐隐于世”的默认、积极寻求解决路径,以人文姿态自然导览者形象,启发读者与自然相处不需要费力地翻山越岭,应秉持自然之心与城市中的动植物为邻,用力所能及之道缓解现代都市人的“自然乡愁”,随后的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者,越来越显示出由荒野走向城市的特点。
有别于洪素丽从“荒野”到“生活自然”的转型,凌拂一开始就强调在生活中发现自然、与自然交流,突破自然书写强调的专业观察,建立“生活型”自然书写形态,加之她笔触轻盈、情感饱满的特质,大大提升了自然书写的审美品质。被称为“自然生活家”的凌拂,善于通过采集身边习见的植物认识脚下的自然与土地,即便观察动物,她也选择隐身家屋窗后,而非主动寻找。凌拂将“都市家居的窗口”当作一只隐藏的眼睛,在寂静里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生物。飞过窗前的普通鸟类、偶尔在屋后出现的动物、流浪的山狗、闯进家中的蛇等,几乎涵盖了她笔下所有写作的动物对象。
对凌拂而言,自然观察是如吃饭饮水般随意的事,如泥与水相拌,鼻息耳目无不浸润其中,例如《斯文豪氏蛙》中,她以家屋窗口为视点,安静平和地仔细观察:“山夜深而且黑,窗外是寂静、空旷的世界,宁静而朴素的夜晚,除非想啜一片冰凉的月光,或者饮一饮清凉的野风……临窗伏在案头,总觉有事。只隔一道玻璃,鸟鸣不断。”柔美的行文外,也不乏自然观察的科学质素:“斯文豪氏蛙隐密、害羞,不易被发现,喜欢栖息在溪谷、山涧或小瀑布等水边。白天单独躲在岩穴或涧中鸣叫;晚上单独出现在洞口或溪石悄然觅食。”⑥田野小径、野溪浅壑皆为凌拂文字的生长之处,她每每别出新意,以女性的细腻视角辅以现代自然书写者的科学素养,激荡出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除了洪素丽与凌拂,1990年代初,很多台湾女性生态主义作家,都表现出对“生活自然”的理解与表达。从文化背景而言,90年代受西方“生态旅游”(ecotourism)概念影响,台湾出现综合资讯型旅行导览手册,人们“消费自然”方式发生改变,从采集、利用、消耗变为观察、参与、共生。自然书写范围随之拉近,一些自然导览性质文本出现,如陈月霞的《大地有情:台湾植物的四季》,杜虹的《相遇在风的海角——阿朗一古道行旅》,谢桂祯、许裕苗的《台东绿色林径游:台东林区自然布道导览》等,均聚焦城市与自然的重叠处,为现代城市人提供绿色向导。
三 “还魅”的文学:台湾女性自然书写的新生态伦理
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之手,颠覆了手工业时代的人地关系,人与自然长期处于疏离与对立。被启蒙理性“祛魅”后的世界,生命的神圣、宇宙的神秘以及世界本源的魅惑,褪去了神秘面纱,在“生产力即强权”观念影响下,女性与自然都统摄于绝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者构建的正是现代性与自然世界间的通道,以“还魅”的独特书写方式,唤回自然灵性,打破人与自然鲜明的主客分界。
在洪素丽与凌拂等台湾女性的自然书写者笔下,科学与文学、理性与感性相互交融,体现了超越二元论的创作意识。科学不再是温度全无的纯理性思维,文学也不仅表现为纯粹感性抒发,二者不再截然对立,而是并行互启。科学的发现让人们更加理解自然的形貌与运作,文学则以审美的态度、诗化的言说,表现出自然的诗意与美感。大自然从客体对象,转化为意识的主体,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文学长期以来对“自然”本体的遮蔽。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不是主客二分的截然对立,正如伍尔夫所言:“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两种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⑦
凌拂擅以细小习见的植物为观察对象,花草在她纤柔的笔触下达到微观的审美层次,明显区别于男性自然书写者偏好的大物体、大现象选题,展现出女性观察者独到的视角。1996年的《食野之苹:台湾野菜图谱》,以作者任教的国小附近山水为范畴,详尽记录了与各色野植相伴的生活片断,组成一篇篇况味十足的文章,印证了“自然无处不在,观察随处可行”的生态观念,配上作者细致的手绘插图和知识旁注,以“说文解草”的方式,将花草小事认真对待,使文本具有值得反复吟咏、翻看的韵味。虽然凌拂的作品通常没有高密度的生物知识或严肃的生态伦理,但她着墨于天地方圆中偶遇的生命,对它们怀着熟稔于心的亲切感,形成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互不干扰美学”。同时,古典文学滋养着凌拂的文字,构成她自然书写的鲜明特色,即使描写眼前植物,也往往能发掘言近而旨远的意境:“面对恒常来说,红桧的世纪浩远幽邈我无意憬悉,然而菌菇的游丝我亦未见得就守得住它的瞬息。恒常无法掌握,短暂易于流失。”⑧不论用典、修辞或况味,都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古朴禅意,古籍诗词不仅给予了凌拂朴拙的生活方式,还直接影响了走笔行文。她行笔从容自然,笔触含情脉脉,极度感性却不失于滥情,经过细致的自然观察后,淬炼出女性的柔性观点和细腻文风。
具有垦丁国家公园保育研究员身份的杜虹,与其他女性自然书写者相比,专业性和专注性显著,其作品多以特定地域自然环境为题材,包含丰富自然元素。《比南方更南》《有风走过》《秋天的垦丁》等文集,深耕台湾恒春半岛,由生态保育工作延伸至书写自然。杜虹虽然是生态研究科班出身,但作品没有说教,甚至超越科学、理性论述,和缓地引领读者走进自然。
可以说,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者的创作流变,无论应对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女性主义创作形态,还是将之放在更广阔的华文文学创作领域之中,都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创新力。这些生态女性主义写作者,由传统“私人领地”不断向现代“公共空间”的跨越,她们抛却传统女性文学的刻板印象,使用知性文字参与社会议题,发挥女性性别优势,越发显示出源自女性而超越性别的智性特征,因而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她们的未来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