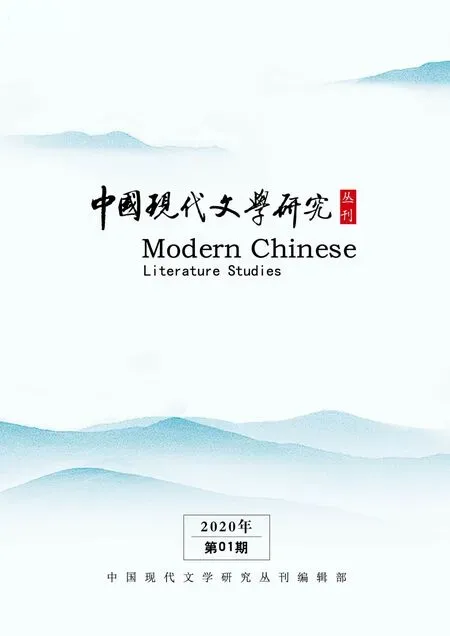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语怪小说”中的政治寓言
——梁启超译《俄皇宫中之人鬼》的意义
内容提要:梁启超经由德富芦花《冬宫の怪談》(1898)重译的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1902),原为英国作家Allen Upward的短篇小说“The Ghost of the Winter Palace”(1896)。在翻译中,德富芦花拆解原作双重第一人称叙述结构,并大量省译;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改写和发挥,建构了“语怪”背后的政治寓言,虽述俄宫1894年之事,实际投射戊戌之后的晚清中国。还原文本旅行中的文化坐标,在小说跨语际之旅中,可以展开对晚清中国翻译文本、思想转型和政治理念的探讨。作为1902年的“政治寓言”,小说在历史回望中对专制制度的反思,也成为呼唤未来的一种力量。
超观曾提到“任公闲时爱谈鬼,但从未究其理,述时必津津有余味焉,屡言得闲当写一文,记其与鬼交涉之经过”。虽此文“始终未果写”①,但梁启超对于鬼的兴味,在其涉足新小说创译之初即有体现。言说鬼神看似和现实无关,而梁氏借助一则异域故事,在翻译的同时,书写了切合国是的政治寓言。
1902年12月,《新小说》第2号刊出一篇署名“曼殊室主人译”的短篇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标为“语怪小说”②。“曼殊室主人”即梁启超③。译文开篇交代“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而其底本实为德富芦花(1868~1927)所译《冬宫の怪談》(1898)④;日译本的底本,则是英国作家Allen Upward(1863~1926)所著Secrets of the Courts of Europe(1896)中的短篇小说“The Ghost of the Winter Palace”⑤。小说刊出前,《新民丛报》曾发布预告:“短篇小说有《俄皇宫中之人鬼》一篇,系法国著名小说家所作。详言俄皇外以尊荣,内实穷蹙,其苦有过于寻常人万万者。至其结构之奇,实非思议所及,今未便先说出。”⑥梁启超误以为作者是法国人,实际是德富芦花删改原作后,梁氏将故事的叙述者当成了作者(详见下文)。梁译《俄皇宫中之人鬼》1904年被《萃新报》转载⑦;1905年收入《说部腋》⑧,1916年收入《小说零简》⑨,1936年收入《饮冰室合集》⑩。译作本为文言,发表后还被《杭州白话报》⑪和《童子世界》⑫分别改写成白话演说体。
《俄皇宫中之人鬼》是梁译小说中目前研究最少、也最为扑朔迷离的一篇。邹振环曾指出其“短篇政治寓言小说”的性质,然仍有可讨论的空间⑬。同是1902年的“政治寓言”,《俄皇宫中之人鬼》表现了与《新中国未来记》不同的面向,体现出梁启超文学书写中的另一种思考;由其英文—日文—中文的跨语际之旅,可以展开对晚清中国翻译文本、思想转型和政治理念的探讨。
一 作为“语怪小说”的《俄皇宫中之人鬼》
梁启超对《俄皇宫中之人鬼》的分类是“语怪小说”。据考察,在晚清有标示的1075篇小说归类成的202种名目中,“语怪小说”仅此一篇⑭。1902年《新小说》发刊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列有“语怪小说”一类:“妖怪学为哲理之一科,好学深思之士,喜研究焉。西人谈空说有之书,汗牛充栋,几等中国,取其尤新奇可诧者译之,亦研究魂学之一助也。”⑮按此说明,翻译“新奇可诧”的“西人之书”,以助于研究魂学,是设此名类的目的。“妖怪学”源自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妖怪学者,论究妖怪之原理,而说明其现象者也”⑯,即关于“妖怪”现象的心理、哲学、生物学等因素的研究。此后,《新小说》所刊《小说丛话》亦提及“语怪小说”:“中国人之好鬼神,殆其天性,故语怪小说,势力每居优胜。如荒诞无稽之《封神榜》,语其文,无足取也;征其义,又无足取也”⑰,对古代神怪小说持批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强调“西人之书”,以之区别古代志怪小说,此“语怪”不同于《山海经》的巫术神话,而是晚清一种舶来品。因题材与侦探、外交小说相关,也有论者将《俄皇宫中之人鬼》归为外交侦探小说⑱。《新小说》设有“探侦小说”一类,“其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本报更博采西国最新奇之本而译之”19。不过,虽“语怪小说”“探侦小说”都言说西书之“新奇”,但落脚点实有差异。在“谈空说有”和“新奇可诧”之外,梁启超在翻译中还有更深的思考。
《俄皇宫中之人鬼》以一名卸任后尚未归国的法国驻俄公使(译文中“余”)之见闻,记述了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冬宫的一段故事。余“有一知己,为尼士智伋公爵夫人(Princess Nestikoff),其子名波里斯(Prince Boris),为皇帝近侍,现正服职冬宫”。波里斯告“余”前夜值守时,见“一颀然硕大之人影,以白布覆面,正循树阴,向前面屋角潜行而东”,以为是虚无党,仓皇失措之时,“有一怪体突走空廊”,正是“身死未寒,举国官吏为之服丧之前皇亚历山大第三”,遂有冬宫闹鬼之说。“余”约其夜半同往,发现确为亚历山大三世,而由其解释,他实为在政治压力下“佯死以掩天下之耳目”。后宫中废空廊之守兵,波里斯外派海参崴,宫中有鬼事“风说遂灭”。
虽有闹鬼—寻鬼—见鬼—释鬼的情节,小说叙述层层铺陈,环环相扣,但“俄宫人鬼”之事,其实是个虚构的政治故事,而非悬疑秘案。梁启超在“译者识”中已进行解说:
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俄前皇亚历山大第三,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崩于格里迷亚之离宫,旋以庄严之仪式,归葬于圣彼得堡,其谁不知?此文不过著者之寓言耳。虽然,其描写俄廷隐情,外有无限之威权,内受无量之束缚,殆有历历不可掩者。专制君主之苦况,万方同概,岂唯俄皇?译此以为与俄同病者吊云尔。⑳
此系在德富芦花基础上㉑翻译改写而成。梁氏自述译此“以为与俄同病者吊”,而“与俄同病者”,在晚清中国不言而喻。以此为基调,梁启超在译文中建构了“语怪”背后的政治寓言。
二 自西徂东的文本旅行
由英国作家Allen Upward的“The Ghost of the Winter Palace”,到日本德富芦花译作《冬宫の怪談》,再到梁启超重译的《俄皇宫中之人鬼》,短短六年间,这篇英国小说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经由德富芦花的译演和梁启超的点染,小说在叙事模式、人物情节上都有变易,且在俄国风情中加入东方色彩。考察文本的生产旅行过程,比较中日译本对原作的改易增删,能够获得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对这篇小说的不同观察和文化互动。
(一)虚实之间:从创作到译演
Allen Upward的小说,题材多关于政治、军事、国际间谍和宫廷秘史,Secrets of the Courts of Europe也不例外。该书副题“一名前公使的秘密”(The Confidence of an Ex-ambassador),包括12篇短篇小说,内容都通过“I”和“the Ambassador”的对话展开。这里“the Ambassador”是个虚构人物,与之对话的“我”也并非作者本人。小说1896年在Pearson’s Magazine连载,根据次年结集本㉒所收报界评论,诸如《名利场》(Vanity Fair)等杂志,都相信“the Ambassador”的真实存在,并对其真实身份展开猜测。关于“the Ambassador”的多维解读,成为德富芦花对小说进行“改造”的前提。在日本侦探小说风行之时,德富芦花翻译了这本书,定名《外交奇谭》,先在《国民新闻》连载,后于1898年结集出版。小说述及欧洲各国政界人物,有真实历史作为参照,又经过Allen Upward和德富芦花的艺术加工,在侦探小说风行的时代,确会引起读者关注。1902~1904年,《外交奇谭》12篇小说分别被梁启超、罗普等译成中文,刊于《新小说》《新民丛报》《外交报》等。德富芦花虽写明原作者,但未标国籍,且将多数篇目中“I”的情节和对话删去,使小说成为“the Ambassador”的独语,因而中译者误以为作者为法国公使,皆注“法国某著”,梁译《俄皇宫中之人鬼》也是如此。于是,这篇虚实掺杂的小说,经由任公的再次加工,带着言说鬼怪、外交侦探、宫廷秘闻、虚无党故事等“时尚”元素,进入晚清中国。
(二)原著与译本:三种文本的比较
英、日、汉语三种文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德富芦花拆解原作双重第一人称叙述形式,并大量省译;梁启超又进行改写和发挥,并留下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1.德富芦花的删削
Allen Upward所著12篇系列小说各有不同场景,包括饮白兰地、吸烟、看报纸、下国际象棋等。小说由“I”用第一人称叙述,但主要故事情节在交谈中由“the Ambassador”讲述,因而各篇除去点烟卷、揉桌布、品酒等动作外,绝大部分都是对话。“the Ambassador”叙事时也用第一人称,一系列小说都是双重第一人称结构,即“I”是小说的串线人物,“the Ambassador”是故事的叙述主体,两个“我”交替出现。“The Ghost of the Winter Palace”设定的场景是两人边下棋边聊天,在讲述俄国故事的同时,穿插着对棋局的讨论。德富芦花翻译时,将“I”和对弈情节删去,整篇小说变成“the Ambassador”的讲述,即将双重第一人称叙述结构拆解,对话模式转为独语,日译本的“余”只对应英文的“the Ambassador”,这就是梁启超以为作者是法国公使的真正原因。比对可见,德富芦花删去42个完整段落,仅小说开头就删去11段,日译本是从英文本第12段开始的。原文由棋局开篇,从棋局类推到政局,“the Ambassador”用一个故事进行阐说——这个故事,就是俄皇宫中之事。在讲述过程中,对弈情节不断插入,不但在紧要关头制造悬念,打破叙事的连续性,同时也避免讲述过于冗长,以二人的互动增加叙事的丰富性。作为小说双重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的潜在线索,对弈将小说分为故事内的俄国怪闻和故事外的棋局进展。德富芦花的删削,使小说叙事结构变得简单。整段删节之外,日译本也不乏改写和重构:
君よ,幸に余を小說家または詩人など云ふ者になりしとばし思ひ謬まり玉ふな。余が今君に語らむとする一條の話は正しき事實にて,露國宮廷の內幕に參する人達は確かに知る所なり。唯其話の殆んど尋常あり得可からざるものあるが故に,君も或は一篇の小說と看倣し去らむことを患ふる耳。㉓
此段系德富芦花添加,原文中并不存在。由于日译本的“余”对应“the Ambassador”,这里又被定为“小说家”,梁启超重译时,就有了“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的误会。在人物、故事的描写上,日译本也有增删:
“It may very well be that this was merely a first visit” ,I added,“a reconnaissance, to discover the nature of the ground, before introducing some explosive machine or other, and the villain may easily have kept himself out of sight for a few minutes. Doubtless he returned immediately, only you had then left the gallery”㉔
兎に角今は實地を試す外なし。若し虛無黨ならむには,今夜宮中の舞踏會を幸ひ,再び忍び入るにぞあらむ。㉕
“虚无党”在英文中并非“the Nihilists”,而是“the villain”(坏蛋)。原文“the Ambassador”并未推测鬼影是虚无党,另一处描述鬼影用的是“the conspirators”(“阴谋者”)。德富芦花的改动,增加了译作虚无党小说的成分。
2.梁启超的改写
相比于德富芦花以删削为主的加工,梁译本在删减字句之外,还做了多处改写。其译本带有“豪杰译”的个人风格,也具“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㉖的特点。
在日译本基础上,梁启超又删减了部分内容。在小说开端,即把关于尼古拉二世的部分删去。这样处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开头过多铺叙,使读者尽快进入故事主题。
梁译本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中国典故改写原文,在翻译的同时,插入自己的言说。这些经由“最富于情感”的梁任公之手的改写和发挥,包括政治评论、环境渲染、对话铺排等,具有“新文体”的鲜明特点,也改变了小说语言风格。例如,述及康士坦丁大公弃位,让与其弟尼古拉一世时,梁氏加了一段评说:“闻焉者骇焉,以为公何高尚乃尔,敝屣富贵乃尔,而乌知夫好逸恶劳、趋安避危,亦犹夫人之恒情。彼其于利害、得失间,审之极熟,不欲耽虚名而受实祸以为高也。”对俄国政史的评点融入译文,成为中译本的特色。
在翻译中,梁启超常多加点染,铺叙发挥。例如写到波里斯独自值夜时,“疏星明灭,树荫婆娑,夜静无人,独立沉郁幽阴之境”,“但见月色分光,夜凉似水,风来叶落,月上阴移,愁惨岑寂之气,竖人毛发”。英文和日文环境描写比较简略,梁氏以传统小说手法详加铺叙,营造了“鬼”出现前的紧张气氛。
此外,梁启超也改写了人物对话,最典型的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自叙:
I could do nothing. I was helpless, a martyr bound to the stake of my autocracy.㉗
余は何事も為す能はず。余は實に吾專制の杭に繫がれたる犧牲なりけるなり。㉘
自皮相者观之,皆以余为君权无限,而不知余为左右所掣肘,无权无力,一事不能办。天下不察,反以余躬为丛怨之府。呜呼!余真无乐乎为君。以堂堂七尺之躯,乃仅为左右之傀儡,其有罪也在余躬,其有危也在余躬。吾尝自哀自讼,不知前世作何恶业,今乃托生为专制君主,历尽人间世不能历之苦况也。㉙
原先简单的两句话,经由任公渲染,极力表现亚历山大三世的怨怼之情。借俄皇之口,梁氏表现的其实是自身情绪——在翻译的同时,书写自己的政治寓言。
三 晚清的政治寓言
以欧洲政史为素材,又经小说笔法演绎的作品,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国都有别样的魅力。在文本背后,梁译小说还有更深的政治寓意。虽名之为“语怪小说”,梁氏却“先与读者约,必毋以读小说之意读兹篇”㉚,正是以此异域故事作为晚清的政治寓言。
(一)虚无党魅影
《俄皇宫中之人鬼》虽在重重悬念以后真相大白——所谓“鬼/怪”是佯死的沙皇,但小说中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鬼影”——虚无党(Nihilists)。梁译本中“虚无党”共出现9次。这“最剧最烈可畏可怖之虚无党”即“民意党”(Narodnaya Volya),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成立于1879年,力主恐怖暗杀,1881年将亚历山大二世炸死。虽然民意党很快瓦解,但20年后,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被介绍到中国,俄国革命风潮与暗杀手段,给了同处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志士极大鼓舞,20世纪初,关于虚无党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论说蜂起,虚无党故事也成为晚清小说一大潮流。“怀炸弹,袖匕首,劫万乘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㉛,描写异域史事、寄寓政治情怀的虚无党小说,带给20世纪初的国人迥异于传统说部的新观感。从外国译本的流行到小说创作的尝试,在政治思潮向文学渗透的背后,有反抗专制的现实诉求,也不乏侦探情节、秘闻逸史的天然吸引力。《俄皇宫中之人鬼》的翻译背景和发表环境,也和这一思潮有关。1901年,梁启超曾专论俄国政情:
以俄国论之,一八〇一年保罗帝被杀,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第二为炸药所毙,而先帝亚历山大第三,自言终日若在幽囚,一夕九迁,曾靡宁息。今皇尼古剌第一当游日本时,亦几不免矣。俄罗斯为地球第一专制之国,其现状若此,无足怪者。㉜
亚历山大三世亦曾被虚无党谋刺,只是未成功。“先帝亚历山大第三,自言终日若在幽囚,一夕九迁,曾靡宁息”即《俄皇宫中之人鬼》的历史依据,可与“译者识”中“外有无限之威权,内受无量之束缚”之俄廷隐情对读。在这一意义上,梁氏的翻译,正体现了其同时期的政治观照。
1902年,《新小说》在刊载《俄皇宫中之人鬼》的同时,还在连载历史小说《东欧女豪杰》㉝。两部作品同是叙述19世纪俄国故事,皆具政治意味。作为虚无党小说创作的早期代表,《东欧女豪杰》开启了国人对俄国女杰形象的接受和想象,而《俄皇宫中之人鬼》所述宫廷秘闻,也成为虚无党小说创作中可资利用的资源。1903年喋血生所著侦探小说《专制虎》即拟其前传,结尾处“后数年,乃有俄宫人鬼事”㉞点明此意。可以说,梁译是作,也为虚无党小说提供了一种方向。
(二)以俄宫事说晚清史
梁译《俄皇宫中之人鬼》言说俄宫1894年之事,却实在投射晚清中国历史。时人注意到小说“述亚历山大第三佯死避位,实著者之寓言耳”,“译此以为与俄同病者吊,亦足以告世之崇拜皇权者”,㉟而“与俄同病者”即指当下的清王朝。1898年9月21日,慈禧宣告训政,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四年后,梁启超仍流寓日本,译述俄国专制君主之苦况,不由生出“对旧日维新变法的怀念”㊱,译笔一转,直以俄宫事说晚清史:
人多以维新改革说吾,若卿者,最熟悉俄国事情者也。卿为我设身处地,余果一从事改革,则彼等太后党、世家党,其有不欲得余而甘心者邪?㊲
梁启超的政治寓言,就在这里。英文本和日译本中,“维新改革”原为“reform/改革”,“太后党、世家党”原是“Nihilists/虚无党”。虽然“改革”前加“维新”语义与“reform”无大差异,但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国,“维新”具有特定含义;而将“虚无党”改为“太后党、世家党”,其政治寓意显露无疑。梁启超将光绪慈禧之事嵌套到遥远的俄国,以亚历山大三世之口,述说戊戌之后的清廷,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以“岁甲午”“光绪二十年”记载俄宫故事的做法。梁氏添加的“以堂堂七尺之躯,乃仅为左右之傀儡”,表面由俄皇言说,实际暗指光绪帝,“余闻焉,心戚戚焉”亦是其本人的内心写照。面对衰颓的晚清帝国,梁启超曾力求变法,然在政治的挫败和个人的颠沛中,唯有用小说“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㊳。梁启超在连载《新中国未来记》的同时,先后翻译了“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㊴和“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如果说《新小说》第1期刊发的《世界末日记》与《新中国未来记》显示了梁启超兼及“末日”与“未来”的思考,第2期的《俄皇宫中之人鬼》则反映了与“未来记”相反的对旧制度的回望。梁氏自言《新中国未来记》“编中寓言,颇费覃思”㊵,而这政治“寓言”,同样可以涵盖借他国之事喻当下之史的《俄皇宫中之人鬼》。同时,在歌颂、鼓吹理想未来的同时,“译此以为与俄同病者吊”,也点明晚清积重难返的颓势。
晚清小说关涉俄国情事者甚多,既有创作如《东欧女豪杰》,也有大量翻译作品,如马克·吐温的《俄皇独语》(The Czar’s Soliloquy)㊶、森林黑猿的《俄宫怨》(《露国の宮廷》)㊷、普希金的《俄帝彼得》(The Moor of Peter the Great)㊸。这反映出虚无党小说的热潮,也说明俄国故事在晚清的流行。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开启了国人对俄国政情的关注,而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沙皇统治,也让时人联想到幽禁中的光绪帝。以俄史为镜鉴者,不独梁氏一人,以至有“新小说宜作史读”㊹之说。《俄皇宫中之人鬼》借异域故事建构自家立场,目的还是指向晚清现实。译作冠以“语怪小说”名目,但根本上仍应视为一则政治寓言。
结 语
1902年,梁启超三十岁,自述“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在流离的岁月里,任公力图“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㊺,并亲自实践,参与创译。不同于传统说部志怪述奇之作,梁译《俄皇宫中之人鬼》在言说鬼魅背后,表达的是政治寄寓和思想建构。在虚无党魅影下,小说的叙事角度、异域秘闻带给晚清读者新的观感,其对专制困境的揭示,也成为呼唤新中国未来的一种力量。
梁译《俄皇宫中之人鬼》融侦探、政治、外交诸要素于一体,对近代中国虚无党小说的书写、现代短篇小说体式的形成等方面都有实际影响;并且,梁启超的翻译和论说,也为虚无党小说译述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文本范式和思想资源。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