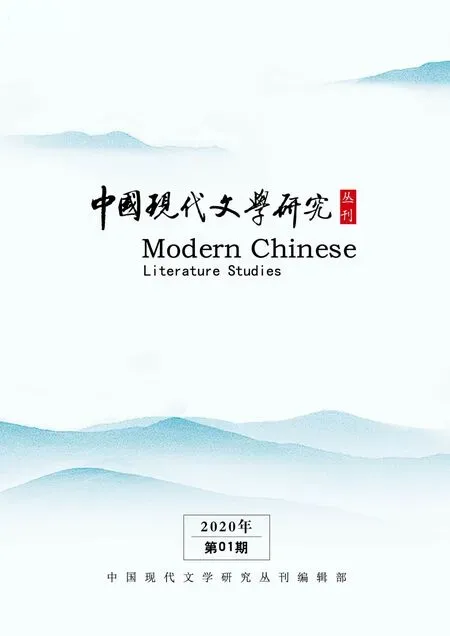鲁迅杂文话语刍议
内容提要:鲁迅的“声音”不在特定形态的文本所呈现的形象、思想、概念之中,而在以主体、语境、文本微观形态、传播能力、功能诉求等为形构要素的杂文话语中,它和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它才是我们把握鲁迅“声音”的渠道。因此,以杂文话语为对象的鲁迅研究,可以打通鲁迅著译文字的文体差异,形成另一种整体观,在一种超越性的“无”的维度上把握作为“暗内容”的鲁迅整体。
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我一直想弄明白鲁迅是什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并不新鲜,类似对鲁迅的“本体”的逼问、走近,如影随形①。但这种追问并不能满足我,或者说解决鲁迅给我的怎么说都无法说尽他文字中的意蕴的困惑,困惑如“这样的战士”在无物之阵中,虽然有所掠取,但不过是空壳,跑失的内容可能比把握到的内容更多、更真实。鲁迅是谁,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激励着我去寻求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鲁迅是无法用鲁迅话语以外的话语述说,一旦述说鲁迅就丧失了,或者说就成为他者所言说的鲁迅了。鲁迅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问题,常常被置换成怎样言说鲁迅的问题。鲁迅并非不能被述说,而是说因为鲁迅的独特性恰恰集中在其“自别异”的语言运作方式,即以主体(作者和读者)、语境、文本微观形态、传播能力、社会功能诉求等为形构要素构成的话语整体,而不在话语所“载”所“言”的如思想、主题、形象、艺术手法、造词技巧这些方面。鲁迅的“声音”是鲁迅话语众多要素的协奏效果,是一种在阅读、思维、实践等“动作”中生成而非现成的“物质”。习惯于视语言为透明工具而把握作家思想、艺术的方式,或许只是重视作家话语中的某些要素,比如作家主体,历史背景,无视作家文本生产的任何时空语境,简单地视文本为作家的声音,而不担心损害其“客观”意义的行为。这从话语自觉角度来说,即便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也是对作家作品的“罢黜—独尊”行为,用鲁迅的话说即“染”的行为,无论染黑还是染白,对鲁迅这样“善做内涵文章”②的作家尤其如此。因为鲁迅不但是话语自觉者,而且是独特的话语自觉者——杂文话语自觉。只有综合以阅读、思维和实践等“动作”来理解,并在运用语言/话语层面上足以对鲁迅产生相当同情和共鸣的,才可以有效地言说鲁迅。
一
读鲁迅,我们首先会被其语言表达的独特性所感染。在鲁迅的文本中,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字句,即便是最平常的字句,甚至标点、图画,甚至空白,都有有待说明的意义成分,是需要“想一想”“问一问”才能得到的“暗内容”③。一般以所谓“温润”“内涵”“曲折”“反语”“反面文章”“讽刺”“形象”等概括鲁迅语言特色者,都不足以解释这些符码何以有如此丰富的意义。我们言说鲁迅,实际存在着言说的两难:譬如说鲁迅“深刻”,立即觉得“深刻”这个词是对鲁迅的独特性的遮蔽,因为鲁迅被称为“浅薄”“落伍”“失败”“创作力消失”的时候也不少④。称鲁迅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时,鲁迅的“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一面就会浮现出来。说鲁迅“不宽恕”,但鲁迅的母亲和挚友许寿裳又认为他“最善良,最具同情心”。因此,那些定性或描述鲁迅的词,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进化论、文学性、典型、语言大师……从四面八方贴近、包裹而来,却无法穷尽或穿透鲁迅自身的语义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他的话语方式,而不是作为话语构成的能指、能指链,这是鲁迅文学的“第一义”。鲁迅的话语,让他的所有著译冲破教科书形式的束缚,科层分野,杂而不乱地构成了鲁迅文脉⑤的整体性特征。
其次,鲁迅话语不是一般的话语,而是杂文话语。经由“立人”—“立国”同构的主体自觉、语言文字和题材的陌生化自觉、传统文学话语的无力自觉、文字意义生成与传播的效果自觉、大小语境自觉、读者自觉、从介入到抵抗的功能自觉等系列自觉而得。每次自觉之前都经历相应的“痛苦”,譬如“考试找茬风波”“幻灯片事件”“十年沉默”“空虚”“碰壁”“华盖运”等;自觉之后则是话语觉悟的进一步和话语实践能力、实践效果的进一步⑥。鲁迅杂文话语的这个历史进程以中国为中心,主要完成于翻译、《华盖集》为初文本的杂文集与《故事新编》的写与编。总之,鲁迅为中国的文学理想在一连串的痛苦与抗争/觉悟之后,收获的是“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样的“本根”和“仁厚暗黑的地母”一样的“中国”之间的中间物:鲁迅杂文话语。这个话语的两端是如此的异质又如此依赖,为鲁迅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增添了一种“分裂的趣味”和“绝望的反抗”的两歧性底色。这个底色随时可以变现为左右、上下、内外、明暗等复调性言说空间,让鲁迅自己,也让其读者进入一个话语“横站”的尴尬世界,从而不安于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里或外、或明或暗的“和平”的、“整体”的话语习惯。阅读鲁迅,除了得到这种词与物的关系的不安以外,再没有什么明确的“建议”或“思想”了。如果有,就难免产生用习惯性的“我”遮蔽鲁迅的焦虑感,因为鲁迅确实一再说其言说给予读者的,倒不如一个“无所有”。他说,“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但是鲁迅不喜欢用左右、上下、内外、善恶这些有判断倾向的“智识”,鲁迅喜欢的是真假、冷热、红黑、有无这样的伦理性“智识”,鲁迅话语的杂文性在于,它是一个制造伦理不安和异趣的“智识型”,在自己和读者那里。
有影响的现代话语理论普遍在关于知识与话语、话语与社会/历史的理论、知识与知识型等方面立论,有些可以拿来作为理解鲁迅杂文话语的有益的参考⑦。鲁迅从1925年起开始专门写“小事情”,可称为小事情叙事。这种鲁迅杂文的小事情叙事,就是用类似知识考古方法的话语实践;用类似存在主义的态度对追求因果线性叙事的传统历史——在没有宗教神权的传统中,作为大一统集权社会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顾其不可置疑的神圣性,用名词解释的方式进行一种再叙事,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这样,在继《新生》甲乙两编和《呐喊》的创作中,鲁迅文学话语在经历了新我—新中国同构的主体自觉、语言文字和题材的陌生化⑧自觉、传统文学话语的无力自觉、自我文字意义生成与传播的效果自觉、大小语境自觉、读者自觉等鲁迅杂文话语的基本内容之后,主要在其杂文和《故事新编》的创作中建构了一种“最鲁迅”⑨的抽象的重复的物质——鲁迅杂文话语。
鲁迅杂文话语是鲁迅话语抵抗意识的自觉:首先,以话语抵抗意义,和逻各斯/经学思维相分别,从而使鲁迅文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历史话语。其次,以个别抵抗整数,和整体史观而有分别,从而使鲁迅的历史性质的话语成为一种“那世界只有我自己”的杂文话语。杂文,就是鲁迅作为“个人”“独”的“心声”“现在和生存”声,在“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⑩的“众数”“众”“将来和复古”的“恶声”中的“敢自别异”。总之,鲁迅杂文话语,是关于(经学)话语的(历史)话语,关于(整体史)叙事的(个别史)叙事,关于一切文字现象(包括他自己文字的“文学”)的“离绝了交换关系”的审美观照。对话语“改良这人生”“改良社会”功能的强调⑪,是鲁迅杂文话语的意义;丰富的信息,是鲁迅杂文话语的营养。最主要的是,强大的生存能力,而不是其所载所言的“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道”或“志”,是鲁迅杂文话语的使命。这关于生存能力的最后一点,涉及鲁迅的“绝望”问题,如果没有这一点,鲁迅可能真的是绝望的。但是本文想在鲁迅的创作动力和对意义虚妄的理解与克服上为鲁迅,也为本文所关注的鲁迅整体文脉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只能是有谱系学历史内涵的鲁迅杂文话语。
福柯分析历史的两个方法:考古学和谱系学,尤其是后者,有一种运用前者,反抗权威传统,甚至抵抗话语自身的意图。⑫这和鲁迅构建杂文话语,用有温度的“局部话语”的知识考古对抗“历史的整数”及其粗暴冰冷的甚至血腥黑暗的“四舍五入”的话语建构,用个人话语对抗权威话语,用小事件的偶发性、断裂性对抗大事件的“因果”与连续叙事、用主观话语对抗“客观”“公允”话语、用边缘对抗中心、用“从肉向灵”的“内籀”对抗“从灵向肉”“从灵向灵”的“外籀”的思维模式、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有相当的契合。这些相互对立范畴的后者,由叙事构成的意义整数和历史整数,排斥了任何意外,所建立的因果、中心、必然、体系,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比罐头还严密”,但是鲁迅在这中间还是发现了无数裂缝,鲁迅的杂文话语,就是在这些裂缝中间生成的“野草”和裂缝形成一种新的因果,共同抵抗四周的“整数”——也许是和这些整数共存,成为现代中国话语一种多姿多彩存在的结构性补充。⑬他的小说、散文、杂文、翻译,甚至学术文,共同成就其杂文话语,逼得它周围的话语从客观、透明、不言而喻、“你说你就错”“从来如此”的隐身存在、无名存在和前提性存在的状态,成为“纯文”“整文”“大一统文”“无物之阵”文……不但被迫现身,还有了可以被言说思考的名字,成了一种非前提性的运用文字的方式、话语。这真是“大道无形”的一种堕落,然而这是鲁迅杂文话语通过“写实”“立此存照”“备考”等话语功能实现的一种文学效果,一种战斗性的、抵抗性的话语效果。鲁迅杂文,如同其《故事新编》中的油滑点,点点相连成线,刻在被所谓后贤“编”成的“故事”的统一、平整、无形的面上,让这个面现身为和线相对立的物质性的话语存在。不但如此,线如一条裂缝,使得“纯文”“整文”“大一统文”“不能完美”,如同祥林嫂在普天同庆的话语世界中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困惑所奉献的被称为“谬种”的死,这些就是鲁迅所谓“天上看见深渊”者。话语整体与话语裂缝的对立,这就是鲁迅的“野草”,形式上包括鲁迅所有的著译,实际上是鲁迅的杂文话语,是鲁迅的“不用之用”——抵抗、对立,这就足够了,却不用把线扩大成新的面,鲁迅对此有深刻的自觉,鲁迅因此走出“绝望”,如同走出“希望”一样;这种自觉,也是鲁迅杂文话语的内涵。一头是历史和现实范畴的“中国”,一头是人性和文学范畴的“本根”,两头发散,两头堵,鲁迅杂文就是这样的中国—本根的结构性紧张。
二
理解鲁迅杂文话语,不妨从两方面借取福柯的话语理论。首先,话语是物质力量。作为表现内在心理世界和记录历史的工具,话语不是透明的,话语显现或者隐藏心理欲望的同时“亦是欲望的对象”;在记录历史斗争的同时,“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其次,话语物质性的构成有三个方面,即言语的对象、言语环境和言语主体。而追求整数效应的文明社会对这三方面有三重禁忌(prohibition)或者说是排斥(exclusion),三者“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这张网络织的最严密,亦即黑色方块最多之处,就是性和政治”。⑭
福柯以为,从词与物的关系来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致,那么把握世界和真理只要遵守词的系统就可以,即便其中有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都是可以忍受的,压迫是对人性中非理性的限制,是人走向真理的代价,这是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的现代集大成者是黑格尔。另一种观点是他的反驳,词与物只是一种想象的、现象的关系。所谓哲学、文艺学的语言学转换,以此为基础。此论有利于以杂文话语的方式来看待作为整体的鲁迅特质,故拿来一用。易言之,从张力结构上静态把握鲁迅的历史动态,不妨放逐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是保留逻各斯概念,作为把握不断变化甚至是转向的鲁迅文学的一种思考和言说方向的参照物,是一个颇为有效的方法。1923年,认为“文学活动,实际上是社会活动之一”⑮的鲁迅的杂文转向⑯,是他多次转向的延伸,但又有全新的内涵:放弃了文学对内容(逻各斯)的追求,只保留文学功能,也就是“不用之用”的用,作为他的文学志业的最后据点,或者说信心。这样理解鲁迅,有鲁迅自身的文本依据,也有两个外在的依据:一是鲁迅和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联系,一是鲁迅思想和知识中的儒释道背景。深受浙东文化影响的鲁迅,不但认可《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语言方式,对佛教语言与教义也有深刻理解。总之,鲁迅在危机中,认识到各种药方的偏至性,越开药方越“彷徨”。《彷徨》时期的鲁迅,不得不重新面对1909年“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问题:金铁国会的本是“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人”;五四小说的本是“为人生”,又加上了一个“时代命令”;到了《彷徨》,这种用文学的语言载“本”之道的信念受到多方面打击,如家庭、社会、同人分化、时代主题之类,从而使鲁迅变得信心动摇。鲁迅对此的第一步的反应是想要“思想革命”“布阵”,延续以前的“进化论”立场,但在“革命文学”围剿中这种出路也“轰毁”了。从“五四”以后的近十年内,鲁迅的华盖运,即他受到的多方面的外来攻击,最后都化成了对他的文学事业的攻击,终于出现“用文艺改良国民”“用文艺改良社会”的信仰危机。危机中,鲁迅的出路具有一种戏剧性:上海提供了他出路的物质条件,如大学院的“补助费”⑰、租界、革命团体、现代出版业和文化市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小说、学术和思想条件丧失了,杂文条件却具备了,这是客观。主观上,则是“不用之用”的坚守。因为1923年的“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开口”困境,鲁迅已经对词与物的必然联系失去了兴趣,再要进行“吾思吾国,如何如何”的文学事业,文学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回归语言自身,对自称为“载道”“言志”的语言现象进行“价值重估”,通过对一切自称是“客观”“公允”的“意义”言说再言说,叙述再叙述,描写再描写,这样不但避开了从正面“立论”容易招致群起而攻之、或被忽略、或被修改的创作效果华盖运,而且放弃了“只让话语在思想和语言之间占据尽可能小的空间,使得它变成了透明的沟通桥梁而不具有自身的实体性”⑱的传统的话语方式,只是坚持“说自己的话”,不“说自然的话”。自己,作为“人的发现”的最直观的言说对象,同时也是话语主体,是自然与社会两属性的矛盾体,或者用鲁迅的话说是灵与肉两个维度19:一个现在/生存/中国/肉,一个伦理/发展/本根/灵,构成鲁迅杂文话语主体的中国—本根结构。因此,鲁迅这个时候的文学不但是人的文学,而且是自己的文学;不但是现代文学,而且是现在文学;不但是文学,而且是文学话语——在文学的内涵、外延、介质、功能上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一方面赋予其“不用之用”的功能,另一方面避免它越出界限,成为“透明的沟通桥梁”,成为没有时空局限性的真理、权威。所以,1924年年底,鲁迅文学再出发,翻译以外,就只写和自己有关系、自己感兴趣的小事情,不惮其琐碎,无聊,因为这样的“我”的文字就是中国—本根的文字,这是他的文学抉择背后的主体自信。写法上凡事从自己出发,所有的议论、批评就是对言语的再言语,揭示其“自身的实体性”本质,驳斥其“透明的沟通桥梁”的虚伪性,而不惮其主观、狭隘、浅薄。这两个特点,已经使鲁迅文学呈现为一种话语建构,并且在这种话语中,鲁迅真正解决了“开口”困惑,将自己的“吾国吾国,如何如何”的从文动机在“人各有己”与“现在”的相遇中,以“对话语的话语”的方式实现了和创作效果的真正统一:鲁迅杂文话语的诞生是鲁迅新主体和现代中国的必然。
写作杂文时,或者确切地说,自觉自信地写作杂文的时候,鲁迅不但不追求“宇宙人生鸿篇巨制”,而且不相信这些,不再看重这些,也不追求词与物的必定的关系,这都是他从文学中卸载的东西。从一般的写作经验来说,没有了这些就可以不用动笔了,但是鲁迅还要追求他的“用”,因此还得动笔。这就是他的成熟期的杂文话语建构。这种建构是抽象的,所谓没有建设,只有不带引号的引语,是对历史、社会话语的文学话语;对被描写的描写——颠倒被颠倒的“人”和“文”的关系的话语革命,建构他以为的人的话语,也就是鲁迅杂文话语,作为人的话语的例证,和非人话语相对抗。这是“冲破一切传统”的文学。鲁迅的“冲破一切传统”的文学从时间顺序而言经过三次变化,从思想冲破到小说冲破,最后到话语对抗。杂文以及因为杂文而增值、变色的鲁迅文学遗产,成为一种鲁迅的话语存在,不能且不再想冲破传统,只是作为和传统共存的一极,如同翻译之于中国一样共同构成互为泻药、互为补药⑳的话语结构,丰富着中国现代语言体系。这种理解或许是过度阐释,但是要想把握鲁迅的真正价值,进而使之“创作动机和创作效果的统一”追求在当下中国成为可能,如果这个研究动机是可行的,那么此研究还有一个附加效果,即或许可以为“反抗绝望”的鲁迅和反抗绝望的鲁迅研究寻找一条出路,使二者在“反抗奴隶的生存”的路上相遇,共同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有效的文化资源:或者被取用,或者被批判。
用一定的理论“套”鲁迅杂文话语是不明智的,但是在“句子的运用”“环境”“主体”“受体”“交往”“功能”“效果”“事件性”“断裂”“抵抗”等方面研究鲁迅杂文话语,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和这些理论发生交集,事实上它们的专业性的启发和理论整合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巴赫金话语理论的社会性视角,对话与交往功能要求;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论以及主体、话语、权力关系的启迪;萨义德“话语的旅行”与翻译,传播的观点等。这些关于话语的权威论述,共同点是承认语言文字的符号性和社会性,福柯进而提出主体性、偶然性,然后是在运用和效果的视角来关注之,这就对之前的思想研究、纯客观语言学研究形成冲击。这种冲击,和鲁迅在思想和社会的两极之间,坚持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中间物立场,也就是兼顾形式与内容,思想与社会,真与善的杂文话语的立场,发挥文学“不用之用”,以主观性极强的个体话语对抗一向被视为“公允”“客观”因而权威的“历史的整数”话语的文学实践,产生共鸣。这种对抗从有结果预期到不再预期结果,因为战斗“正无穷时”,结果云者不过是文字,于是坚持对抗本身成了目标:“他举起了投枪。”
鲁迅在日本的时期,甚至在1923~1927的“第二过渡期”中㉑,鲁迅从文的动机都是“改良这人生”“改良社会”,但是主客观的不利条件,使他放弃了“良”的期待,保持着“改”的极具“动作”意味的姿态。鲁迅的一生及其文学事业,最后定格在“他举起了投枪”这一动作。不问“良”之与否的“改”,这就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国”是其中心,杂文和杂文化的《故事新编》是其文本的完成形态。这是一种话语的姿态,姿态的话语,也就是“无所住心”的话语对抗成为鲁迅文学的全部。这种姿态颇为符合林毓生借韦伯的话说鲁迅关于“不计后果”的“意图伦理”。鲁迅从求改良社会人生的无果而绝望到对改良本身和超越事实判断的意图伦理的坚持,立足意图正义。这里的佛家用语和鲁迅所称道的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图伦理相近。如果说鲁迅在结果期待中获得了焦虑的话,鲁迅在“只问耕耘不求结果”的心态中获得了焦虑的解放,并且使他的写作不但成为张旭东所谓的本色的政治写作,而且还是一种政治“承当”,直接呈现为以“本根”为张力异端的鲁迅杂文话语主体的“中国”形态:“他对政治的承担来自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的反思,这是一个长期的精神过程,和那种盲目的、宗教式的信仰(例如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的信仰)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同意林毓生的看法,以为鲁迅的政治承担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情感,因而不允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㉒但是这样的理解对鲁迅“结构性紧张”的思想矛盾与深刻性不啻于是一种遮蔽,不但是对鲁迅的泛道德化理解,也是对林毓生的道德的纯化阐述。“鲁迅肯定了儒家对于政治所持的理想,认为政治应该是根据‘意图伦理’追求道德性的目标;他同时透过具体的观察,肯定了法家对于政治的现实所获得的了解,认为政治实际上是以不道德的行为来追逐不道德的目标。”㉓可见,林毓生重视鲁迅道德感的同时,也重视其“现实”的一面,这是符合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事实的。这对他而言,是一种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类似存在主义的良方。对鲁迅而言,为求“创作动机和创作效果的统一”,他所从之文最终走向了对具有断裂意义的小事物的关注,对叙事的再叙事,对语境的营造,对读者的期待等运用语言而非被语言运用的模式——以人对语法、主体对道理的革命性转换,实现了上文所谓颠倒被颠倒的“人”和“文”的关系的话语革命的内涵。这些实践在后来的巴赫金、福柯等人的话语理论中不难遇到知音。如果以鲁迅的相关论述来和这些观点相互印证,也是不难找到的。比如上文所论的以“我”为主的小事情叙事如此,鲁迅《故事新编》对旧典的“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的方法亦如此。但是鲁迅杂文话语的“中国气派”毕竟以他的新我主体为灵魂,以所身历的中国历史为骨架,以其多样文本形态为肌肤。因此,鲁迅杂文话语作为一个问题,其学术价值必将有待于对鲁迅杂文话语的主体内涵、历史与文本形态的深入考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