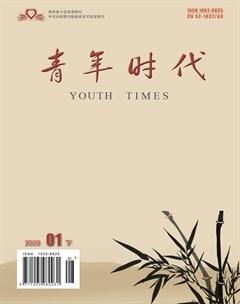浅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北京人》
马彩云
摘 要:曹禺是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在创作第一个话剧《雷雨》时,精神分析学说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十年之久。因此他在刻画人物、描写冲突等方面均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影响。《北京人》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部作品,以一个典型没落士大夫家庭的经济衰落为串连全剧矛盾的线索和具体背景,曾家三代人为主人公,展开了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1]。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北京人》进行阐述和分析。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视角下研究《北京人》,意在探求剧中人物身上的精神分析学因子,从而更加清晰深刻地理解人物和作品。
关键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北京人》;曹禺
一、本我、自我与超我矛盾下的人物塑造
《北京人》中的人物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压抑与矛盾。曾家就像一个黑暗的王国,处处散发着腐朽的棺材气息。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租住在曾家的袁氏父女,几乎每个人都是压抑的。他们内心苦闷,活得拘束。这些都体现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矛盾。
(一)曾文清
曾文清是曾家的大少爷,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但他性格软弱无能,常给人一种懒怠之感,是个没有生命力的空壳。在情感上,他不喜欢自己的妻子,而是爱上了一个真正理解他的女人,愫芳。愫芳与他从小相爱,可就因为他胆小懦弱,不敢要她,导致愫芳从少女逐渐变为老女,在曾家耗费了自己的青春。他的内心是苦闷的,他爱愫芳,可是他尝不到爱情的甜蜜,不敢追求自己希望的幸福。
曾文清没有娶愫芳一方面是道德思想上的约束与禁锢,他的超我人格使他按着至善原则一直坚守着自己原本不幸的婚姻,对愫芳并没有做出逾越礼教的任何事情。他爱慕愫芳、尊敬愫芳,将愫芳视为知己,甚至是他的精神支柱,却没有因为自己的本能私欲而将愫芳据为己有。这是一场超我人格在社会道德标准下与本能冲动的较量。
另一方面,由于软弱无能的性格,在妻子对他和愫芳关系的冷嘲热讽时,他选择了逃避。他没有勇气直面自己妻子的淫威,只能在心底里挣扎;同时他也不敢面对自己的爱情,总戴着逃避的面具来应付一切。他认为愫芳已经在曾家待了多年,不会离开他。所以他就开始大胆地享受着愫芳带给他的精神上的爱情。但是曾文清的本我一直被壓抑着,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即使是有精神上的爱恋,他依旧内心苦闷,活得苍白无力。可以看出,曾文清的自我一直在控制着本我的欲望,使自己在社会现实中处于相对有利或舒适的地位,但这种本能的爱欲在封建礼教和软弱性格的摧残下逐渐变成了不可拯救的痛苦。
(二)愫芳
愫芳是曾文清的表妹,深爱曾文清,愿意没有名分的守在他身边,为他苦等。在这个家中,她也时时处于压抑之中,饱受情感上的折磨。曾文清出走后又偷偷地回来见过愫芳,从那之后,愫芳便决心为他守着这个家。当瑞贞劝解愫芳时,愫芳突然觉得很快乐,心好像打开了,暖暖的,似春天来了一样。她说:“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2]“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单是为着吃才活着的啊!”[2]此时此刻,愫芳的超我人格已经居于上风,她本能的爱欲看似被压抑,实则是在道德教化下得到了满足,她的精神和情感都得到了释放。愫芳拥有美丽的内心世界,愿意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这是她爱和超我的升华。
曹禺在谈《北京人》时,曾讲到一个故事。大概是1957年,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北京人》,周总理去看戏了。散场后,他请剧团把第三场“天塌了”那场戏重新演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导演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是不是新给愫芳加的。导演说,剧本上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人都说愫芳傻,她怎么能爱上曾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了自己[2]。的确,愫芳的在超我的精神状态下,本我达到了最大的满足。爱,使她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人性美得到最大体现,使她那受苦难折磨的灵魂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辉。
二、生与死的召唤
《北京人》中存在着一些“去”和“留”的问题。在曾家这样的黑暗王国里“去”和“留”是关系到人物“生”与“死”的重大命运问题。“去”意味着“生存”,“留”意味着“死亡”。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这两种本能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此涨则彼消,此消则彼涨。生的本能代表着创造和爱的力量,是人生命力量的源泉。死的本能,即生命自身潜在的一种破坏性力量。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主张,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死亡的本能是设法要使个人走向死亡,因为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那么用这种理论来解读《北京人》中的人物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在黑暗衰败的曾家,瑞贞就像一个新生的力量,一直想要逃离这个家,跟着自己的“朋友”走向光明。而无依无靠的愫芳被自私的曾皓当作自己暮年残境中的拐杖,不肯放手;曾思懿因着自己丈夫和愫芳之间的爱慕而处处为难愫芳;自己所爱之人又是个生命的空壳。在这样的环境中,愫芳像那秋日里的花渐渐枯萎,没有生气。这时,瑞贞的劝说,袁家父女和北京人的出现给愫芳带来了生机。“天塌了”[2],愫芳放弃了原本想要守护的一切,随瑞贞和袁家父女一起走出了曾家。结尾,“北京人”的那句“跟——我——来”[2]打开了曾家的大门。“北京人”就是人类生存本能的外在象征,丰满旺盛的生命力的代表。“去”就是获救,就是这黑暗王国中的一丝光明。同时,这也是作者精神诉求上的极大安慰。
曾文清是个精神上瘫痪的人,他曾经有过求生的欲望,走出这个家,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应了他爹的那句话:“没有志气,早晚还是要回来的。”[2]曾文清的“获救”是失败的,他懦弱的性格导致他放弃了生存的机会。他厌恶自己的妻子和家庭,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之人,更没有力量支撑起这个家。他精神上屡遭折磨,心中尽是苦闷,又无法宣泄,只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欺骗自己。最后他索性自暴自弃,否定自己前半生的价值,吞食鸦片自杀了。曾文清的悲剧在于,多年的陶冶熏染的封建文化思想和教养,已经腐蚀了他的灵魂。他自杀说明他已开始认识自我,对自己、对封建家庭生活已经厌弃与绝望[1]。
與曾文清一样有着死亡本能的还有他的儿子曾霆。曾霆的婚姻也是不幸的,他与妻子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两人之间没有爱情,只有痛苦,所以在曾霆得知妻子怀有身孕时,他哭了,嚎啕自己真想死啊。曾霆的自我痛恨,自我责备是他死亡本能的重要体现。他已然对生活和新生命丧失了原本的希望和信心。
三、曹禺的“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对母亲的排他性占有欲。而这种排他性指的是任何人,包括他的亲生父亲。当“任何人”对他构成威胁时,他都会产生仇恨,甚至想要杀掉他们。
关于母亲,曹禺曾在给巴金的信中谈及到。母亲在他出生后就去世了,后由继母抚养。他很爱继母(母亲的孪生妹妹),但当得知母亲的事情后,还是表现出了失去母亲的心痛,以及对所有母亲伟大的赞扬。相反,对于他的父亲,他表示曾有段时间很怕他,父亲脾气很坏,经常训斥家里人,他不愿和父亲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他恨他,怕他,但不能没有他。
后来,曹禺的“恋母仇父”情结便开始无意识地逐渐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北京人》中的老太爷曾皓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皓,自私虚伪,道貌岸然,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人照顾,不惜牺牲愫芳,阻止她嫁人,迫使愫芳成为自己的拐杖。他极度怕死,同时又担心死后的那点面子,所以一遍一遍地给自己的棺材上漆。他恪守着封建教条下的那点“规矩”,做主了儿子,甚至孙子的婚姻,让两代人都处于痛苦中。曾皓虽是父辈长者,但在曹禺的创作中,曾皓这类父亲更像一个吃人的恶魔,带有极大的贬义色彩。
《北京人》是曹禺的戏剧创作在40年代的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期的《北京人》已经不似30年代的《雷雨》那般紧张激烈、激荡郁愤,反逐渐转为平淡深沉、忧郁明朗[1]。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曹禺的《北京人》,一方面有利于加深对剧中人物和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加明晰曹禺话剧创作的价值意义和精神内涵,深入感受其作品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郭娟.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王宁.文学与精神分析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