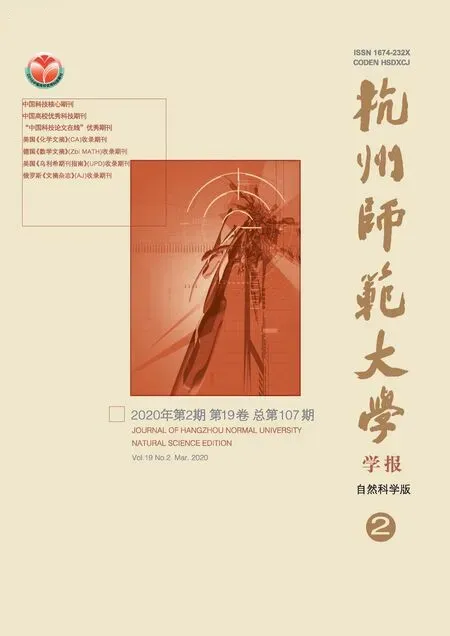农村高中生亲子依恋、羞耻倾向与网络欺凌关系研究
张珊珊,张 野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2019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数规模已达8.29亿,19岁以下青少年占21.6%,人数超过1.79亿[1],青少年已然成为使用网络的主要人群.青少年在享受着网络世界带给他们方便、便捷的同时,也承受着网络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其中,网络欺凌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伤害行为.从概念上来说,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是指借助网络媒介,通过网络交流的方式(如网络言语、网络图片、网络视频等)对受害者实施针对性的一种攻击行为[2].有关研究也显示34.84%的高中生报告自己曾有过网络欺凌行为[3],这说明高中生群体中发生网络欺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其中,网络聊天室、手机短信、QQ、微信、网络游戏以及其他社交平台也是高中生行使网络欺凌的主要途径[4].
网络欺凌作为青少年的一种不良行为,通常和反社会行为、攻击行为、违纪行为一样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了学生的内在个性特征、情绪情感特点、家庭环境与教养、学校监管与教育、社会环境及网络环境等.在家庭环境中,已有研究发现不良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违纪、反社会行为和退缩、攻击行为有正向的预测作用[5-6].还有研究指出,与拥有亲子依恋关系较差的青少年相比,拥有良好亲子依恋关系的青少年社会能力更强、学业成绩水平和幸福感水平更高[7].近期,针对网络欺凌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特别是那些有较多欺凌行为的青少年,都拥有着不完整的家庭,缺乏父母的有力监管与心理支持,时常表现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2].基于上述研究可知,亲子依恋是引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家庭环境因素.因此,本研究首先要探讨的是亲子依恋关系与网络欺凌的关系,进一步确定积极依恋关系对网络欺凌的抑制作用,而消极依恋关系则起着诱发作用.
在导致青少年网络欺凌发生的个体特征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已表明,网络欺凌除与人格特征、自我控制、抑郁等有关外,还和羞耻倾向相关[8-9].如Elison等人的研究发现,羞耻倾向是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所有形式的暴力都可以用羞耻倾向来预测[10].根据羞耻的进化心理模型可知,羞耻是一种消极的负性情绪,而欺凌、攻击则是对此消极情绪的调节、应对策略或进化适应的一种表现形式[11].因此,外源变量引起个体的攻击行为关系中,羞耻可能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还有研究显示,亲子依恋与羞耻倾向密切相关,高质量的依恋关系与个体的羞耻倾向呈显著负相关,而低质量的依恋关系与羞耻倾向呈显著正相关[12].因此,本研究推测亲子依恋可能通过羞耻影响网络欺凌,扮演中介变量的“角色”.
综上所述,研究以农村高中生为调查对象,验证亲子依恋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作用以及考察羞耻倾向是否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设:1)亲子信任和沟通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而亲子疏离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2)羞耻倾向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欺凌.研究以期为农村高中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预防与干预提供实证依据和支持,减少农村高中生的网络欺凌行为,防止网络环境中的不良行为出现,促进农村高中生群体心理健康的发展,同时丰富国内关于羞耻倾向与网络欺凌的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辽宁省4所农村高中抽取1311名高中生,从回收的调查问卷中筛选出有效问卷1 165份,有效率88.90%.其中,男生504名(43.26%),女生661名(56.74%);非独生子女668名(57.34%),独生子女497名(42.66%);非留守儿童514名(44.12%),留守儿童651名(55.88%);高一484名(41.55%),高二465名(39.91%),高三216名(18.54%),平均年龄为(17. 04±1. 16)岁.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亲子与同伴依恋量表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 1987年编制的青少年亲子与同伴依恋量表[13],本次使用了该量表的亲子依恋分量表用以评定亲子依恋质量,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量表均包括信任、沟通、疏离3个维度,两个分量表共50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依恋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分别为0.82、0.81.
1.2.2 中学生羞耻感量表
采用亓圣华于2008年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14],该量表包括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能力羞耻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从“完全没有”到“经常如此”分别计1—4分,项目总分数是所有项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羞耻倾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为0.85.
1.2.3 中学生网络欺凌问卷
采用张野等人2015年编制的中学生网络欺凌问卷[15],本次使用了该问卷的实施网络欺凌分问卷,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权益欺凌3个维度,共11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从“从来没有”到“总是”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实施网络欺凌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信度为0.81.
1.3 质量控制
实施测试前,研究人员统一培训调查人员,调查人员向学生征求同意并发放调查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调查,当场填写且回收问卷.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自愿参加调查,整理问卷时对问卷完整性进行检查.数据回收后,由研究人员对问卷进行编号,并将问卷的数据集中录入到SPSS分析软件中.
1.4 数据处理
在使用SPSS21. 0以及Amos22.0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等.
1.5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KMO=0.87,Bartlett值为28 170.02(P<0.01),共有21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所有项目析出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变异的21.14%,小于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2 结果分析
2. 1 农村高中生亲子依恋、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农村高中生在父子信任、父子疏离、母子依恋各维度和网络欺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表现为男生的父子信任、母亲信任、母子沟通得分显著低于女生(Ps<0.05),男生的父子疏离、母子疏离和网络欺凌得分高于女生(Ps<0.01);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网络欺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s<0.05),独生子女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有留守经历与非留守经历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各维度、网络欺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表现为有留守经历的父子信任、父子沟通、母子信任和母子沟通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Ps<0.05),有留守经历的父子疏离、母子疏离和网络欺凌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Ps<0.05),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高中生亲子依恋、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的人口学差异Tab.1 The demography difference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he tendency of shame and cyberbullying in rural senior school students
注:*P<0.05,**P<0.01,***P<0.001.
2.2 亲子依恋、羞耻倾向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示,羞耻倾向各维度、网络欺凌与父子信任、父子沟通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1),而与父子疏离、母子疏离成显著的正相关(Ps<0.01).除行为羞耻维度外,羞耻感其他三维度与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呈显著负相关(Ps<0.01),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高中生亲子依恋、羞耻感与网络欺凌间相关矩阵(r)Tab.2 The correlation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he tendency of shame and cyberbullying (r)
注:*P<0.05,**P<0.01.
2.3 羞耻倾向在亲子依恋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检验
2.3.1 父子依恋在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预测中的中介作用
检验父亲依恋(父子信任、父子沟通和父子疏离)对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控制性别变量后,分别以父子信任、父子沟通和父子疏离为自变量,以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子信任对羞耻倾向(β=-0.19,t=-6.56,P<0.001)和网络欺凌(β=-0.23,t=-7.09,P<0.001)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子沟通对对羞耻倾向(β=-0.18,t=-6.11,P<0.001)和网络欺凌(β=-0.10,t=-3.55,P<0.001)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子疏离对羞耻倾向(β=0.28,t=9.76,P<0.001)和网络欺凌(β=0.18,t=6.16,P<0.001),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β=0.18,t=6.16,P<0.001),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建立父子依恋(父子信任、父子沟通和父子疏离)通过羞耻倾向预测初中生网络欺凌的中介模型,模型指数:χ2/df=3.526,RMSEA=0.047,CFI=0.99,TLI=0.98,SRMR=0.36,拟合较好.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加入羞耻倾向中介变量后,父子信任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25,t=-5.31,P<0.001);父子沟通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12,t=2.85,P<0.01);父子疏离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07,t=2.01,P<0.05);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16,t=5.30,P<0.001).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抽样2 000次,在95%的置信区间内,羞耻倾向分别在父子信任、父子沟通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区间为[-0.006,0.002]、[-0.010,0.003],均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而羞耻倾向在父子疏离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区间为[0.011,0.028],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37.
2.3.2 母子依恋在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预测中的中介作用
检验母子依恋(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和母子疏离)对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控制性别变量后,分别以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和母子疏离为自变量,以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子信任对羞耻倾向(β=-0.17,t=-5.88,P<0.001)和网络欺凌(β=-0.20,t=-6.99,P<0.001),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母子沟通对羞耻倾向(β=-0.10,t=-3.46,P<0.01)和网络欺凌(β=-0.12,t=-4.10,P<0.001),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母子疏离对羞耻倾向(β=0.22,t=7.51,P<0.001)和网络欺凌(β=0.19,t=6.68,P<0.001)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β=0.18,t=6.16,P<0.001)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建立母子依恋(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和母子疏离)通过羞耻倾向预测初中生网络欺凌的中介模型,模型指数:χ2/df=1.201,RMSEA=0.004,CFI=1.000,TLI=1.000,SRMR=0.172,拟合较好.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加入羞耻倾向中介变量后,母子信任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13,t=-3.14,P<0.01);母子沟通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2,t=1.69,P>0.05);母子疏离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11,t=5.56,P<0.001);羞耻倾向对网络欺凌直接效应显著(β=0.17,t=5.41,P<0.001).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抽样2 000次,在95%的置信区间内,羞耻倾向分别在母子沟通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区间为[-0.001,0.026],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而羞耻倾向在母子信任、母子疏离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区间为[-0.201,-0.073]、[0.021,0.180],均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15,0.029.
3 讨论
3.1 农村高中生亲子依恋、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网络欺凌显著高于女生,与石国亮等人的研究发现涉及网络欺凌的主要群体为男性的结论相一致[16].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首先,Erdur-bake研究认为,男女生在使用网络风险态度上存在差异,通常女生比男生在使用网络上更加谨慎[17],这就减少了女生出现网络欺凌、网络成瘾等偏差行为可能性;其次,男女生在性格上的差异也是网络欺凌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男生更加冲动、喜好寻求独立、但却缺乏辨别力[18],而女生比较乖巧、善于交流,这就使得男生更易依赖于网络生活,进而加大了他们发生网络欺凌的可能性;最后,Ang和Goh研究认为男女生在共情能力上存在差异,在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能力方面,女生都占有优势,她们会表现出弱攻击性和强共情性的特点[18],因而会很少涉及网络伤害事件中.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男生的父子信任、母子信任得分都低于女生,而父子疏离、母子疏离得分却高于女生,这一方面说明处于高中阶段的男生比女生更加独立,对父母的依赖程度也较弱,而上文提到了男生更容易涉及网络欺凌事件中,也可能是男生在网络世界更容易释放、宣泄自己的情感,而不喜欢与父母倾诉有关.本研究发现,为独生子女、有留守经历的农村高中生网络欺凌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无留守经历,这也说明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和亲子互动等也可能是诱发网络欺凌的原因,以往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结果[9].所以,在对农村高中生进行网络欺凌行为的干预时,一方面我们应该侧重增强男生的网络使用风险认知能力及提高其共情能力;另一方面,要重点关注独生子女、有留守经历的农村高中生,并通过改善与父母依恋质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降低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
3.2 亲子依恋和羞耻倾向是影响网络欺凌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父子信任、父子沟通、母子信任、母子沟通与网络欺凌呈负相关.这说明父、母与子女的信任关系、沟通水平是防止高中生网络欺凌发生的重要外部保护性因子.农村高中生获得的自己父母越多的信任,与父母越多的沟通,越有利于他们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的成长,以致减少不良行为的出现[5].其次,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与网络欺凌呈正相关.这可能是与父、母关系较疏远的个体,内心体验较孤独,倾向于通过网络欺凌的方式宣泄内心的压力及对现实的不满,这证实以往研究不良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有着消极影响的结论[6].研究还发现,羞耻倾向与父子、母子疏离呈正相关,与父子、母子信任和沟通呈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羞耻体验是一种消极情感,李瑶等人研究证实父母频繁、严厉的惩罚会使子女过于苛刻和严厉地评价自己的行为、态度和欲望,进而产生羞耻倾向[19].因此,父子、母子疏离作为消极依恋关系是可以增强个体羞耻倾向的体验,而父子、母子信任和沟通作为积极依恋关系是可以减少个体羞耻倾向的体验.
3.3 羞耻倾向在亲子依恋与网络欺凌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检验发现,羞耻倾向分别在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与网络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父子疏离、母子疏离既可以直接影响网络欺凌,也可以通过羞耻感间接地影响网络欺凌.齐春辉等人在探讨羞耻倾向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羞耻倾向对个体的品行问题有促进作用,高羞耻倾向的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更易体验羞耻倾向,并为了维持自己认为的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攻击行为[19].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证实羞耻倾向对个体虚拟网络上的攻击行为(网络欺凌)同样也有着影响作用.另外,父子疏离、母子疏离直接影响网络欺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8、0.19,父子疏离、母子疏离通过羞耻倾向间接影响网络欺凌的路径系数为0.04、0.03.从路径系数上来看,父子疏离、母子疏离的直接作用仍是网络欺凌的主要影响路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良好关系是社会支持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仅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呈正相关,维持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体验,还能增强青少年的心理应激能力.所以,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为农村高中生消极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改善不良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农村高中生积极品质的形成(减弱羞耻、焦虑、抑郁、自卑等情感体验),最终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证实了前人强调亲子依恋在青少年问题行为、消极情感中的保护作用[11,20].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发现羞耻倾向仅在母子信任与网络欺凌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说明日常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充分信任、积极沟通作为保护因素,更可能避免羞耻倾向带给农村高中生网络欺凌的影响作用.
3.4 研究的局限以及展望
本研究虽然对亲子依恋、羞耻倾向和网络欺凌这3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为农村高中生网络欺凌的防范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仍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研究仅关注了依恋中的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可以进一步探讨同伴依恋在网络欺凌中的作用.同时,今后研究可以对农村高中生与城市高中生的网络欺凌的影响模型进行群组分析,明晰不同生源地的高中生在网络行为上的差异性.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学生亲子依恋、羞耻倾向与网络欺凌的关系密切相关,其中主要结论如下:
1)网络欺凌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有留守经历上存在差异;
2)羞耻倾向各维度、网络欺凌与父子信任、父子沟通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与父子疏离、母子疏离呈显著的正相关.除行为羞耻外,羞耻感其他三维度与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呈显著负相关;
3)羞耻倾向分别在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网络欺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