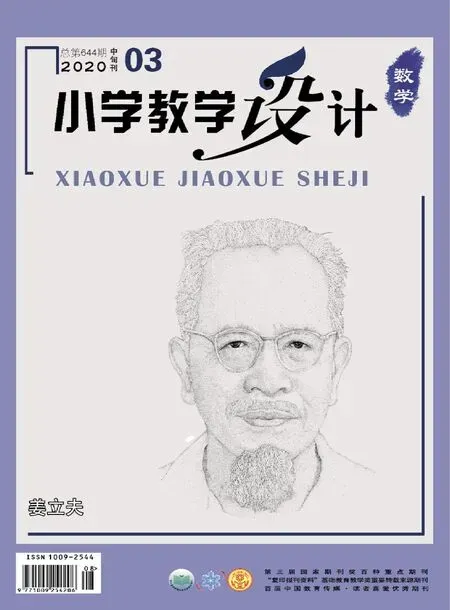勿让优化变成窄化
——以《替换的策略》教学为例
戴 俊
课堂教学中,在对解题方法多样化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思路优化,是激活、打开、凝练学生思维的既定路径,这种优化不应以是否简便、是否易于学生掌握等作为对思路取舍的唯一标准。以《替换的策略》一课教学为例,优化的过程中应尊重和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着重发现每一种方法背后的数学思维,畅通学生的思路,严密学生的思维逻辑性,这样的教学才更加深刻、更加高远、更加指向人的发展。
一、缘起:课堂总结后的嘀咕
《替换的策略》是苏教版六年级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包含倍数关系和相差关系的两类替换。对于倍数关系的替换,教学预设往往是:通过替换将两种量转化成一种量后,总和不变。那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在一次公开课教学中,对于例题“把720 毫升果汁倒入6 个小杯和1 个大杯,正好都倒满。小杯的容量是大杯的。大杯、小杯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教师引导学生用两种方法进行解决:一种思路是将大杯换成小杯,即“6小杯和1 大杯,共720 毫升”替换成“6 小杯和3 小杯,共9 小杯是720 毫升”;另一种思路是将小杯换成大杯,即替换成“2 大杯和1大杯,共3 大杯是720 毫升”。“这两种方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教师进行总结:“只要把两种量替换成一种量,替换以后的和还是720 毫升,它们的和是不变的。”
课至此处,这位教师带领学生经历了替换的过程,学生也对两个量是倍数关系替换的方法有了充分的体验,课堂总结出替换后和不变这一规律看似非常必然和顺畅。
但就在此时,却有一位学生在下面嘀咕着表示异议:“老师,我觉得不一定,如果将两边都乘3,就变成了9 大杯等于2160 毫升,这也是将两种量替换成一种量,但是和却发生了变化。”
这位学生的观点让大家感到很诧异,在随后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哪种方法更容易掌握的“优化”过程中,这位学生提出的两边同时扩大的方法也被“替代”了,后来再也没有被用到或提起。
二、厘清:替换的形式并不唯一
课已了,思未散。课堂中那位学生的嘀咕没有随着课堂的结束而终止, 一直在听课教师的耳边萦绕。
1.两边乘相同的数不是替换吗?

从上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等式左边6 小杯乘3,转化成了6 大杯,等式左边的1 大杯乘3,转化成了3 大杯,相加得到共有9 大杯;等式右边720 毫升乘3 得到了2160 毫升。根据“9 大杯=2160 毫升”,就可以得出大杯和小杯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存在x=n×y 这一等量关系,对于x+y=a,我们常用的方法是在等式值不变的情况下,将x 用n×y 替换,原来式子就转化成了n×y+y=a,即(n+1)×y=a,得出y=a÷(n+1)。
另外一种方法,只要将y 乘n 替换成x,原来的式子就转化成了(x+y)×n=a×n,得到x×n+y×n=a×n,即x×n+x=a×n,得出x=a×n÷(n+1)。
学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这种两边同时扩大的方法,却使和发生了变化。
2. 为何教师更倾向于教学“和不变”的替换?
在“6 小杯+1 大杯=720 毫升”这个关系式中,存在着小杯、大杯和总和三种量。第一种方法,即替换后和不变的思路中,只要将其中的6 小杯换成2 大杯,或者将1 大杯换成3 小杯,另外的两种量无需进行变换。
用第二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根据“等式的性质”,将等式的两边同时乘3,“6 小杯、1 大杯、720 毫升”这几个量都要进行变换。同时,对于“6 小杯×3”的结果,不等于18 小杯,而是转换成了6 大杯,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是很大的思维跳跃。对于解题正确率的追求,无形之中增加了执教者对学生使用这种方法的忧虑。
于是乎,在只替换一部分与需要转化三个量,在部分替换与整体转换的较量、权衡中,我们往往偏向于第一种方法的教学,第二种方法被忽略甚至是被回避,被第一种方法“替换”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重建:在知识脉络的前沿后续之上展开
华罗庚说过:“新的数学方法和概念,常常比解决数学问题本身更重要。”当我们站在学科知识发生、发现、发展的轨迹上来看替换的教学,第二种方法绝不可以用不简便、不常用来搪塞学生。
首先,在五年级的教学中,对于“等式两边同时乘一个相同的非零数,等式依然成立”这一等式的性质,学生在相关的问题解决中萌生出了一定的应用意识和能力。当出现“6 小杯+1 大杯=720毫升”,用两边同时乘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必然会出现在学生数学思维的菜单中,这绝不是偶然迸发出的一道火花,而是其思维发展的一种可能。其次,在学生的后继学习中将接触到方程组,利用等式的性质进行消元将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在六年级学生中出现,虽然“意料之外”,但亦是“情理之中”,教师应有“这可能又是一个良好的教学契机”的资源意识,要对“意外”进行灵活利用,即时开发,要提供学生展示属于自己思维方式和解题策略的机会,提供给学生解释和评价自己思维结果的时空。作为教师,不应漠视学生思维发展的这颗种子,甚至以优化的名义带领学生将其摒弃,这样将窄化学生的思维与思想。正如卢梭所说:“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用成人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
教师不应在课堂中借优化的名义而将方法唯一化甚至是绝对化。课堂不应是解决数学问题的“独唱”,而应是面向学生适应其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交响”。这必然考量到教师对儿童观、教学观、课堂观、发展观等本质问题的理解程度。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的注意力就像一只极易受惊的小鸟,当你走近时,它马上会飞走;当你抓住它并把它关起来时,以后就别想再听到优美的歌喉。”尊重学生的每一次尝试,激活学生的每一次探索,倾听学生的每一次实践……教师与学生同在一个“教学场”中,教师就有可能真正听到学生那优美的“歌唱”,师生也有可能会实现真正的“同频共长”,这才是课程优化、教法优化、思维优化、素养优化……趋近的结果。